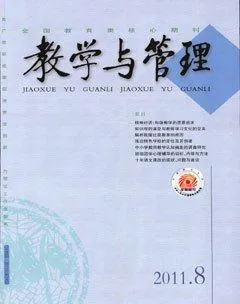“共生”视角下的农村教育扶贫路径探讨
一、资源丰富却经济贫困:农村贫困面临的突出问题
石家庄市地处河北省中南部,共有国家级贫困县3个,省级贫困县1个。综观赞皇、平山、灵寿、行唐四个贫困县的历史沿革和自然资源状况,不难发现,四县均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平山、灵寿、赞皇境内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都在30种以上,并且储量丰富;四县出产的核桃、红枣、花椒、红薯等产品,其产量和品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名列前茅。贫困县境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共同构筑了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除一大批红色旅游胜地外还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处。
然而丰富的资源并未转化为现实财富,2007年河北省贫困户建档立卡数据显示,行唐、灵寿、赞皇三县贫困人口比例和贫困户比例都在30%以上,贫困人口和贫困户所占比例最低的平山县,其贫困人口和贫困户的比例也都在20%以上。调研中发现,这些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生活环境恶劣、生活质量低下,石家庄市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至今一直徘徊在2500元左右。和全国许多贫困地区一样,资源富集与经济贫困伴生是石家庄市扶贫工作长期难以突破的瓶颈。
二、人口素质与自然、人文环境的要求不匹配:农村贫困的症结所在
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并未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不仅“输血”、“造血”工程收效甚微,而且低收入人口返贫率高、贫困代际传递明显。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其症结何在?反观我们在贫困治理各个阶段的努力,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将治贫的重心定位在了经济层面,忽视了贫困主体——贫困人口在摆脱贫困中的作用。事实证明,人口素质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要求脱节,无法将丰富的资源转化为现实财富正是农村贫困问题的症结所在。
1.贫困主体素质偏低是“输血”和“造血”工程功能失灵的根源
研究贫困地区的特征发现,农村人口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偏低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土地本身不是造成贫穷的关键因素,人力才是。在提高人口素质上所进行的投资会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主体素质过低才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各种扶贫措施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一系列的“输血”和“造血”努力之下,石家庄市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至今一直徘徊在2500元左右,脱贫步伐明显趋缓。英克尔斯也指出:现代人素质在国民之中的广为散布并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本身的基本因素[2]。可见,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要彻底摆脱农村的贫困状况,国家的政策、资金扶持只是外在因素,最主要的是依靠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功能。这一任务的实现,没有农民观念的改变、素质的提高,其自身的“造血”系统不被激活,外在的扶持措施再完善也无济于事。它不仅是造成目前贫困地区落后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是造成将来贫困地区更加落后的原因。
2.“贫困文化”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动力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贫困文化是由贫困人口面对贫困时的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所形成的一种边缘亚文化。在调查中发现,石家庄市的农村贫困地区,很多贫困人口就生活在这种自我维系的“贫困文化”体系当中。他们普遍存在着进取不足而守成有余的心理特征,不仅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更重要的是风险承受能力低、不愿冒险、有很重的依赖思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文化知识无所需求,对受教育轻视。近年来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持续的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强了贫困人口这种依赖政府、安于现状的观念。这种贫困文化通过它特有的代际传承的性质,将这套病态的信仰快速传递给贫困地区的未成年人,成为贫困地区持续贫困的根源。
三、构建“共生”教育模式:走出农村扶贫困境的现实路径
人口素质与资源环境要求脱节使扶贫工作陷入困境,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借助教育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赢”,构建适应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共生”教育扶持体系。
所谓“共生”,是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同它外部世界的良性发展形成一个互补的系统,而非单纯征服自然,即人与自然的“共生”;其次是区域文化之间的相处和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共生”[3]。我们的教育的基本立场应当立足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实现贫困地区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共生。
1.改革基础教育,奠定“共生”教育模式基础
首先,继续研究教材使用的“校本研究”之路。正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环境与资源差异,编写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的乡土教材;同时使课程设置切合当地实际,让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所学知识在脱贫致富中的实际效用。其次,要注意因材施教,分层次培养。不仅要使少数能升学的学生“榜上有名”,而且要使大多数不能升学的“陪读”生“脚下有路”;让他们不仅有务农的思想准备,也有务农的技术准备。对此,可采取适时“分流”的办法来实现,根据不同学生的现实状况采取不同的培养模式。
2.创新职业教育,实现贫困地区人与自然的“共生”
贫困农村地区的“共生”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可借鉴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日本通过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法国注重为农业发展提供需要的耕作、收获等机械,设法提高生产率。其中尤以韩国新村运动中的教育最为典型。韩国新村运动中的教育包括几个层次:从基础层次的教授农民制作简便农业劳动服和进行合理的劳动管理到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对农民进行知识素质教育,分层次进行农民职业教育。
鉴于这些国家的经验,可以在贫困地区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不断调整和更新教育培训内容,开展动态的、多层次的职业技能教育。这就需要我们按照“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深入各地广泛开展农村实用种养技术培训,对农民进行现场技术培训和指导。为此,必须充实农业科技力量,壮大农村科技人才队伍,建立适应需要的科技培训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培训制度。同时,加强农民转移培训,开展职业技术技能培养与培训,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职业转移能力。
3.重视人文教育,实现贫困地区人与文化的“共生”
首先,寓人文教育于科学教育,促进二者有机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的价值是中立的,但其社会应用则是有价值负荷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科技治愚、科技扶贫其实渗透和负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在给贫困人口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有重点地对科技人员进行政策、道德、法律等方面的培训,强化其科学的良知和责任意识,从而使其在向贫困人口输入科技信息的同时也输入新的价值观念,打破贫困人口原有贫困文化系统,培养构建他们新的文化体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对当地资源进行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有效改变贫困代际传递的状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其次,加强人文关怀,促进贫困人口的社会融入。贫困人口从整体上说是一个心理脆弱的群体,自我调节能力差,经受挫折后往往心理失衡,具有较强的失落感。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除物质上的扶持帮助外,更需要人文关怀和感情投入。在教育过程中帮助他们树立乐观向上的精神,积极的生活态度,使他们在困难的处境中不断挖掘自己的才智,不畏艰难,共同战胜贫困。
参考文献
[1] [美]西奥多·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演说文集.罗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 [美]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张诗亚.共生教育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新思路.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1).
(责任编辑郭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