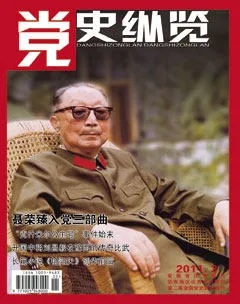瞿秋白与蒋光慈:一对殉于而立之年的亲密战友
瞿秋白,中共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899年1月29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大夫之家;蒋光慈,中国早期革命作家、小说家,1901年9月出生于安徽霍邱县一个轿夫的家庭。两人都在而立之年为革命事业殉道离世,而他们在短暂人生中结下的诚笃友谊,则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美谈。
赴莫斯科:相识相知两青年
1920年初,瞿秋白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他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莫斯科,采访考察,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这一年的春季,蒋光慈也赶赴上海,进入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所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专修俄语。翌年初春,蒋光慈同刘少奇一起受组织派遣去苏联留学。当时,联共(布)创办的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设了一个“中国班”,为中国培养人才。蒋光慈、刘少奇即被编入这个班就读。然而,在这个班的任课教师中,除一位名叫葛丽哥罗夫的教师会讲中国话之外,其他人都不懂中文,语言不能交流,成为中国学生的难题。于是,共产国际便将精通俄语的瞿秋白请来,担任这个班的助教与翻译。瞿秋白与蒋光慈这两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就此相识并一见如故。瞿秋白作为兄长又作为老师,与蒋光慈谈学生运动,谈当今革命,谈理想,谈文学,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使蒋光慈顿生相见恨晚之感。
1922年7月1日,瞿秋白的《赤潮集》出版问世,蒋光慈如饥似渴地读着,睹见书前序中有“西来意”一语,随之感慨顿生,即以《西来意》为题,赋诗一首,送给瞿秋白:
渡过了千道江河,
爬过了万重山岭,
……
不计跋涉的艰辛,
俄乡的风雪冷!
维它呦(维它为瞿秋白笔名,作者注),
俄罗斯好似当年的印度,
你我好似今日的唐僧,
……
瞿秋白读后,热情地对蒋光慈说:“你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蒋光慈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之间过往更加密切。这对师生时常聚在一起读诗论文,交流创作心得,颇为默契。瞿秋白散文通讯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字里行间闪光的思想和非凡的文采,使蒋光慈受益匪浅;而对蒋光慈的诗集《新梦》,瞿秋白也“欣然赞许”,并多次进行了润正。
到上海:良师益友喜重会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这年夏天,经李大钊推荐,他来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次年秋,蒋光慈亦回到上海,故友重逢,欣喜异常。于是,瞿秋白介绍蒋光慈进入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教俄语课。蒋光慈教书之余,坚持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还不断与瞿秋白切磋文学问题,这段时期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蒋光慈便成了瞿秋白家的常客。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回忆说:“蒋光慈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同秋白谈论文学工作方面的问题,了解革命斗争的情况。他是一个努力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又有文学才能的同志。”这一时期,蒋光慈先后完成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和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少年漂泊者》,集内的每篇作品,都由瞿秋白提出具体意见,经过反复修改才定稿的。
在瞿秋白的激励下,蒋光慈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半年中,为配合北伐军的进攻,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起义的阵阵枪声,使蒋光慈兴奋不已。他不断从瞿秋白那里获悉起义的消息,激发着自己的创作灵感。当起义获得最终胜利时,蒋光慈激动地说:“当此社会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我且把我的一支秃笔,当作我的武器,在后面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
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蒋光慈夜以继日,奋笔疾书,终于写成了中篇纪实小说《短裤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对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命名,蒋光慈采取了谐音和嵌字法,让人读之自明。如小说中的人物史兆炎,原型是起义领导人之一赵世炎;小说中的杨直夫,作为中央委员,被塑造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一望便知是瞿秋白的化身。至于名字,“直”者,“之”也;“夫”则“丈夫”之略,意谓“杨之华的丈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蒋光慈是将瞿秋白写进文学作品的第一位作家。因为他对瞿秋白十分熟稔,体察亦格外深透。据有关人员回忆,《短裤党》写作的主要素材由瞿秋白提供,书名亦由瞿秋白协助拟定。“短裤党”三字,源出法国大革命史,即指“共产党”之意。1927年3月《短裤党》一经问世,宛如一颗炸弹强烈爆响,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反动势力更是由恐惧而诅咒。此时,瞿秋白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肯定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并明确指出:“暴民专政”不应成为“众矢之的”,“恰是短裤党这篇小说的理想”,值得嘉许。
在武汉:风雨如磐志不减
1927年,蒋光慈编著《俄罗斯文学》(上下卷),并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为题,收入瞿秋白的《俄国文学史》,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蒋光慈在《书前》写道:“关于本书的下卷,我要深深感谢我的朋友屈为他(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因为这是他的原稿,得着他的同意,经我删改而成的。”而当时收录瞿秋白作品的只有鲁迅、蒋光慈二人。
1927年1月,蒋光慈的第二本诗集《哀中国》,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瞿秋白为诗集做了题署。
3月中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负责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沪上,蒋光慈义愤填膺。5月初,他也追随瞿秋白来到武汉。他要去看“汉江中的热浪”,去聆听“汉江上革命的歌吟”。在武汉,瞿秋白住在汉口辅义里27号,蒋光慈住在党创办的长江书店里。瞿秋白提议要筹办一种刊物,专为当时一些进步的工农兵作家提供发表园地,并委托蒋光慈等为刊物命名。于是,蒋光慈约请了孟超、杨村人等议定以“太阳”作为刊名。正当他们紧张地投入集稿编辑工作时,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武汉发生,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一时间,武汉地区刀光剑影,乌云低黯,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遭受残酷杀戮。
风云突起,时局恶化,使蒋光慈等人的编刊计划落空。不久,党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蒋光慈亦随之回到沪上,在这里终于将“太阳社”成立起来,将一部分党员作家团结在周围。瞿秋白对太阳社热情支持,据作家阿英回忆:“秋白同意参加太阳社,是光慈在动员的。太阳社成立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是经秋白同意的。当时秋白是总书记,不便常出来,太阳社成立会和一般活动他都不来,光慈常有机会去找他。”
蒋光慈继《短裤党》后,于193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给以热情支持和讴歌。在这部作品构思落笔之前,蒋光慈特意听取了瞿秋白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思考和见解。瞿秋白始终是农民运动的倡导者与组织者,他曾热诚地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过《序言》,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瞿秋白的主张和见解,奠定了蒋光慈小说的圭臬,从而使《咆哮了的土地》首开歌颂农民革命运动的先河。
千古文章未尽才。令人痛惜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和蒋光慈这对文坛知己与战友,先后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瞿秋白在1931年1月7日上海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打成“调和主义”,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不予安排工作;蒋光慈因对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不满,于1930年10月遭到开除党籍处分。1931年8月31日,蒋光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及党内“残酷斗争”两面夹击下病故,年仅30岁。瞿秋白在遭受严重打击后,亦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