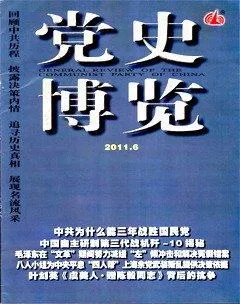邓拓\\丁一岚——新闻战线比翼鸟
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是铁肩担道义的诗人、杂文家、历史学家。他的《燕山夜话》和与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是我国杂文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
丁一岚,晋察冀抗战烽火中盛开的一朵兰花。她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开国大典时,她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转播了这一历史盛况。
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像他们的卓越业绩那样与天地长存。
“我们的婚姻。称挺笔婚如何?”
1942年3月7日,邓拓、丁一岚在河北省平山县一户村民家中结婚。第二天便是“三八”妇女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夫人张瑞华特为他俩的新婚之喜举行了家宴。
家宴中,聂荣臻向他们表示了祝贺,并提起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爱情故事。他说:周文雍同志是广东区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从1925年起就在广州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又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又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是响当当的人物。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到香港。1928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常委。省委开会提出派周文雍返回广州,负责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群众,以表示我党在广州仍有力量。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周文雍在广州出头露面干了两年多,敌人早就盯着他,派他去广州,无异于往虎口送肉。省委领导不听。周文雍很勇敢,组织纪律性很强,二话没说到了广州。果然不出所料。到广州不几天,工作还没有开展,就被敌人逮住了。同时被捕的还有陈铁军姑娘,她也是个优秀共产党员。假扮成夫妻,是掩护周文雍的。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他们始终坚贞不屈。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向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宣布举行‘刑场上的婚礼’。这说明,他俩在革命工作中已经建立了感情。这是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真正爱情的典范呀!
走在回家的路上,邓拓问丁一岚:“聂司令员家宴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从首长的谈话内容来看,从历史的教训,到刑场上的婚礼,无不体现出老首长的关爱和期望。希望我们的爱情像周文雍、陈铁军那样忠诚。”
“说得对。聂司令员多次谈到为革命办报的事,鼓励我们多写好文章,把报纸办得引人人胜。这种鼓励,谓之挺笔。我们的婚姻,称挺笔婚如何?”
1942年秋,丁一岚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从此,他俩真正成了挺笔夫妻。
在这支新闻队伍里。丁一岚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从敌人电讯中摘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重要情报资料。供边区领导参阅。因此,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晋察冀边区领导的“千里眼”、“顺风耳”。
1943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抽调数百名县、团以上干部到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邓拓、丁一岚夫妇同时成了党校学员。校址在平山县的几个邻近山村里。
入学之初,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推翻明朝,建立了大顺王朝,成了大顺王朝的皇帝。遗憾的是,这支进城后的农民军过分陶醉于伟大胜利,享乐腐化,不思进取,致使大顺王朝48天便灭亡了。为吸取这一历史教训,郭沫若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在向党内推荐这篇文章时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白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鉴此历史背景,北方局党校决定将《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平剧《李自成进京》,以便增强教育效果。
创作组虽然成立了,但一直拿不出初稿来。副校长赵振华(李葆华)说:“邓拓是历史学家,有才学,让邓拓干吧!”
凭着丰厚的历史知识以及娴熟的写作技巧,邓拓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创作任务。几天工夫,便写出了四幕十五场的大型平剧初稿。经过同志们的锦上添花,剧本总算定稿了。
大部分角色都好定,只是女主角红娘子难定。剧组认为,红娘子武艺高强,多情多义,智勇双全,有胆有识,丁一岚可以胜任,但丁一岚说什么都不干。在邓拓劝说下,丁一岚总算答应了。
经过一段刻苦的排练,《李自成进京》一炮打响,左一场右一场,越演越娴熟,越演越精彩,大伙鼓掌称赞。于是,丁一岚有了个绰号:“党校红娘子”。
邓拓成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人
1944年,为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
刚从党校归来的邓拓一边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一边进行《毛泽东选集》的编选和出版工作。全书按内容分为五卷。平装五册,精装合装一册。800多页,约50万字。
为宣传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邓拓在这年的7月1日和9月26日两次撰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
出版《毛泽东选集》,这是特殊条件下完成的特殊使命,困难重重,邓拓和同事们克难了许多困难。
首先是纸张困难。1943年秋冬,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三个月,在敌人的经济、军事封锁下,报社很难在敌占区买到白纸。邓拓便领着大家自力更生,办起了手工造纸厂,用稻草、麻绳造出了粗糙、发黄的自制纸。他们以这样的自制纸印报,省下白纸印《毛泽东选集》。
其次,印刷封面的难度也很大。为了出精装本《毛泽东选集》,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的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出毛泽东像的铜版。解决了制版难题。书名烫金怎么办?他让印刷二厂领导发动群众搞发明创造。装订股长崔振南想出了好办法: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炭火,把转盘烤热,烫出了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这就是精装合订本的封面。
为了出版这套《毛泽东选集》,邓拓付出了很多心血。除了写按语,加注释等大量的编辑工作,还有一系列出版工作需要他一一落实。担任排印的报社印刷二厂在阜平县坡山小村,这里距编辑部所在地马兰村比较远,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为了避免出版中的差错,邓拓栉风沐雨。有时甚至是披星戴月。出版过程中,他骑着马来回奔波几十趟,搞校对,看版式,克服难题,检查印制质量。
邓拓的工作受到了聂荣臻的高度赞扬。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邓拓同志从1937年到晋察冀边区,一直到1949年进城后,他都是搞报纸、搞宣传。他毕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领导下。他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他为这部选集写了‘编者的话’,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
兰花吐芳,开国大典那天转播历史盛况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中共中央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当日,朱德向各解放区发布了接受投降的进军命令。
消息传来,邓拓连忙组织印发特大号外。报社的同志临时组成了30多人的宣传队伍。他们连夜打着火把,敲锣打鼓,走向村镇和每一个居民点。每到一处。当喧嚣的锣鼓声把村民们召集在一起时,丁一岚便敏捷地站在板凳上。噙着欣喜的泪花。在两支火把的照耀下,逐字逐句地向大家宣读党中央的电文,把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及时传给了老百姓。谁也没想到,这位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女子,在关键时刻吐字这么清晰,情感如此奔放,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实在令人称绝。
有人跟丁一岚开玩笑说:“将来进城接收了电台,你当咱共产党的播音员最合适。”
8月2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晋察冀日报社随军进城,接管了敌伪的报馆和广播电台。
张家口广播电台功率大,具有10万千瓦的短波台。是当时亚洲地区功率较大者,因而成了中共的重要喉舌。电台技术人员可以留用,但播音人员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并且要一改日伪电台那种靡靡腔调。报社副社长胡开明根据群众意见,提出由丁一岚担任电台播音科科长兼播音员。就这样,丁一岚开始了她40年的广播生涯。
广播电台在张家口市西北边,报社则在市东南的山坡上,两地相距较远。邓拓对丁一岚的工作很支持。每天晚上,《晋察冀日报》大样总要打两份,一份报社用。一份送到电台。丁一岚连夜摘出要闻,第二天一大早就开播。早饭后,她得编稿子,选唱片,晚间还得广播,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她只得吃在电台,住在电台,只有星期天才回家住一宿。有时工作一忙。连周末也不能回家。
张家口失守后,电台撤到了阜平县栗园庄的一座小山上。工作条件更为艰苦,没有录音设备,全靠播音员一遍一遍地直接播出。
解放战争后期,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大军即将南下,毛泽东为新华总社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解放区军民准备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这时,丁一岚已经调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因为她的播音风格庄重稳健,领导上决定由她来播出这篇献词。节目播出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广大官兵称赞丁一岚的广播气势恢弘,有股令敌丧胆的震慑力量。有的还风趣地说。丁一岚的播音是“兰花吐芳”。
历史将这朵“兰花”推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性岗位上。1949年10月1日,丁一岚与男播音员齐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转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实况。
比翼鸟在新闻战线上搏击风雨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统一领导下,另行创办《人民日报》。邓拓暂时离开了新闻工作,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秋天,邓拓又被中央领导点将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那时,邓拓住在人民日报社职工宿舍后院的角落里,三间平房几乎见不到阳光。后来,报社腾出了较为宽敞的房子,几次请他搬家,他总是说:“让别的同志住吧!这比农村打游击好得多。我经常上夜班,没有阳光也不要紧。”丁一岚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总算有个安静的窝,知足啦!”
由于邓拓、丁一岚夫妇在新闻和广播事业上的辛勤工作。党和人民信任他们,一系列荣誉和职务便落在了他俩头上。
邓拓除了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还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并以渊博的学识、诸多的著作,被聘为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丁一岚则先后担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副主任等职。
因此,从战争年代过来的知情者都夸他俩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对比翼鸟”。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邓拓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革命信仰的人,不赞成各种情绪化对党的批评。尤其不同意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因此,当地方报纸组织“鸣放”时,《人民日报》却与众不同地在发表批评性的“鸣放”文章前加注了编者按:还对言辞过激的文章予以删节。在对待报社人员的内部“鸣放”问题上,邓拓在作理性分析的同时。提示有关人员要考虑政治后果。
邓拓的举动使很多人避免了成为“右派”分子的厄运。《人民日报》的老编辑左录、刘淑芳夫妇对笔者说:“全国反右扩大化,《人民日报》却没有一个‘右派’。多亏邓拓同志的严厉批评呀!当时,有的同志对他有意见,真相大白后便感激他。他为别人化解了灾难,却给自己带来了冷遇和中央领导的斥责。这样的好领导。令人钦佩!”
在毛泽东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没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批评道:“邓拓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听了,无言以对,九鼎压身。回到家里,他心情沉闷,好似得了一场大病。
丁一岚问邓拓发生了什么事。邓拓不愿给妻子带来压力,只说毛主席批评了他。但对毛泽东批评时所用的严厉词语只字未提。
1958年8月。邓拓离开了人民日报社,到中共北京市委任文教书记,主管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前线》。
人民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为邓拓举行了欢送会。邓拓在会上作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仍觉言犹未尽,便朗读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以表达内心的感慨: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丁一岚也遇到了无法摆脱的麻烦。195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组织开展形势讨论会。丁一岚对“大跃进”表示疑虑,作了一番发言。没想到,她的发言,被打成了反党“右倾”言论。经过一番思想批判,她被送到河北省遵化县穷棒子公社劳动一年,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两颗璀璨的明珠
1961年,《北京晚报》副主编顾行和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刘孟洪约邓拓开辟一个专栏,请求供稿。邓拓经过慎重考虑后表示同意,决定专栏的名字叫《燕山夜话》,笔名用“马南邨”。他解释说:“燕山,是北京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邮是马兰村的谐音,这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的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
从此,每星期二、四的《燕山夜话》栏内都有署名马南邮的文章。
从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的一年半中,邓拓写了154篇文章。每周两期,他风雨无阻,准时供稿,从不误时,基本上是晚上写,早晨交稿。只有两次例外: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外出视察,晚上有事不能写,第二天便抽空补上,然后航邮报社。
在那个年代,丁一岚总在担心“授人以柄”。焦虑之中,她似乎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就要来临。因此,这位往日的“挺笔夫人”却泼起了冷水,劝邓拓少写。别累着。
邓拓讲:“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给《北京晚报》的同志写了一副对联:‘深入实际兼读史。立定脚跟做圣人’。我说的圣人。就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意思。要做马列主义的圣人,必须立定脚跟,要敢于坚持原理。不做人云亦云、随风飘荡的氢气球。而要做到立定脚跟,就必须深入实际,认真读书。只有扎根实际和人民之中,才能够不动摇。”
邓拓的杂文在《北京晚报》上刊登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出版社将文章汇集成册,这便成了33万字的杂文集《燕山夜话》。此书一版再版,行销百万册,深受读者欢迎。
《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北京晚报》的群众威信则大为提高。《前线》编辑部受到启发,也向邓拓提出了类似的组稿要求。邓拓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但又觉得一个人不能胜任。便约请北京市负责文教的副市长吴啥和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都是专家、学者,都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商定,三人同用一个笔名:吴南星。“吴”即吴晗;“南”即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即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这个栏目是邓拓提议的。他说:“听说‘马铁丁’是三个人使用的笔名,我们也三人,干脆,就叫《三家村札记》吧!”
其实,邓拓心中的“三家村”还有另一含义: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时,他带着报社全体人员躲进仅有三户人家的日卜村,15天出了12期报纸,创下了办报史上的奇迹。后来谈起此事,报社的许多同志都把日卜村称做“三家村”,以表达对那三户村民的怀念。
由邓拓创作和参与创作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成为中国杂文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刊登了57篇文章,未来得及成集出书便受到了“文革”批判。
邓拓之死,“文革”中被迫自杀的第一个名人
读者也许会问,《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既然是中国杂文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作者以心血浇灌的两朵花,怎么成了置邓拓于死地的两发“重型炮弹”呢?
事情得从头说起。1960年,吴晗写了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授意下,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攻击《海瑞罢官》在“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还说吴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毛泽东说过:“《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接着全国大小报刊开始批判吴晗及其剧作《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
彭真及北京市委迫于压力,不得不对吴晗和《海瑞罢官》表示批判的立场,就让邓拓写批判文章。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历史研究和道德继承的学术观念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江青等人看后很不满意,便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接指向北京市委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有人提供了消息:邓拓、吴晗、廖沫沙同是《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于是,他们三人被打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被诬为“反党育论”、“反革命罪行”。一时间,全国大小报刊出现了千篇一律的批判文章。城市和乡村,到处出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摧毁三家村黑店”、“打倒黑帮邓拓、吴晗、廖沫沙”等标语口号。
在这样的大批判氛围中,邓拓感到莫名的委屈和悲哀。随着大批判的深入进行,邓拓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家中的书房里,忧心如焚。丁一岚在外面参加“四清”运动,难得回家。
两个月后,“四清”运动搞不下去了。丁一岚回到原岗位,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与邓拓划清界限,揭发问题。丁一岚很清楚,邓拓不可能反党,要说有错,顶多就是那些文章惹了麻烦。因此。对于组织上对邓拓的审查和教育,她的态度是:“相信群众相信党。”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邓拓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966年5月16日,这是“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并生效的日子。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指名道姓地说,邓拓是叛徒,《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是他伪装积极骗取的。还说“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谁在背后支持他,要一追到底”。
邓拓是部级干部,家里有两名警卫员。自从报上批判“三家村”以来,他就被监视,两名警卫员成了看守员。丁一岚守纪律,不跟警卫员打招呼,绝不越雷池一步。邓拓的姐姐邓淑彬帮助操持家务。当着警卫员的面,她可以给弟弟端茶送饭等。5月17日,她照旧进去送开水,邓拓对她说:“我是冤沉大海呀!”
17日晚上,邓拓沉郁异常。他提笔向北京市委写完了一封7000多字的遗书。
第二天清晨,丁一岚没有听到邓拓那习惯性的清咳,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不顾一切地闯进邓拓的卧室,推门一看,邓拓竟躺在地上。
丁一岚的心一下子碎了,她的眼泪像决堤的河水奔涌而出,可她不能大声哭泣。她只能用毛巾堵住嘴哽咽着。邓拓给丁一岚留下了一份遗书:一岚: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自杀的第一个名人。当时的北京市委派人向丁一岚宣布纪律:不准走漏消息,要绝对保密!接着,随便给安了个名字,拉到北京东郊火葬场一烧了之。
为邓拓送葬的那天,风雨交加。没有花圈哀乐,没有送葬的人群,除了组织上指定的两个人,加上丁一岚,以及邓拓的姐姐邓淑彬、哥哥邓淑群,其他人概不知晓。
邓拓自杀之后,丁一岚被当做“三家村黑店的老板娘”多次批斗。后来,丁一岚先后到北京远郊房山-农场劳动改造,继而又进河南淮阳干校劳动。
“朝晖起处,即我在也。”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作出了《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9月5日下午,胡耀邦主持了邓拓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彭真、薄一波、姚依林等参加了追悼会。
邓拓平反之后,丁一岚担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无论工作多忙,她总要抽出时间参加有关邓拓的诗会、笔会、研讨会、座谈会等。1986年,她65岁,离休了。丁一岚先后筹划编辑出版了《邓拓文集》、《邓拓诗词墨迹选》、《邓拓诗集》等,并参与、促成了《邓拓传》、《晋察冀日报史》的编写出版工作,还完成了《人民新闻家——邓拓》的撰写并使之问世。
丁一岚还向笔者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邓拓与丁一岚结婚后,就把聂荣臻讲过的“刑场上的婚礼”讲给身边人听。有位很有才华的诗人兼编辑、记者,名叫司马军城,他听了这个故事大为震撼。激动之下,他写了篇长诗《绞架下的婚礼》,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歌颂刑场婚礼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1942年冬,司马军城被派往冀东《救国报》工作,并担任《新长城》杂志主编。临别时,邓拓为他赠诗送行:“山中学道飘青鬃,火里抟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成纛日边明。”
到达冀东后,司马军城在滦水边向西遥望太行深处,满怀激情地给邓拓写信说:“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
1943年4月,司马军城在丰润县白官屯附近的采访中被敌人包围而中弹牺牲,时年24岁。噩耗传来,邓拓展阅司马军城的来信,夜不能寐,含泪写了一首挽诗: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三家村”平反之后,丁一岚写了一篇文章《忆邓拓》,发表于1979年2月的《新闻战线》。文章介绍了《祭军城》挽诗的由来,并且说:“老邓,你可知道,多年以后,我们却以你祭军城的诗来祭你,你为战友写的祭诗竟不幸成了你的自祭。三十六年前,你又怎能想到后来会有这样一天呢?”
湖北利川县咸丰陶瓷厂工人胡祥华看到丁一岚的这篇《忆邓拓》后,参阅了其他几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得出一个结论:这位司马军城亦即顾宁。也就是他们利川县汪营镇的牟伦扬。
胡祥华在1982年2月3日《恩施报》上发表了《利川诗人司马军城》,向故乡人民介绍了这位不为人知的历史入物。
牟伦扬的胞妹牟晓云看到了这篇文章后,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哥呀,你怎现在才有消息呢?说你是台湾特务呀!一家人背黑锅。几十年啦。好惨呀!”
几天后,丁一岚接到了司马军城的胞弟牟伦兴、胞妹牟晓云、外甥女周雅琼的来信。这才知道,这么多年来,烈士司马军城的家人竟被以“台属”、“特嫌”对待。牟伦扬的父母戴着“地主分子”和“特嫌家属”的帽子,含冤而去:弟弟妹妹及直系亲属坐牢的坐牢,免职的免职,加上其他形式的迫害,冤情一言难尽!
看着烈士亲人的来信。丁一岚哭了,她立刻联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湖北日报》总编辑雷行、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周明等十多位《晋察冀日报》的老战友,他们以自己的证言以及保存多年的烈士照片为证,为烈士家庭正了名。
讲完这个故事,丁一岚叹息道:“司马军城牺牲后,我脑子里经常响起他的声音:‘朝晖起处,即我在也。’邓拓去世后,每当我看到日出,又总觉得邓拓在复述这句话,印象很深,赶也赶不走!”
1998年9月16日,丁一岚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