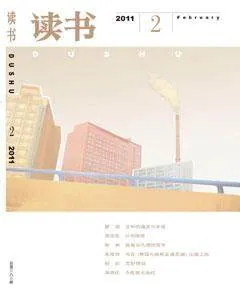为什么要重谈陈查理
一九二五年,四十一岁的厄尔·德·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以侦探陈查理为主角的小说。在此之前,这个美国俄亥俄州小报记者的运气一直不好。虽然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他第一份在《克利夫兰平原报》的工作没干多久就被炒鱿鱼了,编辑认为他喜欢把虚构的东西羼入新闻报道中,可能更适合去写小说。此后比格斯又陆续从事过手稿审读人、戏剧评论员等工作,也写了一些受好评的侦探小说,但对美国文化界都影响不大,直到一九二四年在纽约市立图书馆时偶然看到夏威夷警察张阿平(Chang Apana)打击鸦片走私的新闻,并且由此触发灵感创造出美国大众文化中最著名的华人形象之一 —— 陈查理。
陈查理是个彬彬有礼、年过不惑的胖墩,说着蹩脚的英语,时不时冒出一两句孔子式的格言警句,颟顸又可爱。这个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正面华人形象一经创作出来就很受欢迎,相继出现以他为主角的小说六部,电影更是将近五十部。一九三一年福克斯公司的《陈查理续集》(Charlie Chan Carries On)大获成功,使之成为美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陈查理电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引入中国后也同样广受好评,连鲁迅和许广平也经常去上海各影院观赏这些电影。饰演陈的原籍瑞典的演员威尔纳·欧兰(Warner Oland)在一九三六年访问中国时,当地报纸的标题是《中国大侦探到达上海》。
陈查理作为经久不衰的大众文化形象,在晚近学术界却不那么受欢迎,他被视为东方主义的一个显影:和罪恶博士傅满洲一样,他不过是刻板化华人的另一面。许多用心良苦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便力主将陈查理从美国通俗文化中清除出去。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二三十年来陈查理逐渐从大众文化中销声匿迹,成为一种准“政治正确”的文化禁忌的原因。
不过,最近华裔学者黄运特的著作《神探陈查理不为人知的故事》(Charlie Cha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Honorable Detective and His Rendezvous with American History)却提供了重新理解陈查理的可能性。这本二○一○年八月出版的新书,短短几个月便再版四次,《纽约时报》、《纽约书评》、NPR电台等重要媒体都做了专门报道,黄运特也因此在全美各地不断巡回讲演,成为近期美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黄运特糅合侦探小说和主流文化历史的笔法,勾勒陈查理的前世今生,探讨移民历史,文字灵动,议论风生,触动了许多在“二战”前后长大的美国观众的怀旧心理。然而,重谈陈查理并不在于迎合怀旧之情。这本书对于我们反思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在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国学术界的规范,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而美国主流媒体对该书的众多评论却较少触及这些方面,很值得细细梳理一番。黄运特在中国长大,大学毕业才到美国打拼,能在当代美国大众中引起如此反响,说明了中国赴美的新移民在族裔和文化问题上的独特视角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吊诡的是,陈查理在好莱坞走红的时候也正是美国排华排外的移民立法达到高峰的时候。一九二四年著名的约翰逊—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对亚洲所有地区的移民都加以禁止。华人早在一八八二年就被排华法案挡在美国门外,一九二四年的法令将排华时期延续至一九四三年。美国法律对华人及其他亚裔人的排斥反映的是白人对自己经济文化地位的一种焦虑。但这种拒斥却与陈查理的走红并行不悖,一般对这个矛盾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陈查理这样比较驯顺勤恳的华裔形象其实是美国文化对其内部的非白人族群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移民限制并不能改变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社群已经在美国国内生根立足的事实,因此将少数群体的某些成分进行美化,既能控制其对白人的反抗情绪,也能借此遮盖美国深刻的种族主义矛盾。而且,将亚裔刻画为已经在美国社会证明了自己价值的一群人也婉转地起到了为美国社会制度开脱的作用,无形中将某些不太“成功”的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人,所面对的贫穷、犯罪率高等问题归结为种族素质的原因。另一种说法是从后殖民理论中推演出来,认为白人对少数族裔的感情里同时具有排斥和将其同化的欲望,而这里的同化又不是完全的接纳,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容忍。按这种说法,排斥和有限接纳的矛盾两方分别体现在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两个人物形象中。傅满洲是“黄祸”理论的化身,而陈查理则是“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这两种解释方法都无疑具有其正确性,其共同点就是将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的仇视和推崇看成是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认为跨种族的友爱不是超越于种族主义之上的,反而只是对种族间互相恐惧和疏离的一种变相的遮盖或体现。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种族主义有两张面孔,一张是憎恨恐惧,一张是有条件的爱。
以上这些分析近二十多年来在美国学界一直比较流行,也已经被不少中国研究美国文学的同人所沿用。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并不太令人满意。根据这些理论的逻辑,陈查理仅仅是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冷战初期自我定位的一种需要,是美国各民族和谐神话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但是,美国观众对陈查理的喜爱真的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伪善吗?而身为作者的黄运特本身就是陈查理迷,难道就因此成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典范?我本人第一次看陈查理的电影也是在美国读博的时候,记得当时从Netflix(一个租借网站)借来一部Sidney Toler主演的《陈查理在情报局》(Charlie Chan in The Secret Service),一看便着迷了,忍不住随着剧情起伏和陈查理的连珠妙语而笑个不停。这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