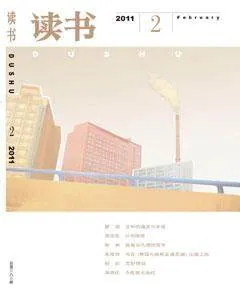想象性地域及其诗意表述
游走于中德之间,肖开愚不得不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自己的居所和作客之地),在故乡、家庭、心灵的园圃和逗留的每一座城市之间做出抉择。他内心的地图在不断地收缩和膨胀,超越了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与西方,在欧亚大陆的版图上画下了许多私人的秘密通道。
途经干燥的甘肃,枯竭的新疆,
茫茫的巴基斯坦,越过沙漠和高原,
横穿风俗怪诞的袖珍国家
去印度,四个人一匹马,远着哪!
——《传奇诗》
与唐僧师徒比起来,肖开愚要幸运得多,现代交通工具削弱了行程的艰辛程度。但他的幸运仅止于此,精神层面上的焦虑不仅没有随着这种艰难程度的减轻而有所缓解,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从表面上来看,肖开愚显得非常轻松,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在两个不同文化的国度扮演着交流者的角色。他接受凌越的邀请,为《书城》撰写《德国书简》,各种访谈、随笔,他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德国的生活。在一切的平静和如意之后,他强烈地感受着自己的身份——客人。
在肖开愚一九九八至二○○○年所创作的诗中,地域是一个关键词,柏林、北京、南京、易北河畔、法兰克福、布莱希特故居⋯⋯构成了一个地域的谱系,尽管没有毕肖普那种强烈的漂泊之感,肖开愚也是地理的俘虏。当然,如果想从诗歌来偷窥一段诗人的私事,那多半是要让自己失望了,一个地点往往是肖开愚诗歌的支点,但我们却找不到那个推动诗歌之球的杠杆,肖开愚的智性写作方式决定了他的诗歌只能是片断式的、恍惚迷离、声东击西,让人无从下手。也许肖开愚的诗歌并没有能力还原事实的真相,充其量它们也只是一个场景一瞬间的静态表演,或者一种情绪的诗意表露,你无从着手窥测整个事件的流程。对于肖开愚来说,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写作,它不是日记和化验报告,它总爱在事实之上施展修辞的魔术,使得一切都变成一场文学游戏。尽管如此,即便最优秀的罪犯也会留下一些有力的罪证:
六公里的不忍到了小火车站,
逆风从东方吹来一场眼泪。
——《送黄卉回柏林家中》
让我的大国把波兰遣散到我的皮肤和脸
——《aus Polska》
当我独自回到四川,我感到
只有灰色——飞机轰地起飞——帮助我领会
而且我像我感觉到:回到了丛林。
——《安静,安静》
引文中弥漫着一种隐隐的失望情绪。“东方”既可以看做是实指,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在《aus Polska》一诗中,(他有很多诗以德文作为标题,是为了表示这种德国脑袋、中国身子的杂交动物在文学生理上也能够成立?)肖开愚将自己假想为一名德国人,却在祈求为自己找一张波兰人的皮肤和脸,这种矛盾性来自于身份错乱的焦虑,一种无法证明自己的破罐子破摔法——“你们说我从波兰来/我就从波兰来。”而在《安静,安静》中,当诗人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他忽然发觉这种回归已毫无意义,四川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处丛林,回到家乡的喜悦感为极度灰色的心理所取代了。
这些情绪没有掩埋在文字的废墟里,肖开愚既被那些城市所容纳,又被它们隔离,时刻承受着即将被抛弃的不祥之感。
这就是你对死亡的解释:近但是隔离。
——《布莱希特故居留言》
布莱希特的死亡之所以让肖开愚有所触动,也许有其生理学上的意义,但从诗歌本身来看,死亡反而显得遥远、虚无,一种空间的隔离感被提上议事日程。建筑物的隔离效果有其局限性,作为一个城市的缩影,我们不妨将其放大,将个人的生死演变为一个族群共同的命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将这句诗改写为:“这就是你对城市的解释:近但是隔离。”一个旅人是无所谓家的,他面对城市集中营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其等同于家,等同于自己心灵的栖息之所,但是这种等同终究要大打折扣。于是它们全都长出了新鲜的骨刺,在他的身体内部四面开花。这种灼痛感无处不在——肖开愚将其表述为柏林之刺,被大祸临头感所笼罩的北京、废墟般的旅馆以及转机过程中的无所事事,都在诉说着生命中的另一片荒凉。
摩托车乱叫着驶向那些废墟。
可这儿,揪心的
——《品达罗斯旅馆》
我只是到这里来转机。
有几个小时,四处逛一逛,遇到什么咖啡馆
就在什么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如此而已。
——《法兰克福一日·留言》
转机不过意味着旅程的中途休息,它何尝不是人生的缩写?旅馆至少可以提供一张安然入眠的床,而转机匆匆的特性决定了最合适的地点是咖啡馆,一个提神、让神经进一步紧张而不是放松心情的场所。相对于旅馆,转机是更大的冒险,前方总有危险和希冀,在等待着我们。就像是一次赌博,我们压下了全部的家当,有可能赚得盆满钵满,也有可能血本无归,而后者显然占据了更大的可能性。此时,横亘在肖开愚面前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岔口,两条出路,一条通往丧家之痛,一条通往多种选择的迷惘,回是回不去了,但向前又能走向何处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似乎选任何一个都意味着你必须丧失许多你的至爱而又无可奈何。
从这个角度来看,旅馆是转机的延长,它们的性质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即使在旅馆中,一个旅人也无法实施他在家中所能够享受的待遇。
即令在这些消过毒的房间里
肉体也不再寻呼谁。
——《品达罗斯旅馆》
在旅馆中,旅客被完全地孤立了起来,仿佛天地之间一沙鸥。肉体丧失了寻呼的权利,并不表示它也放弃了这样的希望,即与另一个地点或者人物建立联系的渴求。至少在它取消了自己这些权利之前,它还心存侥幸,幻想着摆脱固定的束缚,这是肉体的乌托邦吗?经过时间的洗礼,肖开愚的身体中已经撒下了太多黑色的种子(他的文字游戏有时不免有掩饰内心真实感受之嫌),并且随着种种生活中的障碍而生根发芽。但这种黑色绝不仅仅是虚弱的象征,它也是肯定的条件,在形塑着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正如我们所读到的,肖开愚的写作不合常规,以一种跳跃的姿势,他戏耍着语言,也任由语言带领他到一片全新的诗境之中。日常生活成了神话般的旅行,它们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诗歌的复兴之路,因为它们是肖开愚诗歌的基石,一种极度个人化的阅历和经验在激发着他的灵感,告诉他是应该去扮演一个政治上的逃亡者,还是一个诗歌意义上的流浪汉。
的确,作为一个海外的客人,他无法抛弃自己的面孔、皮肤、母语思维的惯性,当他成为一个德国人的努力被证明是不可能之时,他倾向于强化自己的中国身份,来抵制德国文化对他的腐蚀。古典,一个早就被“五四”以来所抛弃的词语现在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它很具有标识性,它是一种可以迅速被指认的符号。肖开愚晚近的诗作几乎清一色都加入了古典的调料。同时,他又坚守着这一诗歌道德的底线:诗歌是对公共话语的反驳。尽管他那样推崇着盛唐,但从他的写作来看,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出任古诗说教者的职务,古典对于他是表述的手段之一,是抵抗当下社会现状的有力武器,却并非核心。我在他的诗歌中读到的,仍然是精神困境的写照。从精神质地上来说,肖开愚与陈东东骨子里的那种六朝之气有着天壤之别,肖开愚的诗风硬朗、多变,行文多有出人意料之处,说它是语言游戏也好(周伟驰持这种看法),说它是“诗人劳神之后的疲惫状”也罢(席亚兵的看法),究其实质,文字层面上的配对,指向了生活的隐秘之处,是生活隐痛的诗意表述。
鸟之疾疾!因为完美而残缺。
鱼之多刺!水为完美而沉闷。
噫!理想国里无心情。
——《人如何谦逊的生活》
(《肖开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四年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