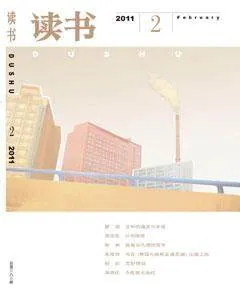荒野情结
《寻归荒野》是十几年前我写的第一部介绍评述美国自然文学的书。当时采用这个书名,出自于我对荒野的领悟。“荒野”是自然文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对荒野的理解堪称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精华。自从我于一九九五年涉足自然文学领域之后,所倾心研读与研究的几乎都与荒野有关。多年的研究与经历使我感到,荒野不仅是实体的自然,也是自然的心境,或心境中的自然。“寻归荒野”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词的简单组合。“寻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走向自然,更不是回到原始自然的状态,而是去寻求自然的造化,让心灵归属于一种像群山、大地、沙漠那般沉静而拥有定力的状态。在浮躁不安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能够从自然界中找回这种定力。
接触自然文学以来,我目睹了“自然文学”从鲜为人知到眼下颇有些热闹的场面。在自然文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延伸出“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及“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从自然文学中原有的“地域感”(sense of place),又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全球感”(sense of planet)。比如,美国学者海斯(Ursula K.Heise)二○○八年的新著就题为《地域感与全球感》(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我本人仅从翻译的角度,也感受到这个领域在国内的升温。多年前与三联书店拟定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四本原著中的一本,只因动手稍晚了一点,国内就出现了两个中译本。“环境文学”及“生态批评”无疑为喜爱“自然文学”的人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但是我依然愿意守候在我最初喜爱的自然文学这一小片文学的园地,如同一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书名《扎根脚下》(Staying Put),并且深深地挖掘。记得在一本描述美国新英格兰文学风景的书中曾看到亨利·詹姆斯的一句话:“人们需要长长的历史才能产生出小小的一脉文学。”
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不同于西方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它是源于十七世纪,奠基于十九世纪,形成于当代的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虽然美国自然文学在传统上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是鉴于它产生于以“伊甸园”与“新大陆”而闻名于世的美国,便自然有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能有的特性:从一开始,它就注定是一首“土地的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在其著作《处女地》中指出:“能对美利坚帝国的特征下定义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影响,不是某个文化传统,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而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从形式上来看,自然文学属于非小说的散文体,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也有人形象地将它称作:“集个人的情感和对自然的观察为一身的美国荒野文学。”因此,在阅读自然文学作品时,犹如亲历其境,令人感受到荒野在闪烁。
自然文学主要特征有三:一、土地伦理的形成。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