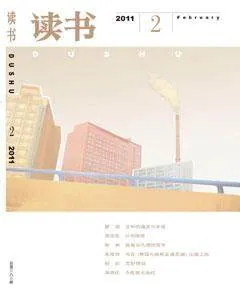公司制度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
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这句话也适用于公司。在我看来,公司制度就是可以“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
要知道公司的力量,就必须了解公司的历史。十几年前我常向学生们提这样一个问题:先有工业革命还是先有公司制度?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工业革命在先,然后才有公司制度。这种误解的出现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国长期没有“公司制度”而有的只是国营的“工厂制度”,对公司制度比较生疏。尽管现在人们对公司再熟悉不过了,甚至产生了相反的现象,即人们只知道“公司”而不知道“工厂”。然而大多数人对公司的了解不过是高大的写字楼、整齐的厂房和设备,以及人们名片上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名衔,可谓一知半解,不甚了了。而《公司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对公司的本质解读和深度透视。
公司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企业制度。公司作为一种企业组织,早在工业革命前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如果追溯以往,在古罗马时代就有“公司”的雏形。中世纪晚期,较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往往是由商队或商船完成的。大家将资金集中起来购买一批货物,选举一个队长或船长来掌管这次商业旅行。当这次商业旅行完成时,大家分享盈亏,作为商业组织的商队或商船的使命也就此完结。这里,临时组成的商队或商船,都是一个“公司”组织,这里的队长或船长就是今天“总经理”的前身。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作为“公司”雏形的各种商业组织已经是遍地开花了。
不过,真正的公司组织还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的。最早的规范性公司组织是一六○○年在英国出现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获得经营东印度贸易的特许权,经营得非常成功。随后,其他欧洲各国都建立了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或西印度公司,经营新航线的贸易,并且大都很成功。由此,东西方贸易以及新旧大陆贸易成为西方人发财致富的“金矿”,并由此引起长达数百年的商业大潮。这场商业大潮将中世纪封建残余涤荡得一干二净,从而促使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在工业革命初期,大多数工业企业都是业主式企业,资本家创办一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初期的机器技术并不复杂,所需的固定资产规模还很小。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使用的扩大,特别是蒸汽机大规模使用后,固定资产规模大大扩大了。这样,单个资本就不能适应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股份公司制度就被引入工业制造业。当股份公司制度进入工业制造业以后,资本规模又进一步扩大了,技术进步进一步加快了,出现了大型企业和资本集中现象,从而造成了垄断。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福特、铁路大王斯坦福等。这些“大王”们,既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代表,也是工业化的助推者。正是这样,公司制度作为一个支点,“撬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大潮。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公司最初目的是集中资源和分散风险。所以,早期的公司组织主要出现在资金规模巨大和风险较高的行业中。如海外贸易公司、开凿运河或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我们很难设想,没有公司制度我们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规模的资金,筹集到大规模的资源,来进行各种大规模的开发事业,如开发大型的矿山,建立大型的水电站,进行尖端的科技创新等等。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有限责任制度。最初的公司企业实行无限责任。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对企业负有完全的责任,这能令投资者更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往往直接经营管理。但这种制度使投资者必须承担完全的风险,也就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所以后来发明了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投资热情,但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亚当·斯密就是反对者之一。他认为有限责任制度下人们只负有限责任,这种制度本身就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最终还是有限责任成为主要的公司制度。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有限责任”也能“负责任”地承担,因此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及不上它所带来的收益。
公司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秘密,即匿名股东制度。今天,大的上市公司可能有千千万万的股东,没有人能说出他们具体是谁,我们也不能知道谁拥有了哪个公司的股票。这就是无记名股票。事实上这个制度也源于古罗马。当时的法律不允许元老院贵族投资企业,但是元老院贵族们又不希望手里的金币仅仅作为储藏手段,他们往往悄悄地将这些钱投资入股,成为“匿名股东”。后来出现的公司股票往往不记名,并且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公司也往往“认票不认人”。这种制度保护了投资者,有利于鼓励人们的投资热情,也有利于资本的流动。
在英国,最早的股票买卖大多是在一条街上的咖啡馆里进行的,以后这条街就发展为股票交易所。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家经营南美洲海岸贸易的公司——南海公司。这家公司很有来头,不仅有不少身份显赫的“匿名股东”,还取得整理国债的特权。因而它的股票价格一度飙升。当时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热潮,不仅投资家和投机者、贵族和国王、军人和百姓,甚至科学家牛顿也禁不住诱惑加入“股民”的队伍。为了获得股价攀升的好处,许多投机家创办了不少子虚乌有的“泡沫公司”。为了打击这些“泡沫公司”,南海公司鼓动政府颁布了“泡沫条例”。这就导致股市泡沫的破裂,于是股价大跌,南海公司也被殃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事实上,在股份公司制度和股票交易所制度下,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用少量的资本调动更大规模的资源,使资本“放大”,达到“撬动”庞大资本市场的效用。近代以来资本市场的发展,直到现代衍生工具的发展,都是这种“支点”和“杠杆”的“撬动”作用。目前,这个资本市场上,每天都有数以万亿计的规模实现着资本流动,在健康的情况下,这种“虚拟”资本市场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虚拟资本的发展,往往一发而不可收,数倍地超过实体经济,最后不得不“缩水”。
公司有没有国籍?这在过去根本不是问题,也没人去想。公司作为资本的载体,执行资本的职能,必定会走向世界。从最早创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直到存续数百年的英荷“壳牌”,无不在全球各地拥有“分店”。它们所获得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回本土。大英帝国在制造业和进出口衰落以后,如果没有海外公司流回国内的利润,早就无法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了。甚至通过这种海外公司的高额利润,英国出现了一大批食利者。所以,所有的公司包括海外公司都是有国籍的。
然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在这一大潮中跨国公司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全球五百强的公司,无不是跨国经营的公司。它们在全球各地经营,用的是当地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有的公司连技术开发中心甚至管理中心也都“本地化”了,有的公司将所获得的利润也留在本地。这样的跨国公司还有国籍吗?这是近些年来引起人们争论的一个新话题。
有的人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使企业活动超出了国界,成为全球性企业或国际性企业。这种公司无所谓“国籍”。然而,当公司利益与当地利益发生矛盾时,当公司的“祖国”与所在国发生矛盾时,公司的“国籍”问题马上就出现了。经常出现的“国货”运动和冲击外国公司的过激行为,反映了人们对公司“国籍”问题的观念和倾向。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跨国公司也往往求助于“祖国”的保护,理所当然地他们也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随行的往往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司代表团,可能是“采购团”、“推销团”,也可能是“银行团”,或许还有大军火商。就在几年前,当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并购企业时,说他们的公司是全球性公司,我们也跟着说跨国公司不存在国籍,只有卖了才能体现开放和“国际化”。但是当我国的公司到他国去并购企业时,他们的政府却大力阻挠,甚至要到国会去辩论。事实上,公司的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也就是公司利益。谁还能说公司没有国籍呢?所以说,公司“撬动”了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公司也是国家利益板块发生摩擦和碰撞的动因。
对于中国来说,严格意义上的公司制度是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被推翻,民国政府建立以后,出现了创办公司的热潮。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影响,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一直发展缓慢。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公司制度基本上不存在,“国营工厂”是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所以说,真正的公司制度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
不过,我国的公司制度一旦出现,就以极高的速度发展。不仅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成为公司,民营资本更创办了大量的公司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巨型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这些巨型公司动辄利润数千亿,当然亏损起来也不得了。民营企业很多是从“小”做起,甚至从“作坊”做起。他们成长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市场经济中,要迅速成长起来有时也很容易。所以,这些年来他们创造了不少公司成长的“神话”。我们注意到一个与富豪榜有关的现象,上了富豪榜的往往上不了慈善榜,而上了慈善榜的,在富豪榜上却没有名。这不禁让人们发出“为富不仁”的感叹。公司的力量不应仅仅体现在公司的利润和成长上,还应体现在为社会的贡献上。这几年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司富豪们也在反省自己。
在中国,公司是以“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得以发展的。这种企业制度,既然直接冠以“现代”一词,就意味着可以跨越数百年的发展史,以最快的速度与西方比肩,甚至超过它们。中国的公司制度,作为支点,“撬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也“撬动”了中国与世界的格局变化。二○○五年中海油斥资一百八十五亿美元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尤尼科;二○一○年中国吉利控股集团以十八亿美元收购福特公司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最新的消息:中国GDP连续两个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相信这一系列事件远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