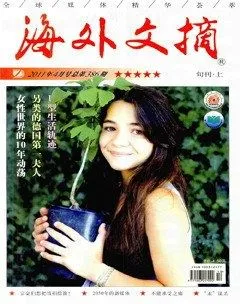重围下的卡拉什人
克什米尔山区距吉德拉尔有两日的步行距离,是美国头号要犯本拉登的藏匿之处,也是一群其乐融融、癫狂无边的异教徒的故乡。对于穆斯林人来说,这山区一隅如同伊斯兰世界里一道久治不愈的伤疤,无论多么顽固,他们也要将这些异教徒拿下。穆斯林称这群异教徒为“卡菲尔”(不忠诚之人),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是早期印欧人中的一支,而他们则自称为卡拉什人。
卡拉什人平生只有一个愿望:与世无争,保卫信仰。每当夜幕降临,阳光沿着山坡渐渐退去,只有兴都库什的山峰依然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闪着点点金光。山的那边,火光为昏黑的夜幕凿了一个闪亮的洞,卡拉什人正围着火堆翩翩起舞。究竟是什么让这夜色如此明亮,是火苗,是女孩子们洁白的牙齿,还是她们飞舞的裙摆?散落在山脊的村庄与连绵的山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高海拔的山谷里几乎是没有牧场的,草料不知被哪个游手好闲的大力神扔到了山的那边,村民们只能把远途拾回的稻草积攒下来,用作房屋的保暖层。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要蜷起身子抵御冬日的严寒。
卡拉什人生活在山坡之上,在他们的诠释下,世界变成一座巨大而神秘的阶梯。高山本身就是一座阶梯,卡拉什人又把这天然的梯层一一对应给女人或男人。山的顶端是高山牧场,是上天赐予圣人和羊群的无瑕世界,只有男人才可以在此追逐猎物:谷底生活着女人、奶牛和不洁之物,这个污浊的世界充满了繁重的农耕活动;两个世界之间是森林,上天的旨意借助于天然的地质层呈现,卡拉什人的生活也顺着这自然的规律而展开。
每逢查莫斯节(也就是冬至节),各种仪式纷至沓来。人们总能在卡拉什人跳跃、舞动的姿势中感受到超自然的力量,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牲畜、人类、神灵可以畅通交流的上古时代。燃烧的刺柏冒着呛人的烟气,人们将祭祀山羊的血泼向墙壁以驱除邪气。那边,男人将自己涂得浑身是红,来证明他们归属于集体;这边,女人们把刻有雕像的面包扔进火堆,焰火将其送往天堂,供神灵任意享用。严寒之中,人却犹如花丛,到处都是节日的盛装。卡拉什人的欢声笑语在山谷中静静地荡漾,和着宇宙的节拍,挣脱了世俗岁月的摆布。因为大部分卡拉什人都是金头发、蓝眼睛,所以他们会被一些旅行家误以为是亚历山大远征军的后代。时至今日,不少希腊人依旧相信可以在卡拉什人的神庙里找到关于雅典娜和德墨忒尔的痕迹,并且坚持要在这雪域高原之上一探究竟。
印欧人种研究专家们会通过语言、宗教和社会结构来鉴定某一人群为何种民族。卡拉什人讲迭尔德语,是吠陀语的一支,属于印度——雅利安语系,而印度——雅利安语又是南亚印欧语系的最末端。卡拉什人应该是在公元前从阿富汗迁徒到克什米尔地区的,然后借助于连绵的山峦和兴都库什山脉的隘口躲过了伊斯兰教的扩张。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得到一块易守难攻的土地更有利的呢?地理位置就是抗击历史最有利的屏障。千百年来,卡拉什人生活在比里尔、鲁姆布尔和邦布列特山谷里,借助于这天然的屏障繁衍生息。山谷中被细心耕种出的农田是卡拉什城堡的主塔,山坡是维护主塔的城墙,而冰冻的山口则是进入城堡的吊桥。几个世纪过去了,山中隐居的人们依旧存在,时间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无论是他们的仪式、习俗,还是身体特征。
然而千百年来,卡拉什人历经衰落,土地被剥夺,宗教被践踏,政策遭歧视,卡拉什人无力反抗。他们又能怎样?据人类学家估计,现存的卡拉什人已不足4000。尽管伊斯兰堡有保护少数民族的朦胧愿望,宗教征服依旧不可避免。卡拉什人的天空下,清真寺越来越多,皈依者越来越多,卡拉什的最后一位萨满法师也金盆洗手。掠夺让人们麻木了,葬礼上再也看不到兴都库什的异教徒们用木头雕刻逝去亲人的画像,在卡拉什人的传统节日上看到巴基斯坦来的旅行团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在这儿,旅行者们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从卡拉什人的节目中找到乐子,还能评头论足嘲讽一番。世界速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各民族的肖像,在穆斯林重围中的卡拉什人,依然挺立着单薄的身影向真主安拉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