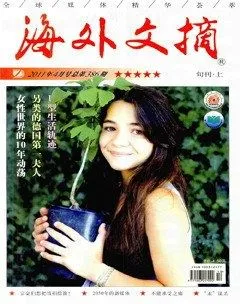新兴国际精英的独立王国
美国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曾言“富人与你我皆不相同”。而在当今世界,此时的超级富豪又和彼时的富人大相径庭,他们更加刻苦耐劳,更具有精英特色。作为一名商报记者,过去10年里笔者都在采访报道新富阶层,出入诸如欧洲私密会议、马萨诸塞州度假胜地以及硅谷会馆等各种高端场所,其间感受最为深刻的是,诚如菲茨杰拉德所言,富人确实与你我不同。
高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催生了新生代超级精英阶层,这些人勤勉刻苦,都受过高等教育,自诩是世界经济浪潮残酷竞争的胜者,手中的财富理所应当,对没有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普通大众态度模棱两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国集团,与自己的同胞相比,彼此之间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不管是栖身于纽约、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今日的超级富豪们逐渐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国度。
胜者通吃的全球化经济
新型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两个现象休戚相关:一是信息技术的兴起,二是商业的全球化趋势。但在各国内部,全球范围的剧变带来的硕果并没有被公平分享。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呈指数增长,依然有千万计的人口没有脱贫。与此同时,上海以及其他沿海城市的新贵们却逐渐与大众脱离,形成自己的阶层。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如印度和俄罗斯)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从相对自由的美国市场经济到富足的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社会民主国家,收入不均的问题都日渐突出。
虽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关于全球化趋势带来世界“平坦化”的论断言之凿凿,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变得更加凹凸不平了。世界市场及技术革新联合打追了一批国际商业大亨,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金一路攀升。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6年前才辍学从商,现在却已经动摇了谷歌的统治地位。在这一剧变中,最大的赢家是个人而不,是机构。
当今世界的超级富人
随着新兴超级富豪的涌现,财富的内涵已经改变。昔日电影《华尔街》所反映的那些40来岁,每年赚二三百万美元便惹人生厌的家伙已不复存在。在网络和全球化时代,通过对冲基金和高盛银行合作伙伴身份每年赚取2000万、3000万甚至4000万美元的30多岁的人并不罕见。于是,在曼哈顿餐会上,坐拥4套房产的富人们便开始谈论购买何种飞机的“豪华”问题。
与昔日的贵族阶层相比,新生代富人和普通民众之间有着更加巨大的沟壑。随着他们随意享用豪宅大院、贵族学校和私人飞机,这种距离感显得更加突兀。我们为他们一掷千金的豪情所倾倒,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便大手笔买下了一艘414英尺的豪华游轮,上面有两架直升机、一艘潜艇和一个游泳池。虽然专家学者对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均现象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忧心忡忡,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新兴富人阶层绝对都是通过真刀实枪打拼挣来的财富。1916年,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只有1/5的财富源自劳动所得,而2004年,富人们的财富则60%来自个人薪金。
全世界最大的独立资产管理机构之一、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彼得-彼得森17岁的时候才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完全是自力更生。2010年福布斯排行榜里所列举的前10位美国富人有4位都是白手起家,排行榜前10位外国富豪中有6位属于白手起家,剩下的4位虽是继承祖产,却也在不遗余力扩充家产,而不是坐吃山空。虽然今天的富豪们都不是生于赤贫境况、注定苦命的孩子,也少不了良好的早期教育,但是他们的财富大都是通过辛勤劳动和智慧赚取的。他们是商界的绝对精英,绝不仅仅只是消费财富,而是创造财富。
富豪的独立王国
21世纪真正的富豪互动大都发生在国际会议上。而这之中,最为著名的当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了,受到其邀请则标志着作为新兴富豪正式进入这个独立王国。与之类似的,还有被认为操控全球政治阴谋的世界上最神秘的组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年度会议、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克林顿全球行动计划”国际会议、“TED大会”、中国海南的“博鳌论坛”等等。此外,一些著名企业也开始独立承办国际会议,譬如谷歌公司的“Zeitgeist”大会便是群英汇聚,诺贝尔奖得主和新兴公司创始人都是大会常客。即便是在大会休息的空当,各个公司老总们也都不忘匆忙打开黑莓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获取最新资讯。如今在精英人士之中,社会地位的标志不再是游轮、赛马或骑士爵位,而是拥有可以改变世界的宏伟计划。
当代富人们自成体系,彼此问的交往比和自己隔壁的邻居更为密切。诚如美国银湖投资集团创始人哈金斯所言:“一个经营着一家大型非洲银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非洲人和我要比和他的黑人同胞有更多共同之处,而我和他也比和我的邻居有更多相同经历和困扰。”他们所在的圈子由“利益”和“活动”所定义,而不囿于“地理”概念。无论在北京还是纽约,伦敦还是孟买,他们约见一样的人,吃在一样的餐厅,住在一样的酒店。作为世界公民,他们从事有着众多重合之处的商业、政治和社会事务,完全不拘于地理因素。
一位事业有成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告诉我,他对达沃斯的街道比对老家曼哈顿的街道还要熟悉。在家时,通常由司机驱车,而只有在白雪皑皑、不便驾驭豪华加长车的瑞士度假村,他才会徒步前进。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媒体老总如此言简意赅地概括:“我们这些人和空姐要比和自己的老婆熟识得多。”2006年美国最大8家银行都由美国人执掌;现如今时过境迁,当初的8家银行还剩下5家,其中花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总裁都是外籍人士。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穆竿默德·埃尔一埃利安是这种跨国富豪社区的代表人物。他的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自幼便辗转于埃及、法国、美国、英国和瑞士。他分别在剑桥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而现在执掌一家基地在美国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所有权则属于德国的安联保险公司。
填平沟壑
说到底,超级富豪们也不尽相同,虽然有恬不知耻、从国家“问题资产救援计划”获利的银行大鳄,但也有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受人敬仰的人物。最终,我们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一个富有创造力、充满生机的超级精英阶层来生产商品、提供就业。全球经济瞬息万变,加之政府严重的财政亏空,必须有人对中产阶级必不可少的公共教育和社会安保系统买单。这其中很多支出都需出自富人腰包——毕竟,如抢银行的盗匪们所言,他们才是真正的钱袋子:另一方面,超级精英阶层所面对的真正威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并不是更高的税率,而来自很可能会发展为民粹主义的公众中正在酝酿的怒火——譬如,美国中产阶级认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多少福利,而决定拥护贸易保护主义或支持惩罚性税务措施,例如取缔布什时期对高收入减少征税的政策。
历史经验证明,超级富豪们有两条出路:要么是压制反对意见,要么是和大众分享自己的财富。哪条出路对美国乃至世界更为有益,不言自明。让我们寄希望于超级富豪们不会闭目塞听,对此视而不见。毕竟,现实世界不会出现一个纯粹由富人组成的、自给自足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