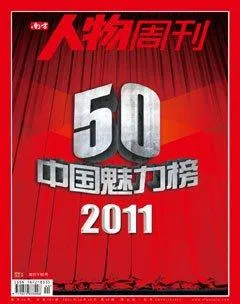来信
视大人而藐之
任何一本描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都不能忽略梁漱溟其人其事。
他几乎是那一个时代读书人性格的缩影,我说的并不是那些见风使舵、谄媚求欢、忍辱偷生,或明哲保身的那些人,而是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的那一群人。这些读书人,总会在历史发展拐点上挺身而出,并有各自精彩的表现。犹如梁漱溟所言:“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梁漱溟的一生所具有的传奇色彩比比皆是,其中以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引人注目。
只有他敢于和毛泽东纵论天下,各抒己见,也只有他敢于公开批评顶撞,甚至激怒领袖人物,直言不讳建议毛要有虚心纳谏的雅量,即使备受批判,也绝不退缩妥协。
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骨,我们找到了现实版。
视大人而藐之。
——杨锦麟
(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
《“问题中人”梁漱溟》
我的祖父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平静地走完了传奇、坎坷的一生。人死本可盖棺论定,无奈有些人不敢正视历史真相,知错不认错、不道歉,更有甚者,借审订祖父《生平》之机,玩弄文字游戏,歪曲真相。我们全体家属据理力争,最后有关方面不得不将关于“1953年事件”的文字从《生平》中删除,人为地造成了一段历史空白。为表达我对祖父的敬仰、对这个结果的态度,我为祖父撰写了一幅挽联。上联:百年沧桑救国为民;下联:千秋功罪谁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可能由于当时不许公开报道这副挽联的缘故,它被广为传抄成:百年沧桑为国为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这有悖于我撰写挽联的本意。“1953年事件”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可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说法。
——梁钦宁
梁先生能有善终,是一个奇迹。
——网易浙江省网友
先师钟文典先生负笈北大时,聆听过梁的教诲。他说,在北大,有两个人骨头最硬,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就是梁漱溟。你们看他那张照片上的表情,他就是那个样子,做学问做人都是那个样子。
——守谦的热炕头
(河南师大教授,历史学博士)
《〈大众电影〉 一本杂志的60年》
封面上的照片,为我的肚脐眼还专门开过研讨会,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了吧!那时大众电影的辉煌无人可比,今天三万份读者还不如我们电影学院网站的关注量大,真让我感慨万千。谢谢你们又让我穿越回到从前,江山依旧,故人难寻!我突然觉得,我要拍些东西报答你们和大众电影曾经的辉煌。
——张晓敏(演员)
60年,大众电影的发行量从900多万跌至3万,它自身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缩影,文章再现了这段历史,值得一读。
——孜孜追梦人(新浪网友)
《黄耀明 大时代的歌者》
多年前,第一次听到《石头记》,就觉得那音乐仿佛在什么山后起伏,线条却很清晰,随之为之倾倒。到《10个救火的少年》,简直成了口头禅。香港总有些文艺人能让人感动,这很奇怪。可能厚重和轻盈同为一理。
——金钱帮主(网易网友)
口罩记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年后我要去北京定居的消息甫一传出,MSN上各路英豪就纷纷跳出,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您是去北京找死吗?”
京都空气“有毒”的消息,微博上早传得沸沸扬扬,可抱怨归抱怨,北京朋友没一个愿意举家带口迁徙南方的。我以笑容报之:“你们不都还活得好好的吗?”
话说到此,我却对广州和西安的PM2.5lqlHuwHDaR6la1SphGwc3jXPJ4yJCHwkCKM/V+lLOFw=指数生了好奇心,京都有美帝存着亡我之心放出的毒气,粤陕总该放心了吧。一查方知,广州拜美帝领馆和华南科研所所赐,PM2.5还算有据可查,西安却只能通过Google学术论文,得出几个零星的数据,可数字着实可怕,一到冬天取暖期,人呼吸进去的就不是氧气啊。看来西安在美帝战术体系里,地位还挺举足轻重的。
广州的情况要好一点,和联合国最低一档的日均标准相比,也就差了一个美国(联合国最低标准为35,美国大约为3-5,广州7月-11月日均约为38)。虽然也不达标,但足以让我赶快打开家里所有窗户,大口呼吸几次,再在MSN上向北京人民抱怨几句:美帝果然看不上广州啊。
数据有了,就该琢磨防御措施了。我上淘宝给在西安的父母寻觅防毒口罩,一朋友听说,也摩拳擦掌准备买上几副,谁知一见口罩真容,就打了退堂鼓。“这,我可真戴不出去。”能防PM2.5的口罩,都不是一般口罩,灰不溜秋,非棉非布,硕大笨重,要是眼睛小一点,远看上去整张脸像平面上竖起了一个金字塔。要是全城人都戴上这口罩出门,《生化危机》就不需要征集群众演员了。口罩价格还忒贵,一个就要20出头,最长只能用两周。
狠一狠心,为了爸妈身体健康,丑和贵都得忍。准备下单时才发现,此物品已然售罄。淘宝客服5分钟才抽得出空来回一句,“亲,这款太热销了,过去一周卖掉了5000个。”再过5分钟才等到下一句,“下一批货还不能确定时间。”
没办法,我只能另辟蹊径,一搜才发现,商家们真是最聪明的人。原来卖服装的、卖商品的、卖家居用品的,还有卖书的,都纷纷卖起了各类防PM2.5的口罩,还同时搭售各类防护服、润肺食品、空气清新剂和科普书籍。而且销量都不错。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专家们会说PM2.5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
从小清新到重口味
本刊记者 杨潇
我旅行到东南亚某个城市的街头,确信自己来错了地方:这里“居然”不禁摩!整个城市都被摩托和皮卡占据,拥堵的路口,它们像蝗虫一样遮云蔽日——因为烧的多是柴油,每只蝗虫只要一生气,就会吐出一大串极浓的黑烟,你无处可躲。听说过有人对汽车尾气上瘾,我自己小时候也喜欢闻公交车里的汽油味,可是,那不是小时候么,蹲在街头数汽车也用不完手指脚趾的小时候么,那时的小清新,断然想不到今日的重口味吧。
借道昆明回国,途中上网,看到NASA于2010年9月公布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显示2001至2006年世界各地PM2.5平均值,赫然发现我所抱怨的那个城市,只是淡蓝中的一点黄而已,哪比祖国江山一片红。当然2006年和2011年已不是同一个世界,时移世易,当天的《云南信息报》就公布了一个真正的好消息:滇池的水质已经达到了地表水五类的标准,草海水域0.5米水深处水溶解氧量为7.34毫克每升,“专家说,水溶解氧量超过5,水中生物就可以成活。”转机回湖南,长沙也沉在昏黄色的雾霭之中,机场大巴拼命放着“我要去西藏”和“草原夜色美”,倒也应景。
但总的来说,在湘南某个小城,暂时还能享受到无公害的白色大雾,空气中有香樟树的气味,与此同时,北京的“爆表”天在微博上炸开了锅,我庆幸自己躲过一劫,回京后向的哥询问那几日情形,当时我们正停在一个路口,他指指10米开外的红绿灯,“根本就看不见灯,全靠鸣笛了……那简直,是仙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