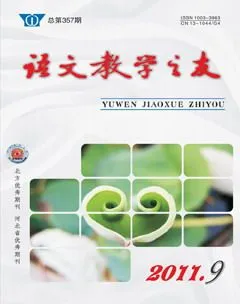“丢项链”新解
高语第四册的《项链》是一篇传统篇目,却常教常新,有挖掘不尽的深厚意蕴,这也许就是经典的魅力吧!
每次教此文,课堂上关于“玛蒂尔德丢失项链的必然性”的讨论都是轻松热烈的。因为文中有明确的铺垫、暗示,那就是舞会上玛蒂尔德忘乎所以“沉迷在欢乐里”,“陶醉在妇女们所认为最美满最甜蜜的胜利里”;舞会结束时,为了不让“朴素的家常衣服”露出寒伧相,“想赶快逃走”,等不到丈夫叫来一辆马车就“赶忙走下台阶”。这些情节交代了玛蒂尔德当时的痴迷和慌乱,而人们在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丢东西。玛蒂尔德没能逃脱这个厄运,丢失了借来的项链。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但课后总感到分析失之肤浅,解决过于草率,这个项链丢得很勉强,“最容易丢东西”,毕竟不是“一定会丢东西”。
我们知道情节为表达主题服务。主题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全部情节之中;而每一个情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应当环环相扣,使全部情节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形象地表明主题。普遍认为《项链》的主题是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这自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有人认为它的主题是金钱至上,金钱主宰人的命运。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小说的全部情节告诉我们,玛蒂尔德就是因为没有钱才不能梦想成真。“项链”是小说的标题,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就像鲁迅的小说《药》一样,这个标题也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主人公参加舞会必不可少的饰物,又暗指主人公的梦想——过那种“高雅和奢华的生活”。小说开头交代玛蒂尔德“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里”,在那个“婚姻只不过是两袋银币的结合”的社会里,她“最后只得跟教育部的一个小书记结了婚”。两个“小”字说明了她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金钱的“围墙”把她挡在了上流社会的圈外,决定了她的梦想只能是妄想。但她不甘心,一旦有机会就决不放手。当她的丈夫弄来请柬,她便用丈夫“预备买一杆猎枪”的钱置办了衣裙,借来了阔朋友的项链。“包装”了自己之后,她便有了阔太太的外表,得以进入上流社会的“门”,因为华丽的衣饰是有钱人的象征。于是在舞会上她大获成功,“所有的男宾都注视她,打听她的姓名,求人给介绍;部里机要处的人员都想跟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了”,似乎她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但“成功”只不过是短暂、虚幻的海市蜃楼,很快就消失了。她不得不冒着严寒,坐上破旧的“自惭形秽的马车”,回到了依然寒伧的住宅,处在了她本来的位置上。梦醒了,那么制造美梦的主要媒介——项链自然也就完成了使命——不翼而飞了。项链丢了,意味着梦想破灭了,项链只是暂借一用,意味着梦想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当真要去追求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作者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上流社会哪里是玛蒂尔德这个阶层的人能够挤进去的,“高雅和奢华的生活”哪里是玛蒂尔德们能够拥有的,因为他们没有唯一的门票——金钱。所以项链的丢失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决定的,是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决定的,是小说的主题思想决定的。借来的项链非丢不可,不丢就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在那个社会里金钱主宰一切;不丢就没有后来的赔偿,就不足以显示主人公命运的可悲,一夜风流十年艰辛;不丢就不可能知道项链是假的,就不足以表现主题的深刻: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超越金钱界线的追求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整个上流社会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利场。自然后来玛蒂尔德夫妇全面、细致、周密地寻找,只能是徒劳无益、无果而终,因为他们在寻找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作者单位:民乐县第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