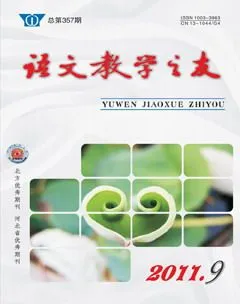诗歌小说两相映导曲同工抒真情
郭沫若创作的《天上的街市》与鲁迅先生的《故乡》虽是两篇不同体裁的名篇,但细细品读不难发现二者在写作背景、主题思想、表现手法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本文将对这三个方面逐一作比较分析,以便能对教学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一、写作背景
两篇作品的写作背景基本是一样的,均写于1921年,都是作者从异地回乡后对黑暗现实有所感而作。郭沫若1914年赴日本留学,在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中三次回国。这时“五四运动”高潮已过,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现实,郭沫若感到极大的愤怒,在“五四”高潮时期对祖国前景的憧憬陡然破灭,由一度兴奋激动陷入苦闷忧伤中,但他并未悲观失望,依然不倦地探索和追求。就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了《天上的街市》。鲁迅1919年年底回故乡绍兴搬家,目睹了农村衰败、凋零的景象和农民贫苦的生活,心情十分悲伤,于是写下这篇短篇小说,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启发人们思考如何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
二、主题思想
两篇文章都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天上的街市》运用了反衬手法来间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写天上的宁静、祥和(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反衬当时社会的黑暗、动乱;写天上的美丽、富庶(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曲折地反映了人间的丑恶、贫穷;天上的自由、快乐(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则是人间凄惨、悲凉的折射。《故乡》则运用对比手法表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现实的故乡是这样的萧瑟、荒寂,而“我”记忆中的故乡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地”,呈现之景是那样美丽,令人憧憬,景象之比,突出现实故乡的衰败和萧条。其次是人物的对比,“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的少年闰土,变成了一个脸色“灰黄”而且有“很深的皱纹”,手“像是松树皮”的中年闰土。曾经是活泼可爱、健康多智、勇敢机敏的小英雄,如今变成一个呆滞、迟钝、麻木、自卑的木偶人;原先是美丽而安分守己的“豆腐西施”,如今变成了自私、尖刻、泼悍的小市民。这些人物的形象性格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雄辩地说明农村破产、农民生活痛苦、小市民阶层日趋贫困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
《天上的街市》作者憎恶当时人间的黑暗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光明、自由和幸福的生活,所以通过想象把美丽的街市放到天上,把牛郎织女的生活写得美满幸福。这实际上是他理想生活的寄托。而《故乡》作者对故乡的景、故乡的人感到失望、悲哀,甚至凄凉之时,仍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既不像我们这一代彼此隔膜,也不会因为要一气而“辛苦辗转”、“辛苦麻木”、“辛苦恣睢”。很显然作者暗示我们,他的理想生活是没有隔膜,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安居乐业。可见两文均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只不过《天上的街市》直接展示光明、自由、幸福的理想生活画面,而《故乡》则间接暗示出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的理想生活情景。
三、表现手法
《天上的街市》和《故乡》两文均采用了借物抒情的表现手法,通过描绘夜晚美景来寄寓作者的理想生活,所不同的是《天上的街市》描绘的是天上的繁华市街,无数街灯通明,橱窗里陈列着数不清的珍奇,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牛郎织女,骑着牛儿,提着灯笼,自由自在地来往,目睹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笑逐颜开,为牛郎织女的幸福生活而庆幸。而《故乡》描绘的则是人间的月下瓜地:蓝天、碧海、沙滩、圆月、一望无际的瓜田,给人以色彩明快艳丽、美好动人的感觉。两位文学大师均通过描绘美好的夜景抒发自己对未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综上所述,《天上的街市》和《故乡》的作者是两位“旗手”(邓小平语),面对“五四”以后那黑暗的社会现实,通过直接或间接描绘自由、快乐的生活图景,抒发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单位:如东县浒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