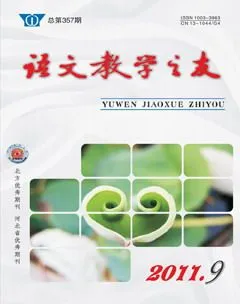细读文本 冷看插图
读图时代的来临,语文教科书在时代的潮流中悄然“应时而变”,其中的插图铺天盖地,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仅人教版七年级下册中,30课的正文中插图就有40幅之多,几乎课课有插图,甚至一课多达两三幅,《丑小鸭》就有三幅之多。文中插图,大致可分为五类:书画作品、人物画、动植物画、实景照片、诗词意画。这些插图,大多品质粗劣,除实景照片还能或多或少再现一点某一场景的真实外(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三味书屋”),书画作品毫无神韵(如《竹影》中的“竹影”和“风竹图”),人物画比例失调、线条简单、形似动画人(如《爸爸的花儿落了》插图里的“爸爸”形象),动植物画死板僵硬、毫无生机(如《丑小鸭》的几幅插图),诗词意画更是离谱(如《天净沙·秋思》的配图)。然而,这些插图毕竟不只是“脂粉”,它是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增强学生阅读兴趣、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辅助师生教与学而精心设立的,它必须为教学服务。否则,要之何用?但是,它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了吗?笔者以为不然。
由于插图浓妆艳抹、披红插花、招摇过市似的粉墨登场,无可置疑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于是,利用插图进行教与学也就成了师生无法回避的共同选择。不可否认的是,插图一开始的确吸引了学生的眼球,为学生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和惊喜,对课文内容的初步理解也确有帮助。然而,好景不长,插图的这点“闪光效应”之后,学生大都不能逐字逐句细细地深层次品读课文,只是粗略地读一下,领会一点大意便觉得十分满足。他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看图取乐上。可以说,读图使浅阅读风气在学生中日益升温,已经严重妨碍了学生对文本深层有效的解读,语文学习兴趣的衰退,也可能与它不无关系。例如,笔者执教冰心先生的《观舞记》一文时,要求学生细细品读,特别是“我们虽然不晓得故事的内容……”一段,透过字里行间,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体会卡拉玛姐妹高超的舞蹈技艺。然而,学生在下面骚动了起来,正当我认为他们是与文本产生共鸣而自得时,一声尖叫彻底粉碎了我的梦:“乖乖,真是个大美女啊!”全班同学也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起来。我如梦方醒,知道学生是对插图中的“美女”感兴趣并进行品评了,至于文本,他们根本没去细读,当然更谈不上细品了,因为他们对“品图”更感兴趣!后面,我做了多种努力,试图把他们带入文本,结果都收效甚微,一节课草草收场。
而且,由于学生不能认真的品读课文,这些品质粗劣的插图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和发展,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也形成了负面影响,甚至图文不符,歪曲了文意,制造了课堂闹剧。如笔者教学《天净沙·秋思》时,在学生初懂文意后,让其对照插图,展开想象,想象作者当时所处的情境,进而达到人情入境的地步,与文字产生共鸣。但出乎意料的是,学生喧闹了起来:有一学生指着图中的“乌鸦”大喊“老鹰”;有一学生感叹“山真蓝,水真绿,夕阳正红,骑马游一圈”;还有一学生说“真是一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人家,风景真美”。反观其图,我也感到颇不适宜,一是画中景物与文不符,如插图中找不到“枯藤”、“老树”的影子,只见“老鹰”,不见“乌鸦”。二是图文内容大相径庭,《教师教学用书》中说得很明确:“一个秋日的黄昏,荒凉的古道上,西风劲吹,落叶纷飞;道旁,缠着枯藤的老树上,鸦雀已归巢,不时地啼叫几声;不远处,在小桥流水近旁的稀疏村舍里,人们正在准备晚餐,炊烟袅袅。这时,一个人牵着一匹瘦马独自缓缓行进在古道上。”但图中既看不到落叶,也没有缠着枯藤的老树,树上无鸦窝,看不出“乌鸦”有归巢之意,不见炊烟,不见牵着瘦马的人。只见雄鹰展翅高飞,朽木桩两根,绿色的流水,火红的夕阳,骑着马的闲游人!三是图的色调与文的感情基调相去甚远,文是“悲”,图是“喜”。试问,这样的插图究竟能给学生带来多少美感?对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发展有何益处?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有多少影响?对文本的深层解读有何好处?再如八年级下册《雷电颂》文中的配图,屈原的形象就与文本相去甚远,甚至可谓南辕北辙。文前的“舞台提示”中是这样描述屈原的形象的——“屈原手足已戴刑具,颈上并系有长链,仍着其白日所着之玄衣,披发,在殿中徘徊。因有脚镣,行步甚有限制,时而伫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举动时,必两手同时举出。如无举动时,则卷曲于胸前。”而配图中的屈原呢?手足并无刑具,颈上亦无长链,亦未披发,更不见手镣脚镣,而是腰挂佩剑(文中屈原云:“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一手指天,长衣飘飘,烨然若神人!试问,像这样与文本格格不入的配图,对解读文本、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及审美情趣、审美品位又有何作用?
为什么语文教科书中的插图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闹出笑话呢?我觉得原因有二:一是教科书中的插图几乎都是“拉郎配”,即文本最初本无配图,当其选人教科书后,教材编写部门的工作者,为了使教科书更丰富多彩,便找了一些接近课文内容的图配上去;二是他们配图时并未进行认真严格的审定,致使一些貌合神离、品质粗劣的图浑水摸鱼,蒙混过关。
老子曰:“大象无形。”文字便是那“无形”之“象”,因“无”而成其“大”,因“无”而无拘无束、幻化无穷、高深奠测。一切蕴含其中,生命有多少内涵和外延,这种“大象”召唤下的感受、理解、想象就有多少空间。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越是优秀的作品,越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越能给予读者创造的弹性空间。而直观浅易的“有形”之画,因其具体实在,而显出平面性、单一性和有限性。试图以图释文,很可能挂一漏万;试图以图兴文,犹如痴人说梦;试图以图代文,那是语文缴械投降。所以,给文配图需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不是多多益善,更不能滥竽充数,弄不好会因图误文,得不偿失!
(作者单位: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