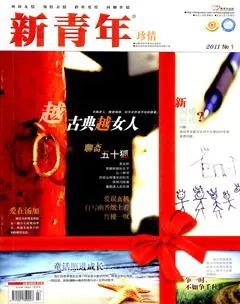聊斋五十狐
如果聊斋里没有这些妩媚迷人的花妖鬼狐,那就只剩下诡异怪诞的躯壳。是这些狐媚妖娆的女子,让一部书,历经这样漫长的时光,依然闪烁着魅惑迷人的光泽。
蒲松龄出于对鬼魅世界不息的热爱与探知,和对纯美女性的痴迷与向往,在聊斋中孜孜不倦地描摹出如许丰沛饱满、特立独行的女子。其中最重要的,大约就是她们迥异于世俗女子的“狐”性。这一点,成就了聊斋故事的万花丛里,最明亮馥郁的那朵。这一点,也构成了所有聊斋女子最值得浓墨重彩的灵魂。
所以《聊斋五十狐》中的“狐”,讲的并不只是妖冶的女狐,还包括那些花妖鬼魅和鸟兽鱼虫幻化而成的精灵女子。她们个性迥异,曼妙多姿,但又因这一点共同的呼之欲出的“狐”性,而使得花团锦簇中,见了一条柔韧的丝线;是它貌似漫不经心却又诱人无比的一束,给予了这些女子,一个身心皆安的归处。
“狐”是一个勾魂摄魄的词汇。妖媚的,风骚的,艳绝的,放任的,鬼魅的,不羁的,淡定的,骨感的,疏离的,肆无忌惮的,却又都不足以概括这一个“狐”字里所植入的无限风情。五十个女子,犹如五十条藤蔓,缠绕蓬生在一起,便成为一只只让人迷恋痴爱的狐。
写作她们的过程,其实就是以当下的眼光,为之重新阐释定义的过程。她们在而今的喧嚣尘世中,因了时代的不同,而有了簇新的意义。作者曾经褒扬的,或许在时下成了无情的嘲讽;而那曾经被贬损的,反倒是见了玉石的温润。所以其中的每一个“狐”,皆在锐利又不失柔软的现实主义的解剖下,带上了扑面而来的现代女性的气息。
因此这是一部借古代狐,观现代女的书。时下职场中毫不逊色于男人的女子们,与聊斋中那些敢爱敢恨、洒脱不羁的女狐们相比,在爱情的这场争夺保卫战中,究竟是迂回向前,还是在节节败退?而假若时空可以跨越,那么聊斋女狐与职场女性关于爱情的PK赛,究竟孰胜孰败?聊斋中那些总是有团圆喜乐结局的书生们,他们行至而今男女在物欲中沉浮挣扎的时代,是会生出感伤失落,还是会有了畏惧惶恐,扭头逃回到那花妖鬼魅的世界里去?
所有这些疑问,皆可以在此书中寻找到答案。尽管,这样的答案未必精准明晰,甚至带着些不怀好意的猜测和臆想,但终归是可以看到时过境迁中人性的变动,还有“狐”性在女子身上的长途跋涉与迁徙。
离去不伤,不过是因为,曾经深爱。而缘来不喜,也只是因为,那份深爱早已经注定。
所以那一个个从聊斋里倏忽来去的女子,她们的“不伤”与“不喜”,原只是“狐”性中,生来就有的对于爱情的淡定与从容。爱情来时,且让它铭心刻骨;爱情去后,就让它随风而逝。
一个“狐”字,真是夺尽了天下所有的妖媚与风情。
常生对于葛巾究竟是仙还是凡女,抑或花妖的执拗探究,犹如当下男人对于女人过往情史的刨根问底。那股子热情,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所爱,是否值得。如若对方历史清白,那么女子的痴迷。便可以珍惜;但若如葛巾一样,来路不明,那么她的一腔痴情,就值得商榷。
——葛巾:今见猜疑,何可复聚
鬼迷心窍。说的便是晏伸这样的男人吧。但假若他的心窍里有另外一个女人,而且紧贴心房,连空隙也不留下,那么纵是女鬼再如何引诱。怕也是进不去的。恰恰他的心里。盛一个湘裙不够,还需要别的女子来坐,所以才让女鬼有机可乘,并差一点,就要了卿卿性命。
——湘裙:不嫁田家牧牛子
青凤与耿生,一个有情,一个有义,只是中间隔着那古板保守的阿叔,便横空里多出了一些波折。不过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总是归于团圆喜乐,倒是蒲松龄用一个缘字来解,反而有些牵强,不如说他是借此。道出了千百年来,男人们的心声,以及对今日早已幻化成凶神恶煞之“岳母”形象的长辈的耿耿于怀。
——青风:惓惟深情。妾岂不知
不过有了红玉,这个男人便成为命运的宠儿,该成亲时有红玉送白金聘妻,该报仇时有红玉代其杀敌,而今该重整旧山河了,照例有红玉前来相陪。而且,这一来,便是一生“明媒正娶”的好伴侣。
——红玉:逾墙钻隙,何能自首
这算是典型的女上司和男下属的恋爱版本了。锦瑟雇佣了落魄的王生,绐他一个在阴间可以“乐死”的机会,还时不时地为他加功晋爵,提携于他。安排了小秘,看似辅助他处理日常杂物。但借此考验也不一定;否则,不会在他被小秘春燕百般挑逗都无动于衷时,便加倍地给予赏赐。
——锦瑟:业多,则割爱难矣
绿衣女: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
这是一个没有名姓的女子,在聊斋中,她的这一段与书生于璟的情缘,亦是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可是每次品读,都会疼痛不已,似乎她之所以存在于世间,不过是为这转瞬即逝却铭心刻骨的尘缘。
蒲松龄称她为绿衣女。这是一个极易让人产生想象的妙称,夜色之下,一个着绿色长裙的女子,穿越山林,为醴泉寺里飘摇昏黄的灯下,勤奋读书的益都书生,送去深山中的一抹温情。她衣裙里的绿色,想必应是湖绿。翠绿太轻,无以承受爱之深沉;新绿太鲜,经不起尘埃扑落;碧绿又艳,不能沉静如水。唯有这湖绿,可以盛得下她动了尘缘之后,心内浮动的无边无际的忧伤。
这只绿蜂幻化而成的女子,想来早已在寺中守候许久,只是她见到的多是苟且偷生之辈,在古寺中栖息,尚不忘利禄功名,甚至为蝇头小利而躁动不安,辗转难眠。她从窗前飞过,看如此庸碌之人们,未曾动过丝毫凡心。也因此,当书生夜起读书时,她才会忍不住,停驻在月光微凉的窗前,赞一声:于相公勤读哉!
书生知道这样一个婉妙无比的深山女子,必定不是常人,但却无法阻挡她微笑娇嗔一句: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何劳穷问?其实书生在绿衣女推门笑人的时候,心内便已经起了波澜,所以即便是良宵过后,有被她噬掉的危险,他也顾及不得。因为,这样一个长夜中可以红袖添香的美丽女子,孤独苦学的他,其实早已渴盼良久。
此后绿衣女无夕不至,与书生饮酒,赏诗,并解音律。书生果然是她知音,听出她必有常人不能企及之亮烈歌声,于是恳请她唱一曲销魂。绿衣女怕外人闻去,犹豫不肯,但却经不住书生再三恳求,答应只轻声歌唱。
她的歌声,果真是宛转滑烈,动耳摇心。不只销了书生的魂,亦让她看清了自己那颗深深嵌入了红尘的心。她唱: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这词里唱出的微凉心境,怕是书生并不能完全懂得。否则,不会在她惶恐有人窥视,绕屋周视时,他问她为何疑惧如此之深。而当她忧虑此段缘分,即将止住时,他又问为何。及至她说,自己心动,或许在人间的时光不会长久时,他又以常理推论安慰,心动眼跳,是人之常事。他终究只是一介书生,没有此灵异女子对世情一眼望穿的颖慧,所以她用歌声告诉他,即便是知道树上的鸟,常常欺骗她,半夜便散去佯装天明,可她还是夜夜不辞辛苦,濡湿了绣鞋,也要赶来看他,只因为,她不想留他一个人,在漫漫长夜无人相伴。而他,却始终不能解其深情,更不能明白,她在死亡的危险逼近之时,心内有怎样的惊惧和哀伤。
她知道有大难将至,所以夜半起身、开门离去之时,犹豫徘徊,终于还是返身,乞求书生送她出门。微光之下,此时她脸上的表情,半是忧惧,半是不舍,不知此一别,是不是再不能与君相见。当书生将她送到门外,她又乞求,让他停住,注视她转过房廊,再返身回去。在他,这似乎只是与平素黎明将至时的离去毫无二致的告别;在她,这却有生离死别的大恸。
果然,在书生正要归去人寝之时,有女子急呼救命的声音。他急忙奔去,却并不见人影,循声望去,竞在屋檐之下,看到一只硕大的蜘蛛,正死死缠住一只哀鸣的绿蜂。等到书生挑破蛛网,去掉捆缚,发现绿蜂已经奄奄一息。
书生将其置于案头,过了许久,绿蜂才慢慢苏醒,开始移步。也就是此时,她用尽平生之力气,跳入书生的砚池,用满身饱蘸的墨汁,在案几上,无声无息地,缓缓写下一个“谢”字。而后,振动翼翅,穿窗而去,自此遂绝。
这最后的一段,不知蒲松龄写下的时候,心内有怎样的撕心裂肺,万念俱灰。可他还是放它飞去,彻底了断了这份情缘,将挥之不去的伤痛,留给那自此也失去了踪迹的书生,还有如我等穿越时光试图找寻这绿衣女子前世今生的后人。
这只是聊斋里众多痴情女子中的一个,比起那些名姓皆俱、为所爱之人奔走劳碌的鬼狐女子,她几乎会被忘记。可是她的忧伤,惶恐,惧怕,不舍,却又如此鲜明,且打动人心。假若她不是生为绿蜂,那一定是江南妩媚妖娆又惹人怜爱的女子,只那不盈一掬的细腰,便可迷倒多少渴盼红粉佳人的男人。
可她却不过是一只弱小的绿蜂,无力逃掉世间灾难,更不能拯救书生的孤独。所以她与他,也唯有此段夜间相伴而歌的缘分,并用一个“谢”字,做最后生死别离的倾诉。
聂小倩:愿执箕帚,以报高义
聂小倩爱上宁采臣,说不上究竟是因其人高洁,没有色心,还是因其助她远离妖孽,可以安葬尸骨。她每每都主动请愿,愿执箕帚,以报高义,却总是被那寡淡元欲的宁采臣,给当场硬生生拒绝了去。但细究起来,宁采臣其实有文人惯常的虚伪,聂小倩所爱,实在是心中被完美化了的那个男人。
真正胸襟坦荡开阔之君子,当也同时内敛深沉吧。但宁采臣不,对于自己的忠贞,非常高调,每每见人,便要申明:生平无二色。彼时宁采臣功不成、名不就,也就在情感上,可以拿出炫耀示人。他的妻子,那时久卧病榻,他处处提及只爱此女一人,很有安慰病妻且在人前作秀的嫌疑。所以其实宁采臣热爱声名,远胜过怜惜女人,否则,不会在“娇艳尤绝”连女子都抵挡不住其摄魂美貌的聂小倩面前,正人君子到几乎像是失了性欲之人。
聂小倩初次试探诱惑宁采臣,他便是一副正襟危坐不近女色的柳下惠尊容,畏惧人言,讲究廉耻,为了护佑道义,叱骂聂小倩速速离去,否则必当众揭发她的丑行。聂小倩复又扔一锭黄金到他的被褥之上,这人也捡起“啪”一下扔到门外去,不理这不义之财。这样一脸正气,直让阅人无数的聂小倩认定是铁石心肠。
不过这样的冷硬无情,倒是救了宁采臣一命。被妖魔挟持用财色勾引男人的聂小倩以实相告,宁采臣怕死至极,忘了昨日那般冷漠,转而求聂小倩相救。聂小倩认定了宁采臣是那正人君子,义气干云,值得相托,所以便看他百般都是好,指点了明路,又哭泣托他救自己逃离苦海,将朽骨带回安葬。
宁采臣爱惜生命,胜过女色,在之后的逃生中可见一斑。隔壁有奇术的陕西剑客燕生喜好安静,不想与宁采臣同宿,但宁采臣依然强行将自己被褥搬了过去。后见燕生藏剑威力无比,又央求其传授剑术给他,以求护佑自己,但却被燕生看出其将来是富贵中人,人不得此道而婉言拒绝。
死里逃生后的宁采臣,没有忘了昔日诺言,为聂小倩迁移坟墓。不过为了遮人耳目,还是在燕生面前撒了谎,将聂小倩称之为自己的妹妹,而不是情人。宁采臣究竟有没有真的爱上过聂小倩,这是一个无法确证的事。他们初相识,他对她的美貌,毫不痴迷,甚至在心里因其夜半闯至男人卧室,要求共修燕好,而万般鄙薄。后来她救他一命,他将其尸骨移到家中附近,远离妖魔掌控,也算不得爱情,只不过是对她恩情的回报。即便是后来娶了她,也是被其日日服侍母亲操持家务所感动。因此宁采臣对聂小倩的情感,一直游离在外,他甚至从未对她说过一个爱字。
不过以宁采臣对情感处处宣称“平生无二色”的谨慎原则,他对聂小倩即便是深爱,也着实不会坦诚表露。他将其葬在自家宅院旁边,并吐露说这样可以听到她的歌哭,不再让其受恶鬼的欺凌。等到聂小倩现形要跟他回家拜谢父母之时,他眼中的聂小倩,则是“肌映流霞,足翘细笋,娇艳尤绝”。这样的审视,终于带上了一点男性的窥探与爱怜,甚至在观察其尖尖小脚的时候,还带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性”趣。
可是这个男人,终究还是胆小懦弱。凡事都听从于母亲,遵从于社会的法则,不会逾越半步。尽管聂小倩主动提出为报恩愿意委身于宁采臣,其母还是惧怕其女鬼的身份,担心这样唯一的儿子断了香火,婉言拒绝。而宁采臣自始至终,都在母亲面前保持沉默,未曾替聂小倩说一句公道话。是聂小倩自己要求以兄妹的身份,留下为其“依商堂,奉晨昏”,这才被宁母同意留了下来。忙碌完一日,宁母未曾给聂小倩准备被褥,明显是赶她回到冰冷的坟墓里去。而宁采臣,与聂小倩对坐一窒,寂然无语,明明知道其诵读《楞严经》让他指点,只是一个借口,不过是为了与他待的时间更长一些,或者给他足够的时间和勇气,将她留下来共宿。但是宁采臣却在过了二更,聂小倩都没有“言去”的时候,着了急,催促她快快离开。甚至在聂小倩直接向他袒露内心惶恐,说“异域孤魂,殊怯荒墓”时,他也未曾怜惜,反而愈加地强调声名和清白的重要,说一则房中无其他床寝,二则兄妹之间应该保持距离,以免引来人的非议。这样的宁采臣,几乎有些惹人厌恶了。看到聂小倩一步一回头哭泣着离去,他依然是心肠冷硬,怕母亲嗔怒,而狠心让她回了孤坟,而且,此后日日如是。
是聂小倩依靠自己的聪慧和贤惠,赢得了宁采臣母子的欢心,并在嫁娶这件事上毛遂自荐,坦陈自己既无害人之心,也不会妨碍宁采臣延续香火,而且早就算准了,宁采臣会有三个儿子,是命定了的。在劝说母亲的过程中,宁采臣依然是没有出一丝的力气,只做了看客,等待母亲的裁决。倒是在母亲同意之后,宁采臣大喜,急急地宴请亲朋。为了给自己增添颜面,又让聂小倩华妆而出,让所有人都为其惊人的美貌而震惊,并将其认定为下凡的仙女而不是女鬼。
聂小倩真是给宁采臣整足了颜面,让爱惜声名的他,过了母亲的关,又得到亲朋的信任,之后连追逐而至的妖孽也给铲除。可是宁采臣在得到美人之后,又做了什么呢?这个中了进士功成名就的男人,在聂小倩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后,还不满足,将昔日信誓旦旦的“平生无二色”给忘得一干二净,很快地便又纳了妾,得到两个新的儿子,成为世上香火旺盛又“妻妾成群”的最幸福的那个男人。
可见如此言行不一的虚伪男人,其实是不值得如聂小倩这样的女子,深爱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