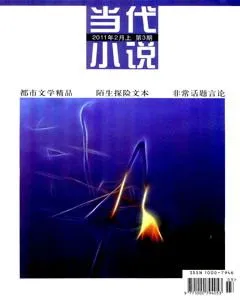开车回家
1
好长时间不回老家棉花凹了,年底的时候我买了辆小车,决定开着车回家。开着小轿车回家的感觉一定很爽吧?以前的时候,我都是坐班车回家。坐班车回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麻烦,有过坐车经验的人都知道吧?所以,一提到回家过年,我就头疼。我宁可平时多回去几趟,也不愿意挤在春节期间回去。可是一到年底,离过年还远着呢,我爹和我娘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放假,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他们说,腊八粥还给你们留着呢。他们说,专门给你们蒸的枣花糕有十几层,今年蒸的最好。他们说,家里那只黑山羊就等着你们回来杀了吃了。他们说,还有那几只纯笨鸡,那一筐子笨鸡蛋……你说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他们是想我了,不仅想我。我知道他们更想他们的孙子,更想他们的儿媳妇,人老了就盼着一家子团圆,享受他们的天伦之乐。平日里他们虽然想,但是他们不敢说。怕耽误我们工作,怕耽误他们孙子学习,这过大年了,他们有了理由,所以一遍一遍地来电话催我。我只好安慰他们,好,好,你们好好留着,很快我们就回去了。很快就回去了。
其实,说到回家过年,我很有些不舒服。一是我老婆张朵不愿意回我们老家过年。这让我很没有面子。大家都知道,面子这东西是很重要的啊。她是我所工作的这个城市里的人,虽然父母都是下岗职工,但是,她还是觉得她是一个城里人,有着城里的低素质的人常有的那种优越感。对农村有偏见,好歹回去一趟也不省心,不是这里不合适,就是那里挑毛病。尤其是我们老家那个地方,生活上有些落后,卫生上有些不干不净的,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她就有些不耐烦。一会儿说水太咸,不好喝,一会儿说,茅房里太脏,蹲不下人。我记得除了结婚那年跟我回家过了一次年之外,这七八年来,她基本没有在我老家过过春节。就是回去,也是年前回去一趟,第二天接着就返回来。或者,年后回去一天,第二天就回来了,算是给我面子。她不愿意回去过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那里初一早上拜年要磕头,要跪下磕头。只要是村上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尤其是新媳妇们,都要由婆婆们领着挨家挨户去拜年磕头。那一年真是闹了笑话了,初一早上,我娘领着张朵去给那些叔叔大娘们拜年,张朵倒是给我面子,去了。但是就是像个木橛子直直地站在那里,不磕头。当时拜完年回来我娘倒是没说什么,可是第二天那些叔叔大娘们见了我都笑话我,说我媳妇不懂事,不知道给老人磕头拜年,说我怕老婆,教育不好老婆,是个孱头。我那个尴尬啊。张朵后来听说了,也生气了,发了誓,再也不回那个可恶的棉花凹过年去了。再一个让我不愿意回去的原因是,我虽然是我们村上考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还到了省里工作,当了大学里的教师,可是我没有混好。我是个没有多大出息的人。我既没有混个一官半职,又没有赚钱发大财。我那些小时候的同学,考上学和没有考上学的,出门闯荡的,都混好了,或者当老板,发财了,或者进了机关,当了领导,即使出国打工,也基本都发财了。回来的时候,要么腰包里鼓鼓的,见了小孩子一百一百地掏压岁钱:要么就为村上办了不少事。总之,在我们老家棉花凹,发财不发财是一个人混好混不好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官不当官也是混好混瞎的标志之一。我既不当官,又没发财,就算是混瞎了的人。记得那年三叔的儿子刘全辍学,跑到省城里来找我,要我为他安排份工作,到后来我什么也没给安排成,我那个难受啊。当年我上大学,我父亲落下了多少饥荒,欠了亲戚朋友多少钱,是全村人帮助了我许多我才走出去的,本想着我混个一官半职,衣锦还乡,为棉花凹的老少爷们多办点儿事来报答他们,可是到头来,我的生活也只能是基本温饱,连小康都达不到,更别说我爹我娘跟着我享清福,我们棉花凹的人跟着我沾光了。我爹虽然没有给我当面讲过我混瞎的话,但我从他的眼神和叹气中我能感觉出来,我是多么没有出息呀。最近这两年,我们老家棉花凹也有好几家买了小车了,尤其是那些在外面工作的,春节回家基本都是开车回家。老婆孩子,大呼小叫,喇叭嘀嘀嘀嘀地摁个没完。只有我还大包小包地拎着,从班车上跳下来,从村口穿过多半条街回家,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害怕在街上遇到熟人啊,我每次几乎都是逃到家里去的。所以,没有车,不仅张朵和儿子都不愿意跟我坐班车回家。我自己也憷得慌。还有一个让我不愿意回家的原因就是,我的老婆张朵虽然很爱我,但总爱不给我面子,她老是喜欢和我对着干,我说东她就说西。我说打狗她就说撵鸡,我回老家去堂兄堂弟家里喝个酒,她也得跟着喊我好几次,不让我多喝。这让我很没面子。你知道,在我的老家棉花凹,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女人的上帝。男人们的事女人是不敢随便管的,高兴了、男人们一脚就把老婆踢飞了。我可不敢踢张朵,我这样的人,不被踢就不错了。所以,在我们棉花凹,要是一个男人连老婆也管不了,那就是没出息透顶了。
我爹那一次去我家里住了几天。他发现在家里老是我下厨房做饭。收拾碗筷,张朵吃完饭一推饭碗就上网去了,或者做面膜去了。我爹看见了就叹气,回来后给我娘说了,我爹说,刘刚这孩子算是混瞎了。混瞎了。这就是我爹给我的评价,我伤了他的心,我也觉得自己简直没出息极了。所以,每到回家过年,我心里总是不三不四的,没有个好滋味。我老婆张朵是个护士,工作忙,她有理由不回家过年,可是我是个大学老师,那么长的假期,我有什么理由不回家呢?
年底的时候,我下了决心,决定捞回点面子。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取出来,又找朋友借了点儿,买了辆小轿车。车不算是好车,价位也不高,但是漂亮、排场。嗯,排场就好,要的就是排场。乌黑锃亮的颜色,流线型的车身,看上去高贵,大气。我老婆张朵也很高兴,她甚至决定打破誓言,跟我回家过年了。她说,只要是不让她磕头,她就跟我回家过年。我说,嘿嘿,那些封建风俗咱坚决排斥,磕什么头呀。我老婆张朵就指了我说,你呀你呀你,别光一张嘴。你同意你娘同意不?我说,我早就给咱娘说了,咱娘开明,说,不磕头。不磕头。张朵说。那我儿子也不能磕头。我才不要我儿子磕头呢。我也顺着她说,那当然,男儿膝下有黄金,有黄金咱也不跪。我儿子刘东说,我不磕头奶奶和爷爷还给不给我压岁钱?我拍一下他的头说,这个臭小子,就想着钱。张朵说,不要钱咱也不磕头,儿子。我儿子刘东却说,那可不行。我想要压岁钱,我磕头。嗨!这个臭小子,真又是个没出息的样!气得我老婆打了他一巴掌,说,真不愧是刘刚的儿子。遗传没出息!
我发动开车,准备上路。我老婆张朵一把把我拽下来,说,去你的。去副驾驶。我来开。张朵和我一起学的驾照,但她比我更有车瘾。这次答应跟我回老家过年,一半的原因是她想跑个长途练练车。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好下来,坐到后面去,和儿子刘东坐在一起,副驾驶我也不愿意去呢。现在有身份的人都不坐副驾驶了。我儿子笑话我,老爸,你多大的身份呀?不就是个教授吗?还是副的!
这小兔崽子!我刮一下他的鼻子。
我儿子和他妈一样,老是喜欢和我对着干。
2
坐自己的车的感觉真爽啊,那个舒服呀。当然了,我知道,要是自己开车就更爽了。更当然了,作为男人,我还是把这种更爽的感觉让老婆享受吧。反正,男人这东西,路上开车也好,床上卖力开车也好,还不都是为了让老婆更爽啊!嘿嘿。男人这个动物,就是高尚,谁让咱是男人啊。我买了一些土特产,买了几箱子好酒,装在后备厢里,咱再也不用大包小包拎着上下班车了。我老婆想到高速上跑跑试试,我说,还是算了吧,咱们都是新手,上了高速不敢跑耽误人家的事,自己还危险,就走国道就行了。张朵也没有坚持,挺直身板,全神贯注地握着方向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我搂着儿子,看着车窗外的树木和村庄。齐刷刷地向后倒去,兴奋极了。我看得出来。我老婆张朵也很兴奋,这个娘们,平时做关键事的时候都不爱兴奋。一开上车竟然兴奋得要唱歌了。怪不得人家说,这车比伟哥还好。原来我还不信,现在我知道此言不虚。不说别的,自从买了车,我们的那个“生活”就比原来频繁了不少,真是实践出真理啊。嘿嘿。
我和张朵商量,我说,老婆啊,快到棉花凹的时候,咱们就换过来,我开着进村,你给我点儿面子啊。我老婆张朵扭过头来,哧哧笑了一下。说。好好好,给足你面子,行了吧。
快到棉花凹的时候,我说,停车,停车。我来开。张朵这次倒是听话,没和我对着干,找了个宽敞的路边停下,从驾驶室里下来,说,累死我了。累死我了。脖子都累疼了。我也从车上下来,说,人家开车累腰累手,你累脖子?张朵说,别啰嗦,快给我按按。捏捏。张朵有颈椎病,我经常给她捏脖子;其实我也有颈椎病,但是她却不给我捏脖子,每次捏不两下就喊累。颈椎病是教师和护士的职业病吧?我看看左右没人,用拳头轻轻给她砸了两下,叉捏了捏肩膀,她伸一个懒腰,说,舒服。舒服。我说,好了,好了。赶快回家吧,回去晚了都吃中午饭了。我拉开车门,钻进驾驶室。一坐在座位上,我就兴奋得满脸开花了。我拉上安全带,发动了汽车。我说,两位乘客坐好,走咧。车子拱了一下,突然又熄火了。咦,这不是让我丢脸吗。我的离合和油门没有配合好。张朵在后面笑坏了,说,刘刚,你到底会不会呀?我说。嗨嗨,着急了,不好意思。新手上路,请多包涵。我儿子说,老爸,您老稳着点儿。我操,这个臭小子,净学大人说话,真是个对头!这次我没有惊慌,慢慢加油门,慢慢松开离合,车子稳稳地启动了。
这就是我的家乡啊。一条熟悉的柏油道,两边是平平的麦田。麦田里不时就有几个大棚。还有几家厂子,什么板皮场,饲料厂什么的。零零散散的村庄,错落有致地布置在平原上,而前面不远就是生我养我的棉花凹了。前几天打电话,我爹说我们这里开始小城镇化建设了,五年之内,这些零散的村庄将不复存在,我们红瓦乡将要建设两个现代化社区,全乡的人都搬迁到那里去。一律的楼房,沿街房,还有花园,学校和卫生院什么的。我的故乡啊,我的村庄,它将不复存在。一股苍凉涌了上来。我对张朵和儿子说,你们看,再过几年,想回棉花凹也找不到了。儿子说。那棉花凹上哪里去了?我说,都要搬迁到乡镇上去了。儿子,好好看看吧,这里才是你的祖根哩。张朵反感了。说,刘刚,大过年的你干啥呀?都城镇化了那是好事呀,你还哭鼻子不成?儿子。别听他瞎咧咧。我只好闭了嘴。专心开车。
突然,我看见一个人背着一筐柴禾在前面踽踽地走着,那个身影怪熟悉。三叔。我吱的一声停下车,说,那不是我三叔吗?张朵看了看,说。三叔又怎么了?快走吧。开车。我说,我看见我三叔了,我怎么能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呀,我得打个招呼。当年我没有给我堂弟刘全安排好工作。我心里有愧。在棉花凹,到处都是我的恩人呐,我开了小车我可不能充大,眼睛里看不见人。要是那样让他们知道了,棉花凹的人就会嘲笑我这个人不仅没出息,而且人品也混瞎了,那可不行。我这开着小车回老家,不就是为了找回点尊严。不就是为了让棉花凹的人知道我没有忘本吗。我摇下车窗玻璃。喊了一声:三叔。那个人转过身来,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我说,三叔,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小刚呀。三叔这才明白过来,咧开了嘴,露出一嘴黄牙,说,是小刚呀。我还以为是哪个龟孙,不会开车,差点儿撞上我。我拉开车门,下车,说,三叔,是我哩。三叔不看我,却伸着脖子看车。疑惑地说,你的车?我说,是我的。三叔把手搭了罩子搁在玻璃上往里看,因为我玻璃上贴了膜,往里看黑乎乎的看不清。三叔说,谁在里面?我急忙把车门拉开。说,张朵,是三叔,还不喊三叔?张朵白了我一眼,只好咧嘴,喊了一声三叔。三叔说,是侄媳妇呀。好几年没回来了吧?张朵扭了脸,不说话。我急忙给三叔递烟,说,去年还回来了呢。在我们棉花凹,媳妇好几年不回家来,大家就都议论这媳妇子不懂事。我看张朵有些尴尬,急忙把烟给三叔点上,说,上车一块儿回去吧,三叔。我小时候有一年病了,发烧,我爹不在家,是我三叔背着我跑了二十多里路给送到医院的,这么多年了,一看见三叔,我仿佛还听见他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三叔看了看我,嘿嘿地笑了笑,说,你们快回吧。我还背着柴禾呢,其实,我也就是让让三叔,他要是真上车。我还真没法拉他,他的柴禾总不能塞后备厢里吧。三叔是个明白人,不上。三叔说,小刚是个好孩子。三叔用手拍拍车盖子,说,小卧车好。我还没坐过哩。我说。那三叔你就上去坐坐。三叔看看张朵,又看看身后的柴禾,说,算了吧。我没这福,你们先走吧。三叔又用手拍了拍车棚子,我儿子突然喊,你个老头子别乱拍,拍坏了你赔不起!三叔吓得急忙缩手。我气坏了,说,小王八羔子,你有没有礼貌!三叔说,孩子小,快走吧,你们。快走吧。我急忙道歉,请三叔原谅,我管教儿子无方。三叔一挥手,说,没事,回家。回家。说完,三叔背起柴禾,撅着屁股先走了。我怏怏地踩灭了烟,上车,回头对儿子恶狠狠地说,你小子回老家给我老实点儿!三叔生气了。张朵得意地坏笑,说,活该。活该。谁让你自作多情。你就不该停。我叹一口气,说,你不知道,三叔那时候对我可好了。可是今天这事弄的,唉!
进街的时候,我故意把车速放慢,把车窗摇下来,慢慢地从街上过去。不时地给站在街里的婶子大伯打着招呼,“二婶子,闲着呢?我回来了。…‘大伯,家里玩去呀,我不下车了。”他们听到我的招呼就缩了头往车里看,看清了,说,“呀,小刚开车回来了。”我点着头,心里充满了幸福。老远看见我爹和我娘在我家大门口站着,周围还有一圈人,看来他们早把我开车回来的事宣布出去了。我对刘东说,“东东,看,你爷爷奶奶接你来了。”我儿子大喊,“停车,停车,我要下车。”我把车停在大门口,刘东早拉开了车门,扑到奶奶怀里去了。前几年,我娘在我这里替我们看孩子,刘东就是他奶奶拉扯大的,他和他奶奶亲。停好车,我和张朵也拉开车门下来。我爹过来,他还有些腼腆呢,也不说话,看着我们只是笑。我说,“爹。”张朵也喊一声:“爸。”再没了话。可我看见我爹脸上的皱纹都开成鲜花了。旁边的几个人都围上来打招呼,我急忙从车里拿出两盒烟来,塞给我弟弟,让他替我散烟。我一个个地握手打拱,问好。他们都围了我的车看,说,这车好。这车气派。又问我多少钱买的,我故意多说了几万,他们就都赞叹,说,还是人家刚子混得好,当大学里的教授不说,车买的也上档次。我谦虚着,喊他们进家喝茶去。
到家里泡了茶坐下,都说这茶好。是碧螺春吧?也有说是铁观音的。其实,这茶一般,不过是一般的绿茶。但是我并不去辩解,由他们说去。我娘拉了刘东,携了张朵早坐到炕上去了,炕烧得滚热,一路上冷脚冷手的,坐上去暖和。三婶子二嫂子几个也跟进来,围着说话。我娘拉了板凳椅子,大家都坐了。又拿出糖果来分给大家吃。我们在堂屋里喝茶,堂屋里冷,我爹捅了炉子,又使劲加了几块木炭,屋里顿时暖烘烘地热起来。我在路上还觉得有些冷,这一烤炉子,也不觉得冷了,心里一股一股暖暖的。很久没有见我的这些叔叔大伯和堂兄堂弟了,我也早不说了普通话,一律换上了方言,这家乡话一说,满屋子都透着亲切。
李小强是我的邻居,也是我从小的伙伴,听说这两年开了个饲料厂,发财了。听说我回来,揣了两瓶酒过来嚷着要和我喝酒,我说,好,好,喝酒。今天中午谁也不许走,咱们在这里喝个痛快。我爹早把一盆切好的猪头肉和猪杂端到炉子上温着,说,今天都别走,我都准备好菜了,中午就在这里吃。又喊我娘,说,刚他娘,刚他娘,把那几个凉菜端上来呀。我娘在西屋里应了,说,马上来。马上来。
我也起身,去后备厢里抱出一厢好酒来,说,就喝这个吧,我带回来的。张朵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白了我一眼。我装作没看见。李小强看见了。打圆场说,你是教授就喝你的酒呀?你这个酒是孝敬我叔的,咱今天不喝。喝我拿来的这个,梁山义酒,咱家乡的酒。不比你的差。我看了张朵一眼,也就不再坚持。梁山义酒是我家乡生产的好酒,也不错。据说很畅销。在梁山喝酒,一般都喝这个义酒。我觉得除了是本地酒外,关键是个“义”字,在我的老家梁山,男人在一起,最经的就是个“义”字了。那就喝义酒。
李小强说,不喝义酒喝啥?男人们吗,不就是活个义字嘛!
刚倒上酒。我的堂弟刘全从门外进来了。他说话有些结巴,他推开门,说,哥,哥,刚子哥回来了?我说,刘全呀,快来,快来,倒上酒!刘全说,我,我,我刚听听我爹说,你,你你回来了。开小车回,回来的?我说,我说呢,我刚才在路上遇见我三叔了。刘全递了烟给我,给别人也分了一圈,烟上印着外文,我不认识。李小强说,刘刚你不知道吧。你兄弟刘全出国了,刚回来的。刘全出国了?我问,有些惊讶。打工,打,打,打工。刘全说。我大概有五六年没见他了吧,从那一次在我那里住了几天回来后,一直没听说他的消息。我问他去哪个国家打工。他说去的是阿尔及利亚。我有些吃惊,非洲呀?怪不得晒得这么黑!大家就都笑了。刘全说,我,我,我在那里——就。就算白色人种了。大家又笑。李小强开他玩笑。说,你不仅算白色人种,你在那里也听不出你结巴来吧?刘全脸红了一下,说,去你的,滚。大家又笑,说,刘全,你说滚倒不结巴。大家又笑,刘全也笑了,吃吃地。
刚喝了一杯,我娘过来喊我,她说,刚子,你出来一下。我娘表情神秘,我只好跟着进了里屋,说,娘,啥事呀?还这么神秘。我娘关上门,说,你得开车去接你四叔一下。你四叔在县城西火车站下车,刚才打电话来了。今天年三十了,没有班车了。我说,我四叔这是从哪里来?我娘说,你四叔出门打工二三年了,从南方来的。刚才打电话给你四婶子,说是没有班车了,让你四婶子骑自行车接他去。二十多里路,你四婶子咋去?这不看见你开车回来了,你四婶子就找我来了,说,想让你去接接去。我说,娘,我这不正喝酒吗?你怎么给我揽活?我娘说,我看你四婶子推了车子怪可怜,这么冷的天,你让她咋去?她来开口了,我还能说不行?我说,要不让张朵去吧,我喝酒了,不能开车。我娘脸就黑了,说,你不想去?你可别忘了当年你上高中交学费交不起,是你四叔拿了钱给你垫上的!我说,你看,娘,别生气,这不是喝酒吗?娘说,让他们喝着,你开车去还不快?接了你四叔回来喝酒。我说,喝了酒不能开车。我娘说,你才喝了多少酒我不知道?喝多了我能让你去?!我说,张朵……我娘拧了我一下,说,张朵,张朵,干啥事就知道喊张朵,你还是个老爷们吗!刚才张朵在那屋里说一路上是她开回来的,说你开不好,你婶子嫂子都笑了,她们笑话你不如个女人哩。你这个没出息样!
好好好。我去还不行。我去。我马上去。我说。唉,我娘这个人呀,真是的。
我拿了钥匙出门,张朵看见了,跑出来说,刘刚你干啥去?
我说,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
张朵说,去哪里?你喝酒了你不知道!
我没说话,开了车门坐进去。张朵生气了,一把拉开车门正要大嚷,我娘出来,一把拉住张朵,说,东东他娘,刚子出去接他四叔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咱进屋去。张朵张了张嘴,看看我娘,没好意思大喊。我趁机把车开出去了。我看见张朵气得一转身进屋去了。
操。这是在棉花凹。不是在省城。我嘟哝着。给自己壮胆。忽然有了勇气。
3
接了四叔回来,又喝了两杯。我就有些微醉了。刘全说,刚,刚子哥,你晚上,你,你上,我,我家喝酒吧。我、我,我来就是专、专,专门来喊你去,去、去我家喝酒的。我说,我都喝醉了,晚上就算了。刘全说,那、那,那可不行。我来的时候我,我,我爹说了,你一定要把你,你,你刚子哥请到咱家来,来吃晚饭。我爹现在在家里正,正,正杀鸡呢。我说,三叔杀鸡呢?刘全说,可、可,可不是。我爹在旁边说,刘全你回家吧,告诉你爹,晚上你刚子哥就去。刘全就笑了,说,大、大爷说了,那就准、准了。我也只好说,我一定去。刘全踉踉跄跄地回家去了。
我说,爹,你怎么就答应了他了?刚才李小强喊我晚上去他家呢。我爹说,谁喊你你也得先去你三叔家看看。我说,咋了?我爹叹口气,说,你不知道,你三叔快不行了。我一惊,说,啥?我三叔怎么了?我爹说,得了孬病了。肺癌。我的头就蒙了,想起刚才在路上三叔呼哧呼哧喘气的样子,怪不得呢。
我爹说,你忘了谁,你也不能忘了你三叔。你三叔帮了咱家大忙了。我说。咱家怎么了?我爹说,你可能不知道,秋里的时候,我崴了脚。又犯了痔疮。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咱家里那些地,全指望了你三叔帮咱收回来的。我说,爹你什么时候崴了脚?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爹摆摆手,说,都过去的事了。给你打电话你能回来割豆子?你能回来掰玉米?你能回来耩地?别说你了,你弟弟出门打工,回不来,地里也全仗了你三叔。我说,都是三叔给收回来的?我爹说,你三叔别看干巴,是个干活的好手,五六亩地的玉米豆子,都是他给掰了割了,拉回来收进囤里的。我要给你打电话,你三叔不让,说怕耽误你工作。
我的眼睛有些热,三叔啊,三叔,从我小时候,我爹当民办教师,顾不得地里,他就没少帮衬了我们。三叔真是我们家的恩人呢。我爹说,其实,不光你三叔,你二伯,你大伯,咱们村上的哪个人没有对你有恩呀?我低下头,心里翻江倒海。这事我知道,当年上大学,交不上学费,就是这些乡邻乡亲你五十他一百给我掏的钱,后来,我娘说,还人家钱,人家都不要,说就算是随礼了。咱庄稼人随礼都是三十二十的,哪里有随那么多的?还不是人家帮助咱?
我爹说,你平时忙工作,不在家,咱家里有什么事还不是这些邻居百舍地帮咱们。你可不能忘了棉花凹,我说,我咋能忘了棉花凹呢。我爹说,你当了教授,你在棉花凹也是个小字辈。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一会儿我提了东西看看我三叔去。我爹说,你去吧。我柜子里还有豆奶粉啥的,都给你三叔提上。我说,我车里有。我都买好了。我提了两瓶好酒,又拿了豆奶粉和一箱牛奶,去三叔家。张朵看见了,说,刘刚你去哪里?我也跟你去。我说,我看看我三叔去。你也去吧。张朵说,三叔呀?那我就不去了。我说,三叔你咋就不去了?张朵说,我还得帮娘炸丸子呢。我说,那好,你好好炸,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张朵说,那你可少喝点酒啊。我说,知道了。
我先给李小强打了个电话。说我晚上过不去了。李小强说,我找你还有事呀,你可得帮我。我说,有事咱们说事,明天再说吧。我要去看看我三叔去。李小强说,去看你三叔呀?那你去吧。去了三叔家,三叔已经把鸡杀好了,三婶子正烧了柴火锅在那里炖鸡。三叔看见我,急忙迎出来,抓住我的手,说。小刚来了。又往屋里喊。小刚来了。刘全就出来招呼我,三婶子也过来和我说话。三叔家我从上学的时候来过,得有十几年没来过了吧。这个小院子还是这个小院,破旧的土墙,破旧的房子。三叔这个人在我们村上是个不招人待见的人,除了邋遢,长得丑陋之外,三叔的肺病据说还传染人。原来的时候三叔就有肺结核,喘气粗,小孩子们都不愿意接近他。我也很少喊他三叔。很少和他说话。知道了他得了肺癌,和他说话就有了些疑忌,我扭着头装着打量四周。尽量不和他靠近。心里却有一阵一阵的悲凉。我把酒和牛奶还有豆奶粉递给三叔。三叔颤抖着手直推让,我坚持放下,他才接了。三叔说,大侄,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刘全兄弟有了对象了。我一阵惊喜,因为结巴,又因为穷。我听我娘说刘全二十六七了还没找下对象,这下好了。我说,哪里的姑娘?订婚了没有?我三叔说,前天刚相见了,两个人都没啥意见,姑娘不孬。我说,那就好,那就好,这是大喜事,到时候我得来喝喜酒。三叔脸上乐滋滋的,说。刘全出国打工挣回钱来了,过了年春天就盖房子。我说,是得盖房子了。
三叔趁刘全去厨房端菜,悄悄给我说,大侄,人家姑娘就嫌一样。我说,嫌乎啥?三叔说,嫌我这个老病根。我说,这就是女方的不对了,父母得好好孝敬,怎么能嫌乎?三叔却兴奋地说。不过不要紧,她很快就没得嫌乎了。我说,为啥?三叔说,你还不知道吧?你三叔快死了。我虽然知道三叔生病,但是没想到他说话这么直接。我吃惊地看着三叔,说,你这是说啥话呢!三叔说,真的。我让你来就是让你劝劝你刘全兄弟。别给我看病了,瞎折腾钱,没用,还是留着以后过日子吧。我说,这怎么行?三叔说,你刘全兄弟太傻,挣几个钱回来不容易,还非要拉我去化疗,我化什么疗?白折腾钱。我还要说什么,刘全进来了,三叔使个眼色,我们都不说话了。
喝酒的时候,三叔不上桌。他让三婶子给他单独拿碗盛了点菜,倒了杯酒,坐在离我们很远的床沿上吃。我喊他上桌来,他不来,他说,不行,我这病传染。我眼里突然有了泪,哽咽着把酒喝下去。那一顿酒我不知道怎么喝的,反正什么也记不清了,我喝了个大醉。我娘说,我是被我弟弟去背回来的。后来回想起来。我只记得我三叔求我帮他劝劝刘全,可这样的事我怎么能张得开口?我是不会去说的。我三叔很伤心,说我没出息,是个糊涂人。第二天早上,我把刘全喊来,我说,你要是想去省城给三叔看病,你就给我说,我帮着你联系医院。刘全眼圈红红的,说,那,那,那好。我说,走的时候我就带着你和三叔去吧,这病不能拖了。张朵听到了,使劲给我使眼色,我装作没有看见,我拍了拍刘全的肩膀,说,明天我就回省城,正好把你们捎过去。
我这句话可把张朵给气死了。管他呢,这是在棉花凹呢。
4
李小强找我是他饲料厂的事,我没想到李小强的饲料厂做得这么大,他告诉我,他这个饲料厂一年光交税就是三十多万。我张大了嘴巴。李小强开了一辆奥迪,我这车在他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李小强对我还是很客气,一点儿架子谱也不摆。他是想让我在学校生物科学研究所给他联系个教授做他的顾问。他说,在我们梁山老家,养殖业十分发达,饲料厂不少,但是加工出既经济实惠又可以快速增肥的好饲料不容易,他想请专家教授给做顾问,把饲料质量搞上去。这样他的饲料厂才有竞争力。我真是得对他另眼相看了,我说,行啊你。真有你的。他说,你就说这事好办不好办吧。我说,这是小菜一碟。我的同事中搞这些研究的有好几个呢,都很有水平,帮你请一个专家,这还不是容易的事!李小强说。那太好了。等你回去联系好了,我就开车去找你。先把教授请来看看,至于薪水嘛,没问题。我故意诈他说,你打算给开多少?他说。你们教授月工资多少啊?我说。教授级别的少说也得五六千。他说,我再开一份工资行不?要不就按年薪,到时候再谈。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牛!他说,办成了也请你做个名誉教授,好不好?
我哈哈大笑,说,有没有工资?
他也开玩笑说,当然有了,我给你股份行不?
那天是李小强开车,拉我去县城吃的饭。他找了一家最好的饭店,要了个包间,又找了几个朋友,陪我喝酒。喝完酒又去唱歌,最后又洗脚桑拿。这些我都笑纳了,洗完澡上了小姐,我正醉眼朦胧地准备接受服务,张朵给我打电话来了。她说,刘刚,你还没吃完饭?你在干什么呢?我只好撒谎,我说,在喝茶呢。她生气了,说,十二点了你知道不?我限你半个小时之内给我回来,否则我开车去找你,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我马上醒了酒,说,不行,不行,我得回去了。李小强笑着说,是不是夫人有令?不敢上项目呀?我说,哪里,哪里,我得回去了。李小强说,别价呀,俗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享受完了再走吧,你不会真的是怕老婆吧?我羞红了脸,说,走了,走了。穿上衣服就出了门。
第二天,张朵的假期到了,我们就得回城了。我说,这年过的还没有过瘾呢,就得回去了。张朵说。要不你继续在这里过,我和儿子开车先回去?我娘听见了。说,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你怎么能开这么远的路呢?还是让刚子开车。你们一块儿走。
我说,那我得带着我三叔。
我儿子刘东说,带那个脏老头子干啥!我瞪他一眼,说,没教养。张朵不愿意了,她心里也不愿意让三叔跟着,她说,刘刚你说啥?就你教养好?
我一看。这下完了,看来张朵要给我开战了。她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呀。在棉花凹,我总不能就这么丢脸吧?我也生气了,把车门一关,指着张朵说,你给我闭嘴,你信不信我抽你个嘴巴?我从来还没有这样对她说过话,张朵一看,马上撒泼起来,她说,你打,你打,你打不死我你不姓刘!
我说,不就一个破车吗?别人坐坐还怎么了?张朵说,破车也是我的车,你凭什么自己随便做主。我也生气了,我说,我这就把车砸了。我拿了一块砖头,想吓唬张朵。张朵没有被我吓住,夺了砖头就拍到车上了,车灯都打碎了。可把我疼的!妈妈的,反了!
李小强过来了,他拉开我,把我臭熊了一顿。他说,弟妹,你别和他一般见识,他这个人,我收拾他。我爹也生气了,照我屁股上踹了一脚,说,你就这点儿出息!你照媳妇发什么疯?你照我来吧!
张朵一把夺过钥匙,钻进车里,发动开汽车,对我儿子喊,东东,咱们走,咱不管他!我儿子也吓坏了,乖乖地钻进车里。这个臭娘们,一加油门,他们娘两个竟然自己开车走了!
我爹要让我弟弟骑了摩托车去追,他怕张朵带着情绪路上出事故,我把他制止了,我说,算了,算了,别追了。越追越容易出事,让她消消气,路上应该没什么大事。李小强也说,没事,没事,别追了,让他们先走吧。一会儿,我去送刚子去。我把他送回去。
进了屋,我爹气坏了,我娘也气坏了。我爹第一次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呀你,就是个没出息样。你可把我们家的脸给丢尽了!你就这能耐呀,你就只有打媳妇的能耐呀?你还开车呢,本想着你开车回来也长长脸,给乡亲们办点事,你倒好!
我娘却是生张朵的气,我娘说,一个女人怎能这么不给自己的男人留脸?这可不是咱棉花凹的媳妇能做的事!数落了半天,我说,怎么办?刘全和我三叔还等着跟我的车去省城哩?我娘说,李小强不是说送你去吗?让他们跟着他的车去吧。你看看你,你看看人家小强。你怎么混的你呀!
我也决定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刘全突然跑过来,哭着说,不,不,不好了,我,我爹他上吊了。
什么?三叔上吊了?我拔腿就跑,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了,我心里想,这个三叔咋这么傻呀!你说说,我这开车回家,惹得是什么事呀!
这叫什么事呀!
下一次,我是再也不会开车回棉花凹了。
我飞奔地跑着,脚下被我踢起了飞扬的泥土,我仿佛听见三叔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气,我正伏在他的背上,他撒开脚丫子,背着我,正往二十里地外的县医院跑去。
责任编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