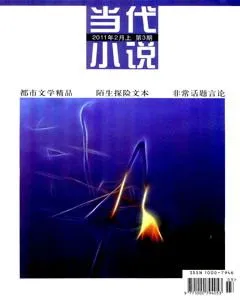晓看红湿处
周五的黄昏,厉义气走了米非。米菲走的时候,动静很大,翻箱倒柜的,收拾了整整一箱子的衣服,像是准备进行一场长途旅行。厉义就猜想。米菲之所以把出走的前奏弄得这么大张旗鼓,无非是想给厉义挽留自己争取点时间,厉义并不为所动,稳稳地坐在沙发里,颇有些冷漠地注视着米菲的一举一动。米菲在最后扣箱包的锁扣时显得有些烦躁和不安,连扣了几次都没有扣好,手指都有些发抖了。抖了几次,实在找不出再拖延下去的理由了,“啪”的一声。终于扣好了箱包的锁扣。拖着那只硕大的箱包,米菲头也不回地就出了门。在门被米菲重重甩上的那一刻,厉义轻轻舒了口气。
窗外。一支玉兰花的枝桠斜在黄昏的暮霭里,白日里看着玉白的花骨朵此时呈现出好看的暖黄色,窗台上一溜码开的啤酒瓶齐齐敞了口,像是有无限的心事想要倾吐似的。却是有口难辩的沉默和肃穆。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响了。
电话是鲍十月打来的。鲍十月在电话里问厉义干嘛呢。厉义盯着玄关处鞋柜上的那双木底拖鞋,告诉十月说,没干啥,我还能干啥呢?发呆呗。鲍十月就说。那出来喝酒吧,西街新开张的湘菜馆见。厉义有些懒懒地问,西街每天都有新开张的菜馆,哪家啊?十月说,就上个月才倒掉的那家彩票站,现在改湘菜馆了。名号叫鱼米乡。记得来啊?哥几个可都等着你呢。放下电话,厉义还在犹豫去不去,晚饭是吃了的,不过只吃了一半,桌上还放着只动了几筷子的“残羹剩炙”,醋泡花生,宫保鸡丁,还有米菲拿手的鱼香肉丝。醋泡花生是每餐必有的下酒菜,鱼香肉丝里的木耳不怎么好,米菲抱怨说小区里的木耳卖完了。在一个面生的妇人那里买的,经水一发,异常的发达,水性太大,切成丝下了锅,油星四溅,噼啵作响。惊得米菲在厨房里尖叫连连。想起米菲,厉义还是决定出去喝这场酒,有那么些类似青春期的叛逆意思在里头。厉义去洗了把脸。又望了望鞋柜上那双被米菲郑重其事摆放在那里的木拖鞋,换了件衬衣就出门去了西街。
厉义喝完酒回来已经是后半夜了。
进了门,厉义把钥匙呼啦扔在门廊的鞋柜上,碰倒了一只木拖鞋,拖鞋砸在鞋柜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换鞋的当儿,厉义一偏脸就看见了那只旅行箱。厉义心底冷笑了一下。换上了拖鞋。厉义去了卧房,打开灯。只见米菲把自己裹在被子里裹得挺严实,只一头黄色的长发从被子里铺散了出来,头发是今天才染的,衬着银灰色的被套那头黄发给了厉义几分陌生感,像外国电影里的某个镜头。被子下面一动不动,厉义盯着这幅带着几分陌生感的场景停滞了片刻就抬手按灭电灯,退了出来。
回到客厅,厉义坐在沙发里发呆。茶几上,摔裂了的电视遥控器像个伤员似的被塑胶带捆绑着。是米菲摔的。不止一次。在很多次的争吵中,那只遥控器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那塑胶带就像是道魔咒。令那只遥控器逃脱不了自己被捆绑的命运。厉义看那只可怜的遥控器时就看到了那张压在遥控器下的便签条。取了来看,米菲张扬跋扈的几个大字写着:房子是我租的。要滚你滚!!!厉义不屑地冷笑了下,顺手将便签折成了一架纸飞机掷了出去。粉绿色的纸飞机在屋子里飞了一圈后稳稳地落在了那只被米菲拖了一圈后又最终拖了回来的旅行箱上。厉义伸手去衣兜里摸烟时才想起进门前抽掉了最后的一支香烟。
厉义决定下楼去买包香烟。
在门廊处换鞋时,厉义又看了看鞋柜上的那双木拖鞋,本想伸手去扶那只先前被碰倒的木拖鞋的,手伸出去了,却在半路停了下来。今天和米菲的争吵就和那双木拖鞋有关,干嘛要去扶起那只被米菲示威一样地摆放在那里的东西呢?这么想着厉义就带上房门下了楼。
楼下的小卖铺已经打了烊,厉义向小区外走去。月色很好。道路上空无一人。路灯早已熄了,这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区,像厉义和米菲这样的外来人口并不多见。小区里的人家该睡的都睡了,该醒的兀自醒着。醒着的也都醒在某扇亮灯的窗子后面,浑浑噩噩却也与世无争。出了小区,往东就是厉义方才回来时的西街,西街在这座城市的西边,在厉义和米菲住处的东边。
西街上,各个店铺前早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少数几家亮着灯的馆子也正张罗着收拾家什准备打烊。一路寻去,竟没有一家卖香烟的铺子。厉义却已是越走越远。先前被香烟逼迫出来的那份焦灼竟渐渐减弱了许多,厉义的步子慢了下来。
不觉就又走到了晚饭时和鲍十月几人一同喝酒的那家湘菜馆前。周边的灯光虽然暗淡了许多,但“鱼米乡”的喷绘招牌依然显得很招眼,网络上下载的一幅盛装土家族少女画像被移花接木地和店里隆重推出的几款主打菜组合在了一起,肆无忌惮地展示着属于草根文化的审美趣味。
店堂里的一个伙计出来收拾门前几把散落的椅子,站在明暗交界处的厉义显得有些可疑,伙计看了他一眼,认出了是晚餐时在湘菜馆喝酒的食客,点头打了个招呼。伙计嘴里叼了根烟,一点头,长长的一截子烟灰就掉了下来。厉义叫住伙计问他附近哪里有香烟卖。伙计想了想,摇了摇头。结果厉义其实是早就知道了,这条街道平日里没少走,印象中的几家香烟铺子这会儿都关了门。不过这一问自有它的妙处,伙计放下了手里的几只长脚塑料椅子,从衬衣口袋里摸出烟盒瘪下去很多的半包香烟来给了厉义。而后,伙计拾起塑料椅子回了湘菜馆。
接过香烟的厉义开始往家走,嘴上已经衔上了一支,手去衣兜里摸来打火机,打火机是一次性的,打了几次却发现也已是弹尽粮绝。厉义一扬手将打火机摔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啪”的一声却砸出一簇火花来。厉义心里的火也被激了起来,感觉今天真正的是干啥啥不顺。心情很糟糕的厉义走到楼下才又发现方才把钥匙落屋里了,厉义狠狠地跺了一脚单元口那扇老旧的木门,楼道里的声控电灯霍地就亮了。厉义的一张脸在那惨淡的灯光下却沉沉地黑了下去。
没错,房子是米菲租的。在厉义还没到来前就跟房东签了合约的。每月的房租也是米菲交的。那是米菲的钱。厉义并不是吃软饭的男人,在报社发行部打工虽没啥大的出息,好歹也是月月有进账的。只是米非似乎更懂得算计和经营。厉义的钱都用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上,米菲的钱却用来交了房租。尽管两人挣来的人民币都混在了一起,那钱上又没有写上各自的名字,但按照米菲的说法,用来交房租的钱就是从她米菲那儿出的、此时的厉义就觉得自己很冤,比窦娥还冤。
日常的开销是没有什么计划的,两人的饮食,其实也就是晚餐都由米菲安排。早餐几乎是不吃的,午餐都在各自的单位里吃。就只有晚餐,米非都尽可能地准备得丰盛些,厉义晚餐有喝点酒的习惯。米菲在这点上很迁就他。在超市站化妆品柜台的米菲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虽是租住的房子,日常的生活用品包括床上用品外带窗帘桌布甚至马桶坐垫都要精心置办,那只在厉义眼里幼稚愚蠢的木底拖鞋最能说明问题,买回来才穿上,大楼下的女人就顶着一头的卷发夹子找上门来了。拖鞋被当作装饰品摆在了门廊的鞋柜上,看着闹心。当厉义看到米菲今天花了180块钱染的那头黄毛时终于忍不住絮叨了她几句,连带着就又说到了那双拖鞋。米菲对厉义的不满表现出了极大的失望,米菲咬牙切齿地说厉义。没想到你堕落到这般田地,没品位没追求没理想没情趣,每天过这种除了吃饭就是喘气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头猪!厉义不知道一双拖拉板怎么就被米菲上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不可理喻!
贫贱夫妻百事哀。尽管两人目前算不得夫妻,可要以法律来界定也算是事实婚姻。尽管两人目前的状态已是准婚姻状态,可婚姻这个词对两人来说还是显得那么遥远。大学毕业四年了,工作从一座城市换到又一座城市,居无定所,风雨飘摇。
此时的厉义站在楼下的夜色里,感觉晚上的那场酒这会儿才上了头。嘴里衔着的香烟离了火就啥也不是,衔在嘴里除了自慰就剩下了傻气。啐出去会显出几分豪气和洒脱,可这黑漆漆的夜里啐给谁看呢,厉义把烟重新装回了那只瘪塌塌的烟盒里。抬眼望了望三楼的那扇窗户,里面还亮着自己出门时开着的灯,很忠实的灯光,
上了头的酒精就让这个时候的厉义想起了十月在酒桌上说的事来。十月是当地的土著,也曾浪迹天涯了好一阵儿。最终回到了铜葵。和厉义一样,十月也在铜葵的报社作发行。那家湘菜馆招牌上的土家族女孩是十月的女朋友,女孩叫黄羚,有着羚羊一般修长的腿,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披戴着隆重的民族饰品游荡在风景区陪客人照相,女孩把自己叫做人肉布景板,一个人头收取十块钱的劳务费。湘菜馆的老板不知从哪个网站的贴图板上搜罗到了黄羚的相片就拿来用了,被黄羚发现后不依不饶地找来理论,最后。在十月的调解下以老板请吃一桌饭告终。以十月的人缘很容易就凑够了一桌子,不过话说回来,这年月,作饭局的应邀嘉宾跑得都快。
酒桌上鲍十月很有些自豪,不断地向座上的人劝酒,一有空就把黄羚揽在怀里抚弄黄羚的头发。黄羚的头发很好,长长的,黑亮。十月注意到了厉义的眼睛总往黄羚的头发上瞅,就说,直板烫,就这一个头三百多块呢,黄羚骄傲地一摆头,抬手打掉了鲍十月抚在自己头上的手说,爪子拿远点,油刺乎乎的!这时的厉义就感到自己真像米菲说的是堕落了,堕落得连当今的头发烫没烫过都看不出来了,堕落得连直发也是可以烫出来的都不知道。那一刻他甚至对米菲花一百多块钱染头而给予的抱怨感到了一点小小的内疚。
黄羚中途接了个电话就提前离席了,对黄羚的行色匆匆鲍十月似乎习以为常,继续稳坐席间。看着黄羚的背影从湘菜馆消失后,酒桌上的气氛一下松散了很多,厉义除外的七个男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转到了黄羚身上,转到了女人身上。黄羚在时,席间也不乏对她的溢美之词,但那都是包在饺子里的暧昧馅子,太多的中国含蓄包在其间,未下口之前只能透过不太明了的外观去揣度其中味。现在则不同了,有如法式的汉堡,青凌凌的生菜融合了太多的奶油生猛地刺激着感官,每一句都显得那么生猛和鲜活。鲍十月呵呵地笑着,很满足地笑着。反倒是厉义的沉默更让鲍十月觉得可疑。鲍十月说,厉义,你小子一贯心里作事,想嘛呢?厉义心里想着。嘴上就不觉地溜了出来,这女孩脑子缺筋。说完了,又冒出了半句,十月你啥时候整了这么一个……话没说完,及时咽了回去。可毕竟晚了,鲍十月的脸一点点地黑了下去:酒桌上就有点沉默,鲍十月默了半晌,夹了筷子清蒸鱼放进嘴里,用手一点一点地抽出刺来说,管她缺筋不缺筋,也就随便玩玩。说完这话,鲍十月的脸色就不那么黑了,仿佛不好的气色都随着那些鱼刺被抽了出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就是就是,傻点好,十月又不指望和这丫头齐家过日子白头到老,缺筋不怕,丫头挺好,该凸的凸该凹的凹,女人该有的打眼望去啥啥不缺。听着众人的话,厉义就在心底感叹真是吃人的嘴短。
不知是出于补偿的心理还是炫耀的心理,鲍十月开始讲述他的情史。据鲍十月所言,截至目前他生命里经历了六个女人。听了这个数字,席间一片艳羡的赞叹声。鲍十月继续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他的讲述,他说撇去黄羚不说,其余五个女人中给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数第一个名叫翁虹的女孩,那时的翁虹和鲍十月都还纯情,该是看《在水一方》的年龄。可现实中的翁虹并不在水一方,现实中的翁虹就在鲍十月身边,一个活生生的,有着温度和美好的青春的肉体的女孩,就在年轻的、却多少带着点柏拉图情结的鲍十月身边。来自身体深处的声音告诉少年鲍十月这个女孩唾手可得。
不厌其烦地吃着清蒸鱼的鲍十月,带着难得的,对往昔抱着一丝回望的神情说,他的这一份自信来自女孩翁虹和自己交往的一招一式中。说完。就又纠正自己说应该是一颦一笑才对,一招一式对于那个年龄来说,太色情。太不纯洁。
鲍十月最终听从了身体的召唤。第一次对于两人来说都显得太过慌乱。那个炎炎的午后,在翁虹家那张狭窄的单人床上,面对第一个在自己面前衣衫褪尽的异性时,鲍十月积攒的所有对女性所持有的美好感觉都被摧毁了。他看着翁虹两腿之间的那个地方不知所措,鲍十月说,他被那黑糊糊的一片吓住了,那个地方和外国油画里所描绘的是那么的不一样,和自己臆想的也是那么的不一样。当他不能自禁地伏在女孩翁虹身上颤抖起来的时候,他看见了女孩翁虹眼里滚落的泪珠。鲍十月不明白,本该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怎么就会在尴尬甚至还有几分龌龊感里结束。
鲍十月吐出了嘴里的一根鱼刺,桌上的那条黄花鱼已经被他吃完了。停止了讲述,酒桌上的气氛忽然间就显得有些肃穆。众人仿佛被揭开了些什么似的,表情里不见龌龊,却多少有几分尴尬。坐在十月身边的一江为着打破沉寂,卖乖地说道,不算不算,十月你小子谎报军情,没弄成的也拿来凑数,明明四个硬说是五个,接着说另外几个。一江的话并没有得到响应。大家还是显得有些沉默。倒是十月打破了这稍显异常的气氛,如释重负地说,操!说这些干嘛?都他妈打鸣叫破了嗓子的老公鸡了,还搁这装什么雏啊?来,喝酒。
大家碰了杯,喝了酒,却发觉空气里那股怪怪的气氛依然没有消失殆尽。仿佛还差那么一点什么才可以推动谈话的继续。
十月就说,知道那女孩现在人在哪吗?就在东街的良友杂货铺。站摊呢。结婚了。应该过得还不错吧,多少年没见过面了,听别人说的。十月的这几句话终于使空气不再那么黏稠了,大家仿佛终于可以看到多年前那场被搁置下来的性事找到了突破口,像一部可以人库了的老电影般完成了它的圆满收场,
现在的厉义发觉自己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来到了平日里极少走动的东街来了。做发行厉义跑的是南区,作为一个外来的人,铜葵的东街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此时厉义的一双眼就不自觉地搜索起街边的店面招牌起来。“良友”杂货铺的招牌就在这时跳进了厉义的眼睛里,招牌下是扇窄小的门,店铺里亮着黄晕温暖的灯光。一个面容娟秀的女子怀抱着个孩子在柜台里一边摇晃一边走动着。厉义推门走了进去。
有火吗?厉义盯着那女人的脸轻声问道。有。建江,给客人拿个火机。女人冲着身后说了一句,厉义这才看到从女人身后站起的那个男人。男人给厉义取了只打火机放在柜台上,厉义摸了送进口袋,又看了女人一眼,转身正要离去时,女人说,嗳,您还没给钱呢。厉义这才回过神来,连声说着对不起就去口袋里摸钱包,却糟糕地发现,钱包竟放在那件白色的衬衣口袋里了。厉义一时愣在了那里,半天才艰难地说了句,不好意思,我,我这忘记带钱了。明天给你送来好吗?
女人有些迟疑,仔细地打量了一眼厉义,眼神里透着些狐疑。厉义就又说,你是翁虹吧?我一个朋友和你是中学同学。说完,看了一眼女人身边的男人又补充道,女的,是一女朋友。
女人开了口。女人说,我不是翁虹,那女的不干了,这店是我盘她的。厉义就有些始料不及,僵在了那里。柜台里的男人开了口,男人说,一块钱的东西,拿上先用吧,改天路过送来就是了。女人看了男人一眼,男人又说,这么晚了,店铺都关了门了,也难去别的地儿寻了。我们铺子开门开得早,关门关得晚,您以后多照顾就是了。女人这才对厉义露了个笑脸,怀里的孩子醒了,开始哇哇地乱哭,男人和女人就急急慌慌地哄孩子去了。
出了杂货铺,厉义点了掏出的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心里竟有些莫名的忧伤。
一根烟吸完,厉义正好回到了家门口。
抬眼望望,屋子里的灯依然亮着。上楼时,厉义摆弄着手里的那只一次性的打火机,就想起那只存放在茶几抽屉里的进口火机来,钢制的。说是防风。去年生日时米菲买给他的,漂亮得像个工艺品,一直没用。
厉义按响了门铃。不一会儿就听见米菲的脚步声,走到门前停下了。门里,米菲嗓音有些沙哑地问,谁啊?
门外,厉义轻轻舒了口气说,我,开门借个火。
责任编辑: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