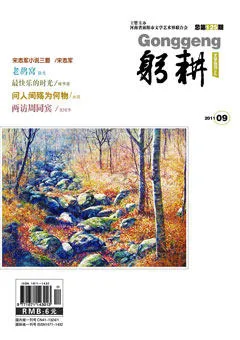沧桑断壁
一堵颓敝破败的断壁,在秋风瑟索的旷野里孤零孑立,凄清,苍凉。
阳光朗朗的,而深秋的田野却是一派荒芜,枯萎的谷蔸和零散的草垛,静静的没有半点生息。在断壁的前方,有一株岁月久远的枯树,没了任何的枝丫,只有那斑驳皴裂的树干,歪斜地挣扎着,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躬着腰,竭力地撑起枯槁的身躯。这情景,唯恐稍微的一点冷风,就将老人吹倒而再也爬不起来。
车翻山越岭,从玉屏过岑巩,刚刚进入江口境内不远,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寨子旁,蓦地现出了这格外打眼的景象。我们,都为此顿生莫名的惊讶惊奇!倘若,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这种萧瑟破败似乎很好理解;倘若,是在文革之初的动乱年代,此种断壁残垣也能勉强接受;然而,在当今经济文化背景下,在此畅阳开阔的田坝当央,兀然地耸立着一堵残破的高大断墙,怎么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从经济学、产业学、生态学,还是从人文学、民俗学、审美学的角度看,都是别扭与不合时宜的。强烈的好奇心让我们下了车,顺着弯曲窄小的田埂向断壁走去。
显然,那是一座大宅深院的院门前墙,虽然砖石残破,虽然杂草蓬生,但那高大的院门和厚实的墙壁,还隐隐地透出当年的巍峨与显赫。我思忖着,在这闭塞的贫穷山沟里,难道还曾经居住过腰缠万贯的巨富,抑或是威震一方的权贵?如此高墙大宅,毕竟不是一般人家所能建造,不是几个银两便能所为。或许,这曾是一处香火旺盛钟磬鸣响的庙宇?不管是宅院还是庙宇,这地盘肯定是精心挑选的。就是我这不懂也不信风水的唯物论者,也看得出这是一方风水宝地。宅院于大田大坝中坐北朝南,背靠苍莽,左右青山蜿蜒,正面冲谷开阔,视野无际,清清溪水淙淙而去;向阳望水,左右拱护,正与儒学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风水,毕竟是靠不住的东西,这不,眼下就是最好的明证:
显赫辉煌昨日是,残垣断壁今朝非。
世间一切,原本就是没有个定数的,凡事都在兴兴废废与轮轮回回中衍变。纵如此,我还是婉惜地慨叹着世道沧桑、际遇颠覆的不测、不幸与无奈。
大宅院的主人究竟是谁?我们转到了断墙的正面。哇!我们不禁惊叹正面高墙的富丽堂皇与奢华显贵!这气派,显然不是独家所居的宅院。要么,是一个大家族的合院,要么,就更像祠堂或寺庙。高墙,构筑在大礅石修砌的高坎之上;大门,用巨型块石拱构,庄重而霸气。整个面墙,雕凿錾镂有象征富贵与权势的云水蛟龙、珍禽奇兽、名花异卉、高官大宦等图案,两幅长长的对联,更增添了不少的儒雅斯文之气。遗憾的是,这所有的图案与字迹,全部被锉凿一尽,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万分惋惜中,我们竭力分辨高墙上部的那三个大字:最下那个应该是个“祠”字,上面那个像“王”,又像“三”,但还是更像“三”字一些,中间那个像“魂”像“皇”像“鬼”,到底是什么,说不准。从这三个字看,这是一个家族祠堂无疑。我们猜,叫“三魂祠”?叫“三皇祠”?叫“三鬼祠”?
至于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高墙上的累累创伤与斑斑凿痕,就像是一锤一錾地凿在我的心上,痛得钻心!那每一条凿痕,那每一道錾印,都是民族文化痛苦呻吟与汩汩流血的创口。时光让创口结了厚痂,而现在突然被生撕硬扯地揭去血痂,鲜血从心尖再次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我痛苦地闭上双眼,不忍目睹。而这一闭上眼睛,却又仿佛回到了童年。眼前浮现出文革初期的一幕幕:红卫兵对所有的“封建主义”糟粕,一律损毁,而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就连城内钟鼓楼上的精美雕饰,都被悉数錾凿。疯狂了,到处都是彻底砸烂封资修的狂热口号,到处都是打砸抢的暴力之声。
图案被錾凿掉了,可这祠堂呢?祠堂又哪去了?整个祠堂都不复存在,为什么偏偏还残留下这一堵门墙?可以断定,这堵门墙,一定是费了很大力量才保存下来的。这保护的力量,不知是灵肉血火,还是坎坷劫难。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是拆除祠堂时,它能侥幸地留存下来;二是若干年来基本农田建设,它仍旧顽强地于石缝中存活过来;三是若干年来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竟也没能将它撕碎。姑且说祠堂是文革时期被拆毁的,那么,当时能保护这堵门墙的人,应该早已作古;而今它犹存依旧,显然还有另外的人在继续保护着,世世代代,延绵久远,莫不是哪个家族暗中明里的力量?
那么,祠堂又到底是哪个家族的呢?在小寨上,我们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个半百老妇。她说那是“王家祠堂”。我们认定那墙上是“三”字而不是“王”字,便问,你们寨子姓王?她说不是。那这是哪里王家的祠堂?她一脸迷茫,说是嫁到这三十多年了,并不知晓个中二三。带着疑问与好奇,回到家后便上网查询,什么“王家祠”、“三魂祠”、“三皇祠”、“三鬼祠”都不是,我又输入“三槐祠”进行百度,终得正解。“三槐祠”,确为王氏祠堂。说的是北宋兵部侍郎王佑,曾栽三棵槐树于庭前,号为三槐堂,并预言“吾之后世,必有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真任了宰相。其孙王雍、王仲、王素分别任兵部、户部、工部尚书,兄弟同朝,位居三公。三槐祠,由此而名,遍及天下。
眼前的“三槐祠”,是江口哪个王家修的,祖上如何,今天怎样,我不想也无力去打探;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王家当年家道中兴,能在这穷乡僻壤里修造规模宏大的祠堂,也确是光宗耀祖;莫不今日,没了昔日的荣耀与显赫?不过,也许更加富裕显达,只是没了那份操劳的心肠。当然,不管贫富贵贱,不管张扬收敛,平安度日便好。沧海桑田,不由任何人臆想与操控,日月天天明,山水年年青。只是面对这残破的断墙,心里总是耿耿。少一点折腾吧,我们的民族历经的坎坷与创痛太多,无论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还是民族经济,大家都少来点摧残与破坏,多来点呵护与建设。也正因此,我又多么地希望今日的王家后嗣,能重修家族祠堂,光复传统的民族文化;须知,盛世修典呀,而今普天之下,哪里不在大张旗鼓地轰轰烈烈地对民族文化大兴土木?
断壁,仍凄清孤零地在秋风中茕茕孑立,与枯树形影相吊,相约而伴。它们像一对饱受磨砺的沧桑老人?是的,一对沧桑老人。然而,我更觉得它们像两面锈迹斑斑的铜镜,在映照着我们的灵魂,也映照着我们的行为,它艰涩而沉重地告诫我们:走好每一步,岁月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