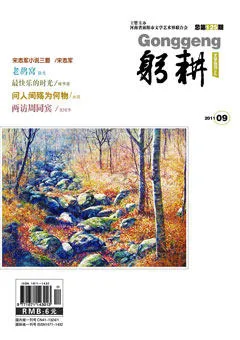凹汉底层诗选
一直在路上
一双脚磨平如镜 磨红
如血 一次次风雨兼程
赶着刻满太多皱纹的空寂
四合院 青山怀抱朝阳
花蕊绽开芬芳 赶着
时光的碎影 躲进墙壁
愁眉不展 一头老黄牛
在四月青草丛 咀嚼
从二娃子笛孔中
出逃的一个音符
嘶——无痕 无迹
一次次 赶着千里之外
辽阔的海尔路工业园
大车间 饥饿的睡眠
在秒针末端滴答流逝
月色在机器齿轮转动中
越发苍白 赶着
巨大广告牌上 一个
赤裸媚眼儿 抛过来
三尺欲望 一只流浪猫
在寒夜毛骨悚然 一颗
骚动的心 枯竭于
十二小时冷漠的灯光
一双脚 只有以这样
一个打工身份漂泊十年
才能在乡下与都市之间
扎实结合 累之上
是故乡田 而
苦之上是故乡草
一辆都市马车
马蹄阵阵 一个人
在一场都市的相遇中
疾驰走过
凝望着麻花辫子
从尖到根红黄卷烫
偷窥到花布衬衣
从内到外超短低胸
韵味悠然的一点乡音
都在冷血的鸟语中
漠然 再漠然
蒙着一层轻盈的面纱
一辆马车从他身旁
风儿般走过
是因为一层面纱
还是因为他本身的容颜
一辆马车急急匆匆
又从城市赶回乡下
可他为什么还是抓不住
黄昏 一抹夕阳
一条在胸口上奔腾的河
车满为患
每天在某五星级大酒店
门口 从车位草坪
到斑马线 横竖躺卧
别克 宝马 奔驰 雪铁龙
优雅身姿 与旋转座椅
寂寞难耐 225马力
燃油直喷发动机蠢蠢
欲动 像一群脱去
贵族外衣的君子 在集体
摆弄或裸露丑陋私物
偶尔射出来半米尾气
比骚尿更刺鼻
这一辆辆 配置昂贵的
重金属雕塑 有四眼无一珠
铁脑无一思 有血盆大口
水桶之胃囊 只喝
柴油或汽油 偶尔犯混
发飙起来恍恍惚惚也喝血
喝光我一个沉默寡言的
甘肃同事 刚过完二十一年
蓬勃的汩汩鲜血 车满
为患啊 车满为患
在某某都市
我漂泊的打工生活
在大片黑夜孤独升起
在大片烈日炎炎的柏油
马路 汗流浃背东奔西波
一个妩媚细腰的女人
纤纤手指一直抚摸在
一张圆滚的大肚皮上
是以少许姿色和肉欲
抚摸出 一枚金色
戒指 一辆高级轿车
一栋别墅新房 一叠
钞票在商场如流水漂漂
我不禁遥望着那枚
金戒指 质问缪斯女神
伟大的理想是什么
卑微的诗歌算什么
煤躺在秋日暖洋洋的床铺
历经千年地质演变的旅程
脚上磨出厚茧 额前爬满
皱纹 唯一不变的是那身
肌肤 乌黑透亮
一直沉默在瞳孔中
越来越深邃
很少有人 会关注
煤的肌肤里面 那些
把煤从十八层地狱
挖出来的矿工兄弟
一辈子抬不起的钢盔帽
不见阳光的深隧道
是一片翻滚的红色汪洋
数个矿难兄弟的灵魂
就在波峰与波谷中撕裂怒号
依旧像生前那样乌黑透亮
干瘦如柴的四肢 还在
为老婆的新房梦 三个
娃儿的学杂费 继续
三千里乌黑而透亮
乌黑朝天 血红朝地
煤躺在秋日暖洋洋的床铺
合起眼睑 一直在
静静等待 一场大风起
一场大雪落 一堆在
炉痹上红旺旺的火苗
要把苦难彻底燃尽
在洗浴城聆听唢呐声
聆听与我一样 在异乡的
落魄人 左臂上乘龙
右臂上乘凤 密发之上
乘着午后的七彩虹
这些光鲜的外表之内
还乘着 他从天外
飞来的唢呐声
劈开一道浓黑乌云
巨大的紫铜圆盘
在飘散着啾啾喳喳
像大片野花绽放
大片青草儿鞠躬
大片马蹄声踏过脊梁
大片流浪的羊群
在拥挤着穿过细密齿缝
六指在不断沉浮
圆盘之上的六个小孔
还飘散出来大片麦地
那被麦芒一针针刺破的
落日 一声声淹没在
数根香烟袅袅中
一声声在灵魂之上
像大片咸咸的
海水漫过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