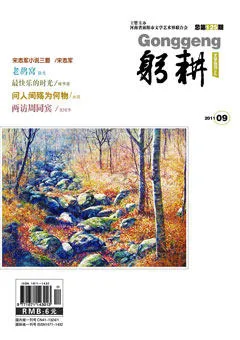夜的突奔
夜色浓稠,刺开它一角的是明亮的车灯。风在车窗外撞击,仿佛扯着裂帛,尾随着车的只有天上的星星,没法分辨出是哪一颗一直在头顶,但是总觉得有一颗必定是悬在车身上的。无数次我有这样的感觉——漫长的旅途,剩下这寂静的世界和一辆奔驰的车。风离开了车子一样会制造出响动,但是碰到了阻碍它的车,立刻充满了愤怒般带着锐响;车子离开这黑的浓稠的夜色,一样不会发出这样的呼啸声,轮胎在地面上沙沙的声音似乎是蚕在食桑叶,黑色的路就是一片巨大的桑叶,正在喂养车子这条条小小的、贪婪的蚕,而人卧在这条蚕的身体里,彷佛停止了呼吸,远离了世界,远离了一切。
我的沉沦开始于这奔突的车,在有限的空间里,刺鼻的气味和噪音慢慢就游离开去了。我进入混沌之中,迷迷糊糊的梦乡。那时我发现夜真的陷得很深很深,比大海还要深。我就这样堕入一种恐慌中,感觉身体在下坠,仿佛是从山顶往山下滚落的一种冒险和尝试。汗涔涔的背让我在梦境里分不清这样的感觉是真实还是虚构,这多像卡夫卡小说中那个变成甲虫的人,怪异的思维导致灵魂脱离了肉身一般,我是那样的惶恐和不安,热汗慢慢变成冷汗。
隧道里两边的灯光突然大亮,我从梦魇中挣扎出来,艰难地睁开眼睛,像婴儿第一次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我看看那些光,它们如水般从玻璃上渗进来,只有司机在活动着吧,其他的人都在熟睡,睡姿奇形怪状,居然连梦呓也没有。从一辆车内观察众生,你会觉得人进入睡的状态时,呈现的是生命的另一种形状,那是揭掉面具后的坦然。打开车窗,风从窗口灌进来,呼啸声更加尖利,副驾驶位上的司机警告说,关起窗子,空调不是开着的吗?于是我无奈地关上了窗子,一下子我感觉世界离我依然好远——未来不可知,前方看不到。微弱的光不足以看见书本上的字,我只好把手枕在脑袋下面,看着车内不断闪烁着的秒表。时间竟像凝滞了一般,我突然发现夜原来是如此的漫长,长到一生时间似乎也数不完。那些纷扰的往事竟然如潮水般涌进脑海。奔突,这个与夜关系紧密的词再次扎进我的灵魂,让我不得不把它镌进微微麻木的神经。
我想到了在广袤的平原上,我和几个小朋友相约去偷瓜,深邃的平原辽阔似天空,假如被发现,我们曾经设想过无数逃的方向。摸索着爬进瓜地,嗅着藤的清新和瓜的香味,我们像嗅觉灵敏的狗,再加上我们摸瓜时的独到功夫,很快就找到了香瓜的所在。那是何等的欣喜,像在夜里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一般,这样的喜悦是无法大声和人分享的,包括身边的朋友。我们靠着电视剧《雪豹》里特种兵一样的手势,交换着喜悦和做着撤退的准备。手势和暗语是保证安全唯一可取的方法。然而就在我们悄然起身摸出瓜地时,瓜棚旁的狗突然狂吠起来。开始时,我们还抱着瓜在黑夜里奔跑,但是跑得不够快,只好丢下瓜,一旦放开手脚地奔跑,感觉风都被甩在了后面,然而还是快不过那条狗。耳朵里狗的叫声已经泛滥开来,红薯的藤子绊倒了我,我就势滚到垄沟里,稍作休息。惊魂未定的我,这时才发现狗朝着另外的方向跑去了。第二天我们发现伙伴小军的裤子被撕开了一个洞,看来狗盯紧的是他一个人。他不敢告诉父母,所以只好自己用笨拙的手粗针大脚地补上那个洞,我们望着那个洞笑。瓜没吃到,但是大家想着昨晚的胡乱奔突,似乎体验到了一种奇异的刺激。全世界似乎都静止了,就剩下自己和那条狗在赛跑,假如守瓜人再加入其中,那场面不知该如何地壮观和惊险。
与夜色有关的还有那片棉花。那片棉花是如此地让人绝望,我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描述过它们。虽然现在它们早已被弹成被子不知盖在谁的身上,或者已经随着泥土腐朽了也未可知,然而当初我守着它时是无助而无望的。我甚至想,自己会随着那片棉花终老一生吗?我也许再也不能体验偷瓜时黑夜里奔突的快感了,那种刺激似乎彻底变得遥远了。捉鹌鹑的老汉打破了我守候棉田的寂静。他居然发现了棉田里的鹌鹑,他用长长的竹竿顺着棉花垄赶鹌鹑,企图把鹌鹑赶到地头的网上。鹌鹑是很傻的,它会顺着垄沟踱步,然而最终也会如鹌鹑老汉所愿,一头扎在网里。
一片死寂的地在那一刻变得生动起来,从面目可憎到鲜活生动,这里有我参与的热情使然。我协助他赶,但是长长的竹竿扫过棉桃时,棉桃落地了,青红色的棉桃就那么夭折了。快意代替了恐惧,我虽然知道这样会受到责罚,然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想快乐。打掉棉桃,这样的秘密我想一直隐藏着,我希望那些棉桃能土遁,或者靠着别的方式消失,然而那么多棉桃是不会倏地消失不见的。那是父亲辛苦劳作的成果,我应该守到它们自然咧开嘴来,才是正途。我居然协助捉鹌鹑的老汉打掉那么多棉桃,简直是“助纣为虐”,不可理喻!果然,父亲大为光火。黄昏时,他来到了地里,粗一看没有任何异样,仔细到棉田里转一下就会发现,多少棉桃都在哭泣。父亲转过身来就开始骂我,那一刻他的凶相让我忘却了喜悦。旋即,他就转身来追我了,我就那么狂奔,发挥着身轻如燕和身形灵活的优势,慌不择路中一下子就钻进了玉米地。玉米地是那么浩瀚,就像浮在平原上的一片海,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片海给吞噬了。父亲咒骂着我,发誓追到我一定要打断我的腿。
我顺着玉米的垄沟朝前跑,夜就在那时像水一样倾泻而下。我穿过了几块玉米地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甚至撞到了一冢新坟上,坟头上还立着花圈。大人经常说,新埋的这些鬼比较容易缠人,顾不得拍掉身上的土,我跌跌撞撞,赶快逃!父亲的咒骂声迫击着耳鼓,我又掉进了夜的浓稠里。那个奔突的夜晚似乎留给了我太多的阴影,每当我做噩梦时,总会梦见在浓稠的夜里,我陷入玉米丛林的汪洋中,喊不出声。不过也许我喊了,但是很快便被浩瀚的玉米地淹没了。现在我想起那些情景,总会忆及著名作家张洁的《挖荠菜》里和我一样的遭遇:“有一次,我在财主家的地里掰玉米棒子,被他的大管家发现了。他立刻拿着一根又粗又直的木头棒子,毫不留情地紧紧向我追来。我没命地逃着。我想我一定跑得飞快,因为风在我的耳朵旁边呼呼直响。不知是我被吓昏了,还是平时很熟悉的那些田间小路有意捉弄我,为什么面前偏偏横着一条小河?追赶我的人越来越近了。我害怕到了极点,便不顾一切地纵身跳进那条河。 河水并不很深,但是足以没过我那矮小的身子。我一声不响地挣扎着,扑腾着,身子失去了平衡。冰凉的河水呛得我好难受,我几乎背过气去,而河水却依旧在我身边不停地流着,流着……在由于恐怖而变得混乱的意识里,却出奇清晰地反映出岸上那个追赶我的人的残酷笑声。”这样特殊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盘踞在我的心头,由此我恨父亲,为了几个棉桃,他居然忍心让我深切体会那黑夜里奔突的恐惧。那时,伴随着我的还有饥饿和寒冷,露水似乎已经落到头顶,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吃上一个热腾腾的馒头啊。
浓稠的夜在车的奔突中渐渐明朗起来。哦,那是城市的灯光。路这片巨大的桑叶终于喂饱了车这只蚕,随着一声沉闷的回响,轮胎的沙沙声终于消失。开了车门,似乎又回到了活生生的世界上。那些纷扰的回忆似乎随着静止的车辆远去了,霓虹闪烁着,渲染着真实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