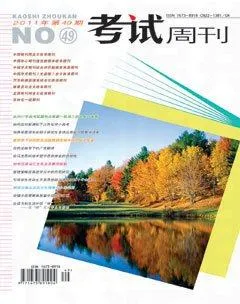浅谈明恩溥中国观及对中国的影响
摘 要: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的著作《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乡村生活》以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和中国人性格的细致描写和尖锐批判为特色,是其中国观的代表作,对中国学人研究中国国民性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明恩溥 中国观 《中国人的特性》
明恩溥(1845—1932),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在天津、山东等地传教30多年,期间他把自己的见闻编订成书:《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特性》(也译为《中国人的性格》等)、《中国乡村生活》、《中国在动乱中》等,其中《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乡村生活》是其中国观的代表。
一、明恩溥的中国观
明恩溥的中国观即他对中国的认识,包括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
1.明恩溥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以《中国人的特性》为代表。
(1)对中国国民性的肯定方面
勤俭的美德。他说:“中国人具有那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的勤劳美德。”[1](P21)与勉力劳动相联系,“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是节俭的楷模”[1](P12)。
坚韧的品质。明恩溥称道中国人生命力顽强,富有耐性与毅力。
孝道的普及。他认为若不理解“孝”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就无法了解中国人。
适应性强。明氏强调这种适应力在海外华人身上有更多的体现,并对此给予高度赞许。
(2)对中国国民性的否定方面
面子主义。“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的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1](P9)
缺乏效率。他认为中国人很懒散,做事缺乏效率,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很浪费时间。
保守主义。他把中国人知足常乐的性格视为保守观念在其行为上的体现。
2.明恩溥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以《中国乡村生活》为代表。
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明氏最先察觉到它的稳定性,并认为这是由乡村结构和宗法制度所致。就乡村结构而言,中国人多聚族而居,这样某个地方的人便易结成一个稳定的集团,这种稳定对社会的安定有重要意义,但也会造成该地与外地交流减少,这就阻碍了进步。就宗法制度而言,他认为中国的宗法制度较之法律制度更严密。这种社会中,人们普遍守法,有责任心,因为他们知道若违法了,牵扯的是整个家族。但是,他也认为:在一个家族中,只有大家长才有权力对一件事做出裁决,其他人只能服从,即使是错的也不能违抗,否则便是忤逆。因此,这种制度阻挡了错误,也阻挡了进步。
此外,明氏还对中国的教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以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以背诵这些经典为主要教学方法、以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使中国出现一种强大的保守力量,使中国人普遍地向后看,使中国人缺少全面的素养。
除了正确的认识外,他对中国乡村社会还有一些误解,如对中国的民俗、戏曲等。
他不理解中国人求雨时为什么敬这么多神:“有着多种多样真实的和想象的存在物为农夫们所崇拜,以求满足他们对降雨的需要。这些崇拜的对象有:慈悲女神,即观音菩萨;战神,即龙王……似乎这些崇拜的还不够,另一些人崇拜玉皇大帝,还有一些人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崇拜的‘孙大圣’。”[](P170)明氏对中国戏曲也有误解:“即使再有耐心的欧洲人,也不可能在听完一场戏后,而不精疲力竭。”[2](P58)“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音乐,众多的参与者,以及普遍的混乱。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演出丝毫没有什么吸引力。”[2](P61)
二、明恩溥中国观对中国的影响
明恩溥的著作对以鲁迅为代表的致力于改造近代中国的有志之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氏对中国虽有褒扬,但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才是主旋律。“尖锐的揭露中点缀着谨慎的赞扬,使明恩溥的作品至少有一个公正的外表。但是,有的时候,他那支爽快的笔会使人认为,中国人除了欺骗的艺术之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愚蠢的。这一点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中尤其明显。‘无视准确性’、‘误解的才能’、‘婉转说话的才能’、‘思维含混’、‘缺乏信用’等章的题目都反映了这一倾向。明恩溥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中国乡村生活》,对中国缺陷的强调同样留下了中国人都是傻瓜的印象”[3](P114)。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仍有很大的价值,尤其是《中国人的特性》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围绕此课题,陈独秀、李大钊、严复、鲁迅、林语堂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批判了中国的传统,寻求图强之路,其中尤以鲁迅最杰出,以林语堂最不同。
鲁迅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精神上。他曾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4](P31)为此,鲁迅国内外有关该问题的见解。留日时,他就看到了《中国人的特性》,看后深为触动:此书冷峻批判中国国民性缺点。后来他多次介绍并力主翻译此书:“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5](P626)
若说鲁迅是针砭民族性的国手,对民族的热爱使得他不能容忍国民性的种种痼疾,使得他能以冷峻的态度透视中国人的灵魂,搜寻出民族心理的阴暗面,以便警醒,那么林语堂的态度则温和很多。应赛珍珠之邀,也为了反驳明恩溥,1935年,林语堂写下了有关中国人的性格、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在此书中林语堂对明氏的错误观点给予了反驳,并用诙谐轻松的语言向西方介绍了他的祖国和同胞,行文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感。他说:“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我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的不让他们知道。”[6](P2)他试图以旁观者的身份论述中国人的特性,但是不难发现他在以亲和的态度表达深沉的情感。
“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中,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对民族反省思潮影响最大的要首推亚瑟·史密斯(汉名‘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7],所以要正确对待他的批评。
参考文献:
[1][美]明恩溥.匡雁鹏译.中国人的特性[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2][美]明恩溥.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3]Paul,Varg.Missionaries,ChineseandDipolomat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8.
[4]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林语堂.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7]俞祖华.略论近代中国的民族反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