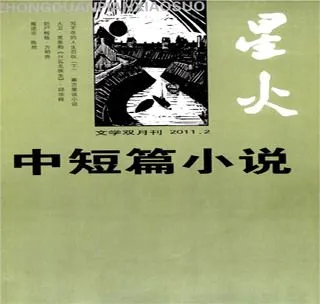关于小说之六:写不尽的人生百叹(下)
这篇文章讲小说中的人生之感叹,这其实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很简单,你细细思索了,它就变得复杂了。无论简单或复杂,前面的文字都还远远不能说明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看铁凝的《永远有多远》。
叶广芩让现实中的一件旗袍指引我们走向历史。《永远有多远》则是先抒写已经过去的时光:“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胡同里那些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记着。”铁凝用第一人称展开故事,借这个在北京胡同里生活过的女孩子之口,吹拂过来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从前,二十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后,我和我的表妹白大省经常奉我们姥姥的吩咐,拎着保温瓶去胡同南口的小铺去买冰镇汽水……”在这里,铁凝并不是写汽水就一门心思写汽水,而是由胡同南口说到胡同北口的副食店,告诉人们副食店都卖什么,然后说小铺“其实是一个小酒馆,台阶高高的,有四五级吧……南口不卖油盐酱醋,它卖酒、小肚、花生米和猪头肉,夏天也卖雪糕、冰棍和汽水……你知道小肚什么时候最香吗?就是售货员将它摆上案板,操刀将它破开,切成薄片的那一瞬间……”等我们似乎共同感受了小肚的香味之后,才说了喝汽水的感觉:“我只觉得冰镇汽水使我的头皮骤然发紧,一万支钢针在猛刺我的太阳穴……这就叫冰镇。没有冰箱的时代人们知道什么是冰凉,冰箱来了,冰凉就失踪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到了铁凝手里,却是如数家珍一般,在她的故事里,生活中的一丝一缕都是有滋有味的,她将这样的丝丝缕缕精心梳理,尽收于笔下,就连屋顶上的一只黄猫也不放过。当然她是有节制的,不忽略细节,也不会让细节拖累自己。屋顶上的猫只是一笔带过,邻家女孩的日记只是一笔带过,那“消沉”二字对“我”的震撼也是一笔带过,许多一笔带过的细节使作品的情状生动丰满起来,字里行间渗透着叹息与情感。
感叹未必一定是重大事件之后的感叹,让细微的生活情状之中泛出的细微叹息,体现着小说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怀。
不能不特别提到的是那个叫做西单小六的女孩,西单小六的故事不是一笔带过的,而是整整用了一节的文字,是铁凝笔下如丝如缕生活情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的眉眼在姐妹之中不是最标致的,可她却天生一副媚入骨髓的形态……她的步态松懈,身材却挺拔,她就用这松懈和挺拔的奇特结合,给自己的行走带出不可一世的妖娆,她经常光着脚穿拖鞋,脚趾甲用凤仙花汁染成恶俗的杏黄——那时候,全胡同、全北京又有谁敢染指甲呢,唯有西单小六……”西单小六不仅敢用恶俗的杏黄色染指甲,还制造了不少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们难忘的,是曾经有这样一群男人,他们齐心协力,共同行动,抢救出了一个正跪在搓板上的他们喜爱的女人……”西单小六是那个时代极具个性的叛逆者,这个独特的形象更反衬了白大省的朴实与“仁义”。
接下来该说白大省了,白大省“仁义”,白大省的仁义是与丝丝缕缕的生活细节缠绕在一起的。这仁义,是从喝汽水的时候,从“她跟着我在僻静的胡同里一溜小跑”,从她头发上挂着的一小块洗头膏开始的,“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奶奶背回过家(确切地说,应该是搀扶)。小学二年级,她就负担起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了。”白大省仁义,或者说有点傻,“她长大之后仍然傻里傻气地正派,常常让我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白大省恰好与西单小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单小六的放荡不羁与生俱来,白大省的仁义和傻气也是与生俱来,可她却又从内心深处渴望着浪漫的生活,“她说她最崇拜的女人是西单小六。”因此白大省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剧人物。
悲剧从是那个叫郭宏的男人开始的:“也许郭宏本是要与白大省结婚的,他们已经在一起过起了日子。白大省把伺候郭宏当成最大的乐事,她给他买烟,给他洗袜子,给他做饭,招一大帮同学在驸马胡同给他开生日Party……郭宏家的人来北京她是全陪,管吃管住还掏钱买东西……可是忽然间,就在临近毕业时,郭宏又结识了一个女日本留学生,打那以后郭宏就不到驸马胡同来了……这是一个打定主意要吃女人饭的男人……”白大省失恋了,失恋的白大省扬言要报复那个郭宏,却拿不出有力量的手段,她只会蒙头大睡,只会羡慕那个叫西单小六的美丽女子……
铁凝刻画了一个仁义的人,一个永远诚心诚意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报复别人呢,这不符合白大省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所以铁凝不写报复只写仁义,她让白大省在一条诚心诚意的人生道路上向前迈进,欲罢不能,无法回头。后来白大省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她对待工作和对待所有的人一样,都是诚心诚意。后来她开始了第二次恋爱,第二次恋爱的白大省对待那个男人仍然是诚心诚意,“她在新布置好的房间里给关朋羽过了一次生日,这回她多了个心眼儿,不像给郭宏过生日那回请一堆人。这回她谁也没请,就她和关朋羽两个人……那天晚上……”那天晚上白大省和关朋羽度过了一个有点甜蜜又有点尴尬的夜晚,幸福似乎就要来临了,“要是我们的另一位表妹不来北京,我判断关朋羽会和白大省结婚的,可是小玢来了。”这位从外地来的小玢最大的特点是不仁义,她挤占了白大省的衣柜,独占了白大省的床,分食白大省的午餐,“她把白大省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这些白大省都接受了,容忍了。但是,“最后她又从白大省手里夺走了关朋羽。”小玢的不仁不义进一步反衬了白大省的仁义,我们读者也要开始为她不平为她焦虑了,但是白大省却仍然义无反顾欲罢不能地将她的仁义进行到底:“她似乎有点绝望,却谈不上猛醒……白大省说他们结婚时她没去,她是想一辈子不搭理他们,那时候天天下班回家就发誓……可也不知怎么的,临近结婚时白大省还是给他们买了礼物……”
不仅“我”对“我”的表妹白大省很无奈,情节发展到这一步,在一旁看故事的观众似乎也会对这位白大省很无奈了。但是,铁凝并没有让这位白大省停下来。因为这时候我们还不能真正看清白大省非理性的思维方式。
用理性的思维铺展文字,抒写描绘非理性的行为,这是小说的制作方法之一。常常是,原本理性的读者,被非理性的小说里的人物所捕获,随着他们哀伤或者欢乐,随着他们进入到故事的深处,与这些虚拟的人物一起,度过他们生命的历程。
接下来白大省又开始了她的第三场恋爱:“转眼之间,白大省和夏欣已经认识了大半年,就像从前对待郭宏和关朋羽一样,她又在驸马胡同给夏欣过了一次生日。白大省这人是多么容易忘却……”我们现在更要为白大省忧虑了,因为这位夏欣是个一无所有也一事无成的男人,“我不喜欢一个大老爷儿们坐在一个无辜的女人家里白吃白喝外加穷‘白话’。我对白大省说夏欣可不值得你这么耽误工夫,白大省说我不如她了解夏欣,说别看夏欣现在一无所有,她看中的就是夏欣的才气。噢,夏欣居然有才气……”就是这么一个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夏欣,却被白大省当成了宝贝,“他,一个连稳定工作都没有的男人,一个连养活自己都还费点劲的男人,一个坐在白大省家中,理直气壮地享用她提供的生日蛋糕的男人。在白大省面前居然也能指手画脚,挑鼻子挑眼。那可怜的白大省竟然还执迷不悟地说:我可以改啊,我可以改!”但是,这个一事无成还被当成了宝贝的夏欣却选择了离开,最终又是让白大省白白付出了她的爱。
白大省一生永远遭遇男人的背叛。在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第一次背叛了白大省的郭宏又回来了,因为他自己也遭遇了背叛。“此时此刻郭宏坐在了白大省的沙发上喝着饮料,让半睡的女儿就躺在他的身边……郭宏说我要和你结婚,而且你不能拒绝我,我知道你也不会拒绝我。说完他就跪在白大省眼前……”此时此刻的白大省心情复杂,有点不知所措:“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场面,一个仪表堂堂的大男人就跪在你面前求你。渴望结婚多年了的白大省把自己想象成骄傲的公主……”把自己想象成骄傲的公主,这是白大省永远的渴望,或许也是所有女人的渴望。白大省渴望“听见一个男人向她诉说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多么难以让他忘怀的女人,就像很多男性对西单小六、对小玢、对白大省四周很多女孩子表述过的那样……”这就是女人,这就是所有女人的渴望,是令人感叹的女人的渴望。但是郭宏却说:“就因为你宽厚善良,就因为你纯、你好……”
白大省失望了,白大省并不欣赏自己的好,她对自己的好其实是万般无奈。故事发展到了这一步,铁凝仍然还不放过白大省,仍然把她的好继续向前推进:“她让我猜她昨晚回家之后在沙发缝里发现了什么,她说她在沙发缝里发现了一块皱皱巴巴、脏里吧唧的小花手绢……肯定是郭宏那个孩子的手绢。她说那块小脏手绢让她难受了半天……她把它给洗干净了,一边洗,一边可怜那个孩子……郭宏他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她说想来想去,她还是不能拒绝郭宏。我提醒她说别忘了你已经拒绝了他,白大省说所以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我问她说,永远有多远?”
小手绢是一个经典细节,表现出永远令人无奈的善良,它也让白大省的形象更加鲜活,更加典型且又独特,无可替代。
铁凝刻画一个好女人,但是“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更准确地说,她是刻画了一个不想成为好女人的好女人。她写了作为女人的永远的无奈。又写了人的个性的永远的无奈。她完成了一种微妙的心灵表达。
在我们这个人的世界里,存在着许许多多无法改变的不变,也存在着无法阻止的改变。变与不变都会令人叹息,令人欢乐或哀愁。小说家感知了叹息,小说家抒写了叹息。哪位小说家的叹息感染了读者,他的作品可能就写好了。
(责编:熊正良电子邮箱:xh37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