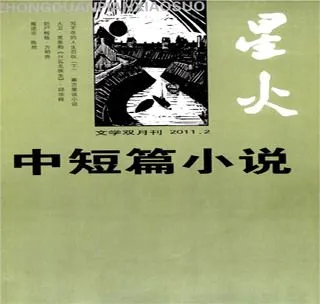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天还没亮,水库的水面上吱呀吱呀的行进着一条小船,小船上站着一个女人。湖面上凉风习习,四周分外的寂静,只有湖水拍打着船帮和船橹与船隼在摩擦中发出的声音。从小船上几乎看不到前方的水路,由于走得熟了,这里的人们几乎闭着眼睛也可以把船划到湖中要去的任何地方。水库修好后这里的人们大多迁移到别处去了,只有少数眷恋家乡的人才顽强地固守在这个穷地方。小船来到大坝边靠稳了,女人提了个小包袱,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稳稳地跳下船,那船就掉转头,吱呀吱呀地划回去了。
女人从坝下走到坝上,又从坝的另一面从坝上走到坝下,就来到了一条通往外面的沙石公路。四周仍然很黑,除了偶尔几声蛙鸣外,安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女人紧掖着小包袱,踩着满地的碎石,匆匆地赶路。她干活总是十分地认真,总是比人家先到干活的地点,所以必须起得比别人早。她必须在事主家的客人来到之前到达事主家,做好干活的准备。
远远的看见有一户人家亮着灯,女人就嘘了一口气,加快了脚步。
天还刚微微亮,女人来到有灯光的人家门前停下了。厅堂的中央摆着一口油漆棺材,棺材前面的小方桌上立着一个黑框的遗像,一个老人在像框中微笑着。前面点着一盏豆大的小油灯。桌子上摆满了鸡鸭水果等供品。两枝粗大的红蜡烛在桌子旁边熊熊燃烧着。屋子里空无一人,显得有些冷静和阴森。
也许是听到了女人的脚步声,这时从里屋转出一个满身带孝的人来,对女人说你来了,先休息一会吧,他们还没到。他所说的他们是指她的同伴们。他们一共有六人,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完整组合。一人负责架子鼓,两人吹唢呐,一人开音响,一人唱歌,一人哭丧。女人就专门负责哭丧。农村人办红白喜事都十分讲究,有一整套规矩和程序,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逾越。尤其是办丧事,清规戒律更多,不仅要请祭仙和做法事,跪跪拜拜一环不少,而且营造氛围也显得十分重要,哭丧是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但现在农村计划生育,孩子比过去少了,加上年轻人多数外出打工,已经和城里人差不多,对农村的规矩也知之甚少,再加上现在的女孩一般都不会哭丧,只知道呜呜呜地抹眼泪却编不出什么词儿来,怎么也哭不出那种氛围来。后来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先请一两个会哭的哭上一会,用录音机录下来,再在高音喇叭中播放,很远就能听得见,气氛就出去了。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也不是个好办法,远远地听可以,到了跟前就不行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总有点弄虚作假欺骗先人的感觉。亲戚们对孝子们也有微词。所以哭丧这项职业就应运而生,女人和她的同伴们把这类工作叫做做日子。
女人做日子有些时日了。她的丈夫原来在一个私人煤矿做事,长时间的井下作业使他得了矽肺病,走一百米路也要气喘吁吁的休息好几回,长年在家卧床休息。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了女人身上。女人文化水平低,干不了什么大事,就干上了哭丧这一行。做一天日子有五十块钱的进帐,对女人一家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女人的同伴们陆续到齐了,他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女人从包袱中拿出一件白色的衣服穿戴好了,来到棺材前,用手在鼻子上狠狠一拧,那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我的可怜的老爸啊,随着一声呼天抢地的呼喊,随着悲呛的音乐声,那哀戚戚的氛围就表达得淋漓尽致。
天大亮了,东家的客人陆续来了。男人们就在灵前上一炷香,跪在灵前磕几个头。女人们一进门就用手拧着鼻子,扑到棺材前痛哭一番,这时候哭灵者就要打足精神哭,要用自己的哭声带动其他的哭者。女人哭起丧来也是十分地认真,其他的哭丧者总是干嚎的多,有声音没有眼泪,事主也是只要哭丧人哭得响亮,并不苛求哭丧人流多少眼泪。女人哭起来却总是声泪俱下,如醉如痴。好像死去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人。只要来宾不是铁石心肠的女人,受到哭灵女人的感染,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
哭丧的女人不是一整天都哭。只是有客人来了陪着哭上一会,时间隔久了没有客人来也要哭上一会。其余时间是歌手唱歌,做日子的组合里有一个专门的歌手,革命歌曲流行歌曲和戏曲都可以唱,譬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揭了皇榜当状元等都可以唱。歌手唱歌的时候远远听去似乎不是办丧事,而是在唱卡拉OK。在座的客人都说说笑笑,与哭灵女营造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
哭丧女人哭丧的时候总会想起自己的丈夫,想起了丈夫就更想哭。女人与丈夫结婚的时候,丈夫也是一条人高马大的山里汉子,夫妻恩爱的时候可以整夜整夜折腾得她无法休息。第二天照样精力充沛外出劳作。他的精力总是那么旺盛,好像永远也使不完。由于水库淹了大部分土地,村子里人平均只剩三分地,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他拖家带小的就没有去,而是厮守着女人和儿女在家过日子。再后来一个私人老板在村子不远处开了个煤矿,他就去了矿上做事。三年时间闹了个重病回来,夫妻俩肠子都悔青了,可是没有办法了。现在丈夫天天躺在家里什么事都做不了,过去甜蜜的夫妻恩爱也力不从心了。还要天天吃药打针的。人也瘦得不成人形。想到这些女人就想哭,哭丧的时候就哭得比任何人都悲哀。
没有哭丧的时候,女人就到其他同伴那里帮帮忙,整理乐谱或者收拾乐器什么的。实在没有事了就静静地站在一旁听歌手唱歌。其实女人也是会唱歌的,尽管没有这个歌手唱得好。可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她就十分喜欢音乐课,考试的时候老师总会给她很高的分数。她的丈夫就十分喜欢听她唱歌。她丈夫最喜欢听她唱七仙女唱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过去身体好的时候偶尔也会五音不全地对上一两句,或者抱着她亲上一两口。可现在什么都不行了,丈夫再也吼不出那五音不全的声音了,再也无力气抱着她亲上一两口了,但丈夫仍然会偶尔在晚上要求她轻轻地唱上几句给他听,想到这里女人就想哭。有时她看见丈夫病得太难受了,她就会坐在床前轻轻地唱树上的鸟儿给他听,这比一般的药都管用,丈夫就会慢慢地睡去,她才敢躲到外面偷偷抹眼泪。她刚开始做日子的时候,丈夫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哭丧,而是要她去唱歌。可是组合里的几个人一商量就否决了,因为那个年轻的女孩根本不会哭丧,但歌是唱得很好的,哭丧的工作就落到了女人的身上。她就只有骗丈夫说自己是唱歌,好在丈夫也不在身边,这个善意的谎言才不会穿帮。
女人出来哭丧的时候,家里就剩下丈夫在家。儿子和女儿都上学去了。儿子上初中,女儿还在上小学五年级。女人最担心的就是丈夫。她担心她不在家的时候丈夫会出什么意外。现在尽管丈夫卧病在床,但一些大事还是他作主。有一天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天就要塌了,她会不知如何是好。她于是商量着在家里床头装了一部电话,自己买了一个便宜手机。尽管家里穷,但她觉得这个手机还是必须买的,自己的电话只和丈夫通话,别人的电话一概不用手机,也用不了许多钱。女人每次在外做日子,都要和丈夫通一两次电话,听到丈夫接了电话她才会放心。丈夫也很心疼女人,她每次出去都必须起得很早,他就会反复叮咛她要注意安全。还专门请隔壁的堂兄用小船把她送到坝下。晚上接到女人的电话后又把她接回来。
女人做日子的组合里,只有她和唱歌的女孩两个女人,其他四人都是男的。每次做日子的时候,只有她是悲悲戚戚的。其他的人都是有说有笑的。女孩不唱歌时就用小镜子照照自己,还不时用小眉笔描描眉毛。四个男的一闲下来就有说有笑地抽着香烟。东家每天都给大家发一包香烟,也不管你抽不抽的,女孩和女人都把烟收下了,女孩是带回去给父亲抽,女人带回去是给丈夫抽。按医生说的丈夫是不能抽烟的,肺都那样了,抽烟等于加速自杀。可女人看不得丈夫那痛苦的样子,心疼丈夫一个人在家的无限寂寞,就放宽了限制,允许他每天抽三支烟,每天出门的时候把三支烟放在丈夫的床头上。女人想不通同伴们在死人的棺材面前还那样谈笑自如,一点悲哀的情绪都没有。她自己是见不得棺材的,一见到棺材就会想起死去的父母,想起重病的丈夫,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流出来。
请人哭丧的人家一般都是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家境不好的人家只请唱仙,不请哭丧的,都是自己的亲人哭。今天这一家是比较好的。死去的老人在城里还有房子等产业。病重了老人自己要求回来,一是求个叶落归根,二是死在城里要火化,这山区可以土葬,可以躲掉死后的火光之灾。
我的老爸啊你怎么就去了啊,正当大家准备收摊吃中饭的时候,一声炸雷般的哭声从门口炸开,弄得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是老人的女儿回来了。一进门就往棺材上撞。女人马上进入角色一边陪着哭一边用力拉着老人的女儿。老人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老人是昨天才去世的,老人的丧事是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家操持,女儿回来了,还有一个儿子没有回来。老人的大儿子在家务农,二儿子在城里做点小生意,老三老四碰上好时光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都买了汽车买了洋房。老人的一家在当地是很风光的。女人哭着哭着就想起了自己,想起了重病的丈夫。自己不要多么的富有,只要一家人健健康康地过日子就行。可老天就是不给自己机会。这都是命啊。
丧事的第二天是最忙的,一整天都是做祭。就是祭仙为家庭成员和亲戚读祭文,以哪个的名义祭哪个就又跪又拜,围着棺材转圈儿。祭仙读祭文实际是唱,带着哭腔拉着长长的调子,模仿女人的哭嚎,越悲切祭文就读得越好,所以乡下好的祭仙就很吃香。
由于今天很忙,所以女人照样起得很早,可当她急匆匆来到事主家的时候,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一打听才知道老人的三儿子回来了,昨天晚上连夜开了家庭会,除了丧事的有关事项外,还讨论了遗产分割问题。原来老人早就立了遗嘱,要把城里的两间门脸店留给大儿子,一套住房留给其他三个子女。谁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三个子女结成了统一战线,坚决反对这个分配方案。讨论的焦点由办丧事转向了分遗产。
其实老人的想法是有理由的。老人年轻时也是大学毕业,分配在银行工作,可那一年不知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被打成了右派,开除了工作不算,还坐了好几年的牢,新婚的老婆也离婚走了。出狱遣送回家后在农村监督改造,找了个农村女人结了婚,生下了四个子女。直到摘了右派帽子落实了政策才回到单位上班。老人的大儿子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出生的,从小就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白眼和委屈,也造就了他老实本份的性格,现在成了一个本份老实的农民。其他几个子女就幸运多了,做生意上大学,闯出了自己的新天地。二儿子虽然没上大学,但头脑精明,赚下了不小的家业,三儿子自己在广州开了公司,女儿也在深圳一家大公司做白领,凭什么也要照顾一下老大,让他多一点生活保障。老人可能还有一个考虑,老人是农村出来的,家乡是家族发脉的地方,必须有一个子女固守在祖宗立业的地方,哪怕是穷一点也要有人做出点牺牲。这个人只有大儿子可以胜任。事实上老人退休后,大多时间是在大儿子家过的,几乎没有去过其他儿女家。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在遗产上帮一下大儿子是理所当然的。
遗产风波还没有结果,丧事办得就没有那么顺畅了。本来准备吃了早饭就要开祭的,可几个子女就是不到场。那三人甚至商量着进城请律师打官司,说那遗嘱没有经过公证是无效的。祭仙捻着祭文就是开不了场。女人也已经做好了哭丧的准备干着急。女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无钱的人家日子不好过,这有钱的人家怎么也不好过。她不知道老人的儿女们是怎么想的。她记得老人在世的时候,儿女们每年都会回家过年,看起来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怎么老人一去就变得六亲不认起来。
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了,他在大厅的棺材边大声吼道,你们做儿女的都给我听着,你们父亲尸骨未寒就在这争东西,像什么话。你们要打官司明天打去,今天先把你们父亲给我埋了。说话的也是一个老人,是村子里辈份最高说话最有份量的族长。听到族长发火了,几个儿女才磨磨蹭蹭地出来。
由于上午耽误时间太多,这天的家祭搞得很晚。女人十分担心家里的丈夫,偷着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听到丈夫接电话了才放了心。她告诉丈夫今天可能回来很晚,问丈夫吃饭了没有,女儿回家了没有。她的儿子在镇子上念初中,在学校住宿。女儿在村里上小学,每天回家住宿。女儿虽然小可十分听话,洗衣做饭什么都会干,一双儿女是她夫妻俩最大的精神寄托。丈夫在电话里告诉她,家里的母猪可能要下崽了,哼哼叽叽的不肯吃潲。女人叮嘱丈夫要留意点,不要让母猪生产时出了意外,更不能让母猪压死了猪崽。那头母猪是家里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一年下两窝崽,就是几千元的收入。
这天晚上女人十二点多才回到家里。一进家门就看到儿子也回来了,爷儿俩正看电视呢。她知道儿子是回家拿菜的,儿子很懂事,为了省钱从不到学校买菜吃,都是吃从家里带去的干菜。上次去带了一缸子香椿炒牛皮豆,还放了少许腊肉,一星期了可能吃完了。家里的电视也是新买的。前不久丈夫在城里的几个同学专程来看他的病,走时放下一千元钱,说什么也要他们收下。她就用三百多元钱买了一个电视机,原来那个黑白的已经看不清图像了,也是考虑到丈夫一个人在家太寂寞。其余的钱都给丈夫买了药。现在女儿已经睡了,儿子在父亲的床头歪着,说说笑笑地看电视,看到他们亲密无间的样子,女人心里感到一阵安慰。女人到床头拍了拍儿子的头,又到猪圈看了一下母猪,没有看到下崽的迹象。女人就到厨房洗了一把脸,也到房间坐下。
看到母亲进来,儿子说话了。儿子说五月十二号的汶山大地震,已经死了好多人。学校的同学们把买菜的钱都捐出来了,支援灾区,我也想捐点。丈夫也附和说几万人埋在地下,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啊,太惨了。汶山大地震女人也是知道的,只是最近做日子比较忙,没有时间看电视,不知道最近的救灾情况。看到儿子那殷切的眼光,说捐点吧,国家有难我们再穷也该出点力。一家三口就商量着捐多少,最后决定儿子捐五十元,自己和丈夫捐一百元。
第三天是老人上山的日子,女人和她的同伴的工作是做路祭。路祭就是八仙抬棺上山的时候在路上休息时,祭仙要读一段祭文,女人照样要陪着孝子们哭。直到把老人送到下葬的地方,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路祭的时候女人发现事主家的儿女们个个表情漠然,对大哥的态度明显有一些仇视。女人就想要是老人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多好。
就在女人快要到老人下葬地的时候,女人的手机响了,是隔壁堂哥打来的,电话里说家里出事了,要她赶快回家,他到坝上来接她。接到电话女人的脑袋就蒙了,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来不及打招呼和结工钱,撒开步就往家里飞奔。
回到家里的时候,丈夫已经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堂兄告诉她,今天上午收桐子的来了,丈夫艰难地提着家里一大袋桐子去收购点,在村口被一摩托车撞了。堂兄还说已请村里的医生看了,医生说没有办法了,看他自己的造化吧。女人顿时觉得昏天黑地,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了。
从这天晚上起,每天白天和晚上,女人的家里都会传来阵阵歌声,一个女人在对着他的丈夫轻轻地唱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责编:朱传辉电子邮箱:zch7611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