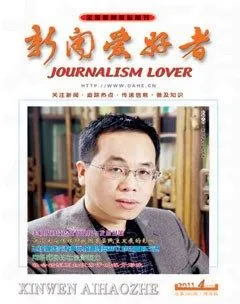白先勇小说的佛教情结
白先勇作为誉贯海内外的台湾当代作家,他将门虎子的显荣出身、幼年罹受的缠扰病榻生活、少年遭遇的家国的变故战争及此后跨洋旅美留学的非凡经历都令人叹为观止。然较他的经历更加令人仰止的是他一生中有大批蜚声文坛的作品出世,以及充斥作品中锐敏奇丽的宗教色彩。究其一生,佛教不失为指引他心灵的一盏明灯,他总是试图透过宗教的视野来探究生命的本相。
溯源白先勇的佛教情结
佛教文化对白先勇的影响,既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同时也是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佛教有所谓“因果相续,因缘所生”一说,我们从白先勇的成长经历可以探溯他萌生和维系宗教情结的源头,那作为佛教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君子象征的莲花,是怎样在他思想和作品里扎根发芽,婆娑开花。
白先勇是中国近代史上战功彪炳的国民党名将白崇禧之子,据白先勇回忆,他父亲是一位儒将,文学造诣很深,学了很多古文、古诗词,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对白先勇走上文学之路表示理解和尊重。白先勇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从小就有机会接触、阅读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红楼梦》,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红楼梦》最感动他的就是其中“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佛家思想。白先勇是一个有慧根的人,与佛教有缘的人,“很小的时候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①,“看了《好了歌》,对那里面写的那些特别感到惊心动魄”②。这种感性上的宗教感,使他在理性上天然地“对佛教的看法,特别感到动心”③。
白先勇少年时期的文化心理构成中,就存在着隐性的宗教文化因子,他的宗教情绪更多地是来源于佛教思想的濡染。童年时,白先勇曾患病卧床达四年之久,几乎与世隔绝,这就养成他一种敏感、内向的性格,这种心理机制是滋生宗教情绪的良好土壤。幼年养病期间看到嘉陵江涨大水,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漩涡卷走,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却又无可奈何的悲悯之情,使他觉得一切皆空,人生无常。成年后母亲去世,“因为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④。这些对现世现实通彻的体悟与佛教本身宣扬的人生哲理不期而合。
博采众长——儒道佛文化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一个人总是会受到他所成长于其中的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中国哲学与思想主脉的儒道释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他以独特的方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自己的眼光和标准对儒道释学说作了自我新的阐释和再现。
中国的传统宗教是儒、道、佛三教的融会贯通、相生相克,佛教的大慈大悲早已和儒教的仁政思想合二为一,佛教的色空观念和道教的消极避世也早已犬牙交错、纠缠不清。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就能看到儒、佛、道三重宗教文化的纠缠融合,尤其《台北人》诸篇,作品中的人物,处事精明,机敏过人,本该在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但终究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过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从中可以看到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道家消极“出世”思想的抗争和妥协。在那些人物身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是他们人生意义的最高准则和目标。然而他们虽有积极“入世”的愿望,但处在动乱的时局下,他们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儒家文化中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与释道文化中消极“出世”的明哲保身态度的矛盾,一直在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着。当他们在生活上、政治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占据上方,他们不甘寂寞,努力进取,意欲在险恶的政治舞台上一展英姿;当他们在生活上、政治上失意时,往往退隐山林,修身养性,或浪迹天涯,追求自我和自然的和谐;有的甚至皈依佛门,万念皆空,走上“宁静”、“无为”的“出世”之道。
《冬夜》中写的是分别了20年的两个教授重逢后的一夕长谈。一个是老教授余钦磊,曾在台湾某大学教文学课程,另一个则是被誉为国际历史权威的旅美学人吴柱国教授。两人曾是领头发动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余钦磊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一直在大学教书,吴柱国则留居美国,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名人。在一个凄冷的冬夜,两位老友相会在余教授的住宅,回忆了共同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壮举,青年时代为国为民的理想和激情,回想青年时代的美好爱情,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爱国之情也好,爱情也好,随着境遇的变化、年龄的衰老,一切都无奈地逝去,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出于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理想而埋头于“潮湿”的地下室,在“一堵高墙”般的藏书中,忍受着物质的拮据、精神的寂寞,三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地苦读,最终收获的只是迷茫;再如《谪仙记》中的李彤,出国前也是和吴汉魂一样胸怀大志,期望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而他们这样的有理想的青年为了事业,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最终却在失败之后颓废、沦落,完成了由“入世”到“出世”的过程。
白先勇之“佛学治心”
在各种宗教中,白先勇受佛教影响较深,宗教感情也最认同佛教。他是把佛教思想当做一种人生哲学,佛门成为他笔下一些人物逃避现世困苦、修身养性的皈依之地。他常借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使读者看到人生因为诸种欲望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而能够拯救心灵于苦海的就是淡泊名利,摒弃欲望,以佛教治心、修炼身心。《台北人》中的一些人物在青年时期积极“入世”,尊崇儒家;中年时期仕途坎坷,讲求“出世”,信仰道家;到了晚年一切都陷入绝望的境地,看破红尘,便皈依佛门。《国葬》中的刘行奇、《思旧赋》中的李长官、《梁父吟》中朴公等一些人物的心路历程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佛门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白先勇的小说常常流露出佛教“诸行无常”,人生皆苦等观念,并借助佛教的宿命论传达出个人的渺小和身不由己,以及在“业报”“轮回”面前的无能为力,世间事物生灭有定,幸福和欢笑,伟大与辉煌,到头来只能是归于虚空,功名会被遗忘,富贵无法常在,这使得他的小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悲观情绪。读他的作品时能从中体悟到人生的无常和孤独,同时,这种佛教的神秘感和凄凉、苦涩的情调,赋予了白先勇作品独特的魅力和感染力。
白先勇常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来抒发自己的心灵感触,把抽象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式的感慨形象地外现在作品中。无论是《国葬》中的李浩然、《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还是《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等,这些人在大陆时都曾富贵无比、红极一时,但是,时过境迁,辉煌不再,青春老去,曾经光鲜的生活仿佛南柯一梦。他们有的命运无常,凄凉地死去;有的门前冷落,庭院荒芜;有的心如死灰,遁入空门;有的只能怀着失落的心情去参加新贵的宴会。这样人的人生的大起大落,证实了人生的无常和不确定性,而他们的不幸与苦难也暗示痛苦源于欲望。蓝田玉(《游园惊梦》)若不是由于前世的冤孽——与郑彦青的爱情,怎么会承受情感的折磨和煎熬?!而痛苦的根源也许就是她内心对物质享乐和男女情爱的欲望。白先勇用小说中人物无常的命运告诉读者,常怀佛家之心才能超然物外,脱身于人世苦海。
佛教思想影响着白先勇的人生观、文学观,并成为他一些文学作品的一种宗教底色,这不仅与作者兼收并蓄的思想体系有关,也反映着他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显示着作者艺术处理的从容不迫和驾驭小说的轻灵自如。
注 释:
①②③刘俊:《白先勇答问》,见刘俊《以残缺的爱为视域揭示人类情感的困境——白先勇早期短篇小说主题透视》,《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2)。
④白先勇:《青春念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参考文献:
1.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2卷):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2.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1卷):寂寞的十七岁》,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3.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4.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5卷):游园惊梦》,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