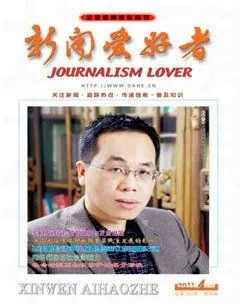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摘要: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业务 特色
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记公司时期,但作为发端,英敛之时期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为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主要有四大特色。②
新闻体裁多样化,新闻种类增多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此时的《大公报》的体裁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到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发布。
这一时期新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③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开始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注重“精品意识”和“互动意识”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实践基本秉持了其《本馆告白》中所渗入的“两个意识”。
其一是“精品意识”。首先,其时的《大公报》几乎不登载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转而将报道重点放在关涉国计民生的时政新闻上,这本身就是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表现;其次,该报的“精品意识”还表现在较早刊登高质量的“新闻连载”方面。正如《本馆告白》中阐明的那样——“各报附录书籍多限于篇幅,虽陆续排登,骤阅之,每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殊觉味同嚼蜡。本馆附录各件其篇幅过长不能全录者总期成一片段,不致有闷葫芦之叹。”早期的《大公报》已经在通讯、调查等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新闻连载”的形式,例如,1902年6月24日该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来函代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的通讯文章,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进行了连载,该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恽学士被御史黄曾源参劾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在文中巧妙地穿插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种种暴行、相关人等的关系等背景资料,突出了当时通讯文体的传奇性、故事性的特点。又如:该报曾连续十期刊登了调查当时我国22条铁路的“新闻连载”,该文题为《调查各省路政纪要》,每期介绍2~3条官办或商办的国家铁路情况,而且介绍每条铁路的文字还用小标题隔开,这样,虽然是连载,但每期刊登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使读者读后并无“闷葫芦”之感;除此之外,大量刊登原创文章和译文,也是《大公报》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有力证明。该报创刊伊始就曾在《本馆告白》中表达了这个办报理念——“海内同志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详告本馆,当为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或创意欲撰、欲译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绍介、普告学者。”基于此,该报曾在“专件”中发表连载《南非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在“译件”中刊登翻译文章《英国工业新教育案》等文章。
其二是“互动意识”。早期的《大公报》深知报纸的未来系于读者的支持,故非常注重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办报思路最先见于《本馆告白》中:“日报一事全赖集思广益、不厌其详。本馆虽托有各处友人广咨博采尤恐圜于耳目或偏执,见有失实事求是之义。尚幸四方同志匡其不逮,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馆亦为采登。”在具体实践中,该报经常举行面向所有普通读者的“征文比赛”。如,该报曾于1911年11月22日举办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不仅详细刊登征文要求、奖励办法,还陆续刊登获奖作品。同时,《大公报》还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来稿”、“来函”的形式予以刊发,充分体现来自民间的声音。
讲求“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业界普遍认同并时常运用的新闻操作手法。虽然,在彼时《大公报》所处的时代尚无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大公报》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了,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该报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
从1917年7月3日起,该报开始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五天的集中报道。以下便从新闻业务角度对这组报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数量上看,该报一共做了11版的报道,大约刊登了各类新闻约120余条。其中7月4日和7月5日两天每天做了两个版题为“讨贼之师起矣”的组合报道,7月6日做了两个版题为“薄海争传讨逆声”的组合报道和一个版的《大公报特别附张》,7月7日又刊出了题为“逆贼无死所矣”的组合报道。至此,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完整圆满地结束。
其次,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的报道速度、稿件质量以及版式安排都颇为出色。不难看出,《大公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了纵深两个层面上——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直接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以事件为线索,关注并尽最大可能报道事件各方的态度、声明、举动等。这样,既保证了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又确保了报道的全面、客观、平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具体报道中,每篇消息的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新闻,但往往主旨明确,一目了然;评论一般以述评为主,也有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如《致国人》,言辞恳切,亦能一语中的;稿件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发人思索。如每天都刊登一个突出大标题的“专版”,这种做法类似今天的集纳专栏,主题非常集中。同时,配合新闻,刊登言论并巧妙地登载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新闻以加大报道的覆盖面。例如,7月4日刊登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辞职书》一文,就很能体现编辑的匠心独运。行文上,还注意通过字号的变化来隔离标题和正文并由此来标示新闻的重要程度。
还有就是加大了对“张勋复辟”所衍生的事件进行报道,从侧面呼应整个报道。譬如下述几则新闻标题——“京报界失言论自由”、“日本调兵到京消息”、“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等。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冠以“喻评”的新闻述评,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例如:7月3日报道中刊登了一篇很短的花絮式的报道——《两日来之成绩》,并注明“冷观”字样。该报道原文如下:“今将复辟后两日来之成绩摘要开列于左。一、恢复红顶花翎;二、恢复三跪九叩;三、恢复总督巡抚大学士;四、新增忠勇亲王一尊;五、骇走北京住民数千;六、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七、骇跌中交票价。呜呼复辟……呜呼民国。”这篇只有80余字的小文,却生动地反映了复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虽称“成绩”,实则反语,策划很到位。
广告内容丰富且操作手法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再有就是,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或者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亦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以上是笔者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早期《大公报》所进行的粗浅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主要是因为该报当时在业务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对今天的媒体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文中的新闻作品皆摘自《大公报》(1902~1925)。
③参见《大公报·本馆告白》,1902年6月17日。
(作者为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