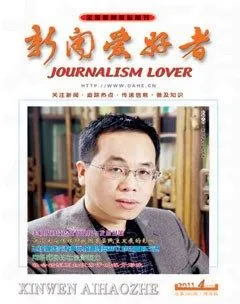从虚假需要\\符号价值到拜物教
摘要:广告文化批评的最重要范式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广告制造虚假需要的指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影响使人们注意到任何物品都是带有符号价值的,这种观点的极端形式不但挑战广告创造虚假需要的说法,而且挑战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对生产过程的侧重。但相关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概念可以为当代的广告文化批判提供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广告 虚假需要 拜物教 鲍德里亚
广告不仅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也是大众社会文化生活中最活跃和强有力因素之一。广告在当今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说广告是面对现代生活的精神荒漠而提出的以消费作为救赎之路的新宗教。广告在当代的重要地位也使它成为当代文化批评批判的焦点。
虚假需要与异化
广告文化批评的最主流模式是指责商人将广告作为一种工具来操纵并控制消费者,使他们渴望购买一些本来不需要的东西。这种被制造出来的,反映制造商利益而不是消费者自身利益的需要只是一种虚假需要。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尔库塞。在1955年发表的《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承认文明的发展需要以压抑人的本能欲望为代价。但马尔库塞认为,还必须区分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基本的压抑根源于物质匮乏,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有些压抑只是代表特定文明阶段统治者的利益,是额外压抑。近代科技的发展已消除匮乏的威胁,但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里,压抑不仅没有消失和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现行的本能压抑主要不是产生于劳动之必要,而是导源于由统治利益实行的特定的社会劳动组织,就是说,压抑基本上是额外压抑”①。
实施“额外压抑”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在需要的层面对人进行再结构,即制造一种“虚假需要”。在马尔库塞看来,物质需要并不是人的本质需要。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非但不满足于物质享受,而且力图摆脱物的束缚,追求更加高尚的境界。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却把物质需要当成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这种不是基于人的本质需要的“虚假需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们的。在他眼中,广告无疑是制造虚假需要的能手。在他1964年出版的最著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在又一次区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时专门提到了广告的作用。他说,现行的大多数需要,如“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所恨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需要。”②
符号价值
但虚假需要一词同时也是充满歧义的。在马尔库塞的表述中也流露出一种倾向:似乎虚假需要就是社会所制造出来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还存在一种与之相对的不被社会、文化所中介的、自然的、本真的需要。而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有许多例子表明商品不光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社会文化方面的符号价值。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一瓶陈年佳酿葡萄酒,虽然没有打开并饮用,但它仍然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象征性地消费着(比如被人长久凝视、梦寐以求、品头论足、照相或拿在手里摆弄来摆弄去),并使人得到极大的满足。在某种情况下,对这种葡萄酒的购买也许只是为了通过高昂的价格来取得声望,维布伦在1899年的论文里称这种消费为“炫耀型消费”。这种为了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而进行的消费,用今天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符号消费。一件商品越是能够彰显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它的符号价值也就越高。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符号价值的消费已经构成了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他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流通、购买、销售,对做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③。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在使用价值与符号的关系来区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威廉斯也认为,当代广告赋予了商品那么多复杂社会意义和符号的价值,这说明现代社会并不是只强调物质的占有。与之相反,我们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唯物。
符号学认为人类文明的特征就在于人是通过符号的中介来把握世界的,所以,在所有的文化形态里,产品的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任何社会和文化形态都会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再生产自己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文化模式。人类需要的每一方面都有符号和物质的关联,就算是我们最为基本的生理上的需求,如吃穿住,也总是“被厚软而充满符号中介意义的毯子所紧紧包裹着”④。
鲍德里亚:超越生产领域
既然无论古今,社会产品都会附有社会文化符号方面的意义,那么如果批评广告为商品制造符号价值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为广告辩护的人就声称,广告合理化的基石恰恰正在于它的符号意义生产方面。甚至有人把广告赞同于艺术。艺术常被定义为一种对现实的阐释或变形,其目的是为了让观众以特定的方式——超越功利性和实用性,达到纯粹的形而上——去思考。而广告也有同样的目的,运用的是类似的手段,因此衡量广告也应该遵循与艺术一样的崇高标准。⑤
如果说广告与艺术之间不再有根本的差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艺术与现实的界限也彻底消失了,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两者都已经瓦解为普遍的仿像。他非常强调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象征意义,指出现实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符号化的幻象”,我们就生活在现实的审美幻象之中,总之,符号不仅是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构成了现实。由此,鲍德里亚认为,现在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了,商品形式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在马克思时代,只是在物质生产中出现了异化现象,现在情况变了,连道德、爱、知识、意识在内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在市场领域里运作,具有交换价值了。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现在该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重心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这时符码控制着需求与社会化过程。所以现在重要的是要垄断符码,而不是垄断生产资料。因为现在符号形式压倒一切、统治世界,所以分析任何问题不应该从生产过程入手,研究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应该分析符号领域。
而广告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广告操纵了符码体系以后,任何的物体,不管它的物理构成如何,都可以具有它所想要的任何的符号意义。这样说来,一辆汽车可以是优雅的、细腻的、煽情的、年轻有活力的、男子气概的或是温柔的女子气的等。汽车本身谈不上有什么内在而本质的性质或意义,它的意义取决于它在整体符码系统中的位置,因此它是这些意义中的任何一种。
作为拜物教的当代广告
在对当代广告的文化批判中,我们真的像鲍德里亚说的那样到了该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了吗?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接受新时代的挑战呢?苏特·杰哈利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出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解答。
“拜物教”(fetishism,在心理学中有人译为“恋物症”)这个词最早是从人类学对fetish(即“偶像崇拜”)的研究中借来的。⑥马克思很早就用此概念来分析商品。拜物教与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紧密相关。商品既有交换价值也有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包括两种价值之间的融合,是对商品价值的误认:即在交换体系中(一整套关系)被给予的价值被错误地认为是商品本身拥有的。所以,拜物教就是指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异化:商品本来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它中间包含并体现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经过这一层抽象,人们看不见这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反而觉得自己要受到商品的统治,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力量赋予到了商品的身上,并对其顶礼膜拜的状况。那么广告的神奇力量是不是也是一种误认与神秘化的结果呢?这种力量的实质是什么呢?
苏特·杰哈利认为,当代世界的广告也是一种拜物教。苏特·杰哈利试图在广告的分析中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和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他认为,商品拜物教中最重要的就是挖空商品的意义,藏匿真实的社会关系,通过人们的劳动将社会关系客体化于商品中,然后再使虚幻的、符号的社会关系乘虚而入,在间接的层面上建构意义。生产已被掏空,广告重新填充。真实在虚幻的遮掩下已经无影无踪。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结构下,只有当生产的社会意义消失以后,市场的社会意义才能显现出来。皮囊中空的商品形式,终归需要有某种意义加以填塞,而不管那意义有多么肤浅。⑦
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中,市场中的商品掩盖了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商品的社会意义被误认为是商品自己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对传统社会中的人来说,人们并不缺乏有关产品生产过程的信息,比如:谁生产了它?它从哪里来?它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怎样?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直接为人所见的却只有商品,生产关系是间接表现出来的。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甚至国际化,人们更加无法看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它也就更加缺乏意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不同,现在的商品并不带有谁是制作者、有什么样的动机、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的标志。如果我们知道谁是生产者,就有可能得到一些信息,但我们现在却无从得知这些信息。人与产品的互动,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知道漂亮的、代表幸福与可爱的鞋子和儿童玩具是由东南亚某个血汗工厂里的童工生产;这些人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才能拿到维持生存的基本工资;这里不允许成立工会组织,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条件,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使工人们有高得惊人的自杀率和伤残率,而伤残者又不能得到合理赔偿……如果这些信息都能被全体消费者所知,商品还会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这种意义上,广告确实是一种拜物教。它呼风唤雨的力量是由于商品的生产过程被掩盖而带来的意义的缺失。处于意义的真空状态的商品于是只能接受广告符号的任意编码与摆布。从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基本视角再反观西方的广告文化批评,我们发现他们的批评方法过多地强调了作为中介的符号的独立性。这种强调与当代以信息技术为最新特色的西方社会现实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正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最新电子通信传播技术的全面发展和消费主义的社会景观,使西方人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包括广告文化批评在内的批评方法本身看做是当前西方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症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审视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与当代各种新思潮的对话中不断保持创新能力。
注 释:
①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美]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②赫伯特·马尔库塞[美]著,张峰、吕世平译:《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③转引自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④⑦苏特·杰哈利[美]著,马珊珊译:《广告符码:消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拜物现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第61页。
⑤参见Theodore Levitt,“The Morality(?)of Advertising”,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48,no.4,July/August.
⑥参见《大英百科全书》中“fetishism”的词条,“fetishism”,http://search.eb.com/eb/article-9034143。
(作者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