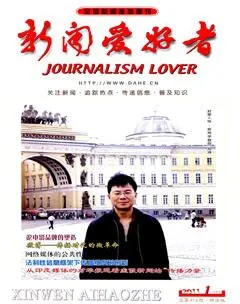乡情的执
摘要:作为土家族作家,陈川的创作不仅立足于民族的土壤,描绘真实的土家风情风貌;更以一个思考者的身份,关注土家人的生存处境,审视土家人的生命形态;而且,小说叙事话语新鲜独特,富有渝东南地域特色。
关键词:地域风貌 土家风情 生存境遇 生命思考 叙事话语
地域风貌、文化风情的书写
对地域与文化风情风貌的倾力倾情书写是陈川小说的一个亮点。陈川深爱着他脚下的这片热土,这块地处黑山(武陵山脉)绿水(鸟江)间的渝东南土地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愿意也有意在自己的作品中糅合、呈现这一特定地域的地物特征、风貌人情、风土民习。
地域风貌的书写。作为土家族作家,陈川笔下的渝东南地区也呈现出独特的地域魅力,即一种神秘、鲜活而又粗犷刚烈的地域风貌。
渝东南地处中国的第二梯带,云贵高原的边缘,这里依山傍水,这里的人们靠山吃水。因此,山和水便构成了陈川作品地域风貌的主打元素与魂灵。他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山的神秘幽深:“一条赶场大路蜿蜒在大山之中,时而在山脊,时而在深谷。到处是幽深的密林,遮天蔽日,古藤缠绕”(《塑造》);山的雄壮崇高:“大山连绵,莽莽苍苍,像是从天边涌过的波涛……大山沉默着……而博大的胸怀,无穷的力量和蓬勃的生机不正是蕴藏在这无边的寂静中么?此刻,他在灵魂深处理解了大山的这种崇高的静穆,真正欣赏到大山的壮美”(《塑造》);山的孤独肃寂:“这是一片广袤、沉寂的土地……芭茅草、灌木丛,还有一笼笼野金银花藤蔓,布置出一个苍黄、芜杂的世界,让人感到一种沉闷,一种荒凉,一阵孤独”(《那里,在远方》)。在陈川笔下,我们不仅能体验到山的迷魅魄力,也可领略到水的万种风情:“每当夕阳落到山垭,瑰丽的晚霞把她的全部色彩倾倒在阿蓬江河面,或桃红,或金黄,或紫蓝。闪烁变幻,像一个多情的女人,眨着媚眼,逗引人们投进她的怀抱。”(《汪=新传》)
在陈川的小说中,千姿百态的山和水无疑成为土家风情的承载者,从这片土家人生活生长的山水里,我们能触摸到土家人生存环境的艰难与生活的艰辛。
土家风情的凸显。作为土家族的一员。作者深爱着自己的家乡与民族,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具有自觉的民族承担意识。因而,偏僻、封闭的土家山寨构成了陈川大多数小说的叙事场景:“大山里有许许多多的沟,有一条叫灰溪沟”(《汪二》);“高岩是一个乡场,背抵大山,一壁白晃晃的绝岩遥遥在望。临面有一条小溪,水很浅……独条街,百十步,全用光溜溜的青石板铺就……两排房屋连椽接瓦”(《塑造》);“水寨耸立在眼前。两面万仞绝壁,夹一潭净水,一片死寂”(《梦魇》)。茶溪、椒溪、老街、青冈林、罩子盖、苦竹盖、诺扭湾、濯水镇,这是一个个散发着馥郁土家山乡气息的小说故事衍生地。即使是作者笔下的马喇城、石城也并非真正的城市,而是小小的边城。在这一个个寨子中,土民生活在一座座“矮爬爬的,不少屋顶盖着生了青苔的杉树皮”的摇摇欲坠的吊脚楼里。这是土家民族典型的居住民俗。陈川更让读者领略到粗犷质朴的土家日常饮食民俗:喝的是香喷喷的油茶汤(油茶汤解渴提神);吃的是包谷粉子饭、包谷洋芋饭:下酒下饭的菜是蒸腊肉,带有膻味的麂子肉,一块块肉都有巴掌大,膘肥流油,实在解馋。喝下半碗自己酿造的“包谷烧”,便昏昏欲睡了。
作为一个生活在高山恶水间的民族,土家族有自己特有的渔猎文化与习俗。《汪二》、《那里,在远方》、《梦魇》将富有土家特色的“撵仗”(狩猎)、“赶闹”(捉鱼)这样的集体渔猎活动进行了鲜活的再现。“围山撵仗。闹鱼取虾,见者有份”,这是土家人的规矩,是土家族的民俗民习。
土家族人长年生活在闭塞的山区,生活贫困,劳动繁重,娱乐方式单一。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土家族人会用独特的方式来放松精神,娱乐身心,除了他们特有的“摆手舞”、“茅古斯”、“撒尔嗬”、“薅草锣鼓”等舞蹈形式外,丰富多彩的山歌,就成了他们极为重要的娱乐方式。山歌诞生在劳动中,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土家人乐观、睿智、幽默的民族性格。通过山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陈川小说的一个特色。“唱歌莫唱扯谎歌,风吹石头滚上坡,冬水田里捡菌子,青冈林里鲤鱼梭”,这是《那里,在远方》中山野村夫劳动时唱的《扯谎歌》,风格清新幽默,体现出土家人特有的乐观、风趣和诙谐的民族气质。“凉风绕天要晴,庄稼只望雨来淋,庄稼只望雨来长,留郎只望妹才行”,这是《塑造》中火辣辣的姑娘小伙子传情达意的对唱山歌;“我想你苦来想你多,想起你来睡不着,想着了又梦见你在怀,醒来才晓得是空场合”,这是《汪二》中主人公的风流调笑情歌。在土家族山歌中。情歌数量最多且最有特色。可以说是“十对男女九对歌,十首山歌九情歌”。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情歌,其意真挚感人,情调质朴优美。是土家族男女相识、相知、相爱的媒介,既体现出土家族人的多情、诚挚和忠厚,又体现出土家族人的机智、俏皮与乐观,使土家族青年男女的爱情附上了浓厚的浪漫色彩。在陈川的小说中,山歌歌词简洁,旋律简单,虽短短几行却可以给小说增添无限的韵味空间,而且破译出了土家族人特有的歌唱习俗与文化内涵。
此外,陈川小说中还有对哭嫁、交亲等土家婚庆习俗(《心事》、《太阳下》),巫婆驱鬼的巫卜民俗,人死后的丧葬民俗(《塑造》)的征用与呈现。总之。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作家,陈川将渝东南土家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民族风情有意识地糅进自己的小说,并对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与恰如其分的彰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
对生存境遇的呈现与对生命的思考
作为土家人民的儿子。陈川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怀。熟悉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和民族文化传统,因此其创作抒写人情,思索人生,关注人的命运。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却又根植于民族的土壤,表现淳朴的民情习俗,关注民族的生存与未来,创作上有着鲜明的民族印记。
文学源于生活,陈川的创作扎根于故乡的那片土地,描写熟悉的人和事。作品浸蕴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他把创作的视野聚焦于人,表现他们的人生轨迹,思考他们的生存本真。
《那里,在远方》讲述了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刘仁和到全县最偏僻、最贫穷的罩子盖“微服私访”,了解民情。山里人淳朴、善良、热情、厚道、待人诚恳,但山里的环境却异常艰苦:“这片土地确实瘠薄。终年雾沉沉的,日照太少,所以有罩子盖之名。一入冬经常雪凌封山,寒冷刺骨,人们只能蜷在火铺上度日。出产也很少,只有包谷、洋芋……交通也极其不便。距乡政府有四五十里,而且悬崖阻路,危险难行;买一头牛犊,要背上山,老死了、累死了,就剁成块,背下山去,换回一点盐巴。”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罩子盖的人并没有退缩,靠这一片土地顽强地繁衍生息。受人尊敬爱戴的老支书,因久病而无钱治疗,可至死也不离开这片土地。在故事中,作者还穿插了龚老大与寡妇银花深沉、坚定、刚健的爱情。这篇小说给读者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山寨沉重严峻的生存环境及山民生活的贫困,龚老大与银花大山性格般的爱恋,作者更想挖掘的是山民们坚忍不屈的生命态度,是他们对土地的挚爱,是他们力求生命繁衍、壮大民族群体的原始生命力及力求改变山村落后面貌的生命祈求。整个作品呈现的是一条土家山民坚忍不拔、乐死达观的生命轨迹。
但我们又隐隐感觉到,作者要反映的不仅仅如此。正如文章中所说:“这也许就是山里人的性格吧,是固执愚昧呢?还是自尊自重?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但这于事无补,得想办法慢慢开导他们,他想。”盖上的年轻人宁愿不结婚当“单条子”,也不下山去当上门女婿;老支书宁愿死在这片土地上,也不肯到山外的医院去看病等。对山民们思想的封闭、落后与顽固,对稳固如山的民族性格惰性,陈川有了隐忧。
短篇《梦魇》更是一篇现代土家的“寓言体小说”。所谓“寓言体小说”就是:“小说文本虽然描写现实生活,由于作者理性观念的介入,赋予文本以寓言性,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这种小说的叙事模式是寓言话语,它以隐藏性的指涉方式言说人类生存的各种信息,体现人类整体生存状态和集体深层心理。文本与外在世界丰富深刻的对应关系传达出隐喻的效果,寓言话语的模糊性、多重性使文本的理性结构呈现为一种深度空间,为读者开启了多个透视文本中心的解读视角。”《梦魇》讲述了一辈子谨慎规矩木讷、年过六旬的老焉,在载送陌生人去水寨的水路上第一次看见了枪,也第一次打了枪,但这个足以让老焉一辈子值得自豪的奇遇,却让他和家人遭到了寨子里其他人的讥讽和嘲笑:“人家三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也没放过盒子炮呢,他老焉不是做梦么越活越糊涂哕,哈哈嘿嘿嘻嘻嗬嗬……”在德高望重的三公的劝说下,老焉终于相信打枪的奇遇不过是自己做的一场荒唐的梦,并从此一病不起。《梦魇》的旨意丰富而深刻:不被人理解、孤独无援的老焉,嘲笑、讽刺老焉的寨子山民,心地善良却无法让人同情还带有悲哀的三公,小说触及的是土家民族超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模式中沉淀的集体深层文化心理的积习和惰性,反思的是土家人生命形态上的心理萎顿和生命性格中的偏失赢弱。
陈川的目的是显明的,他的小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土家人的生存境遇,审视土家人的生命形态;同时,站在救赎的立场,揭示土家人生存的孤独和荒诞、生存的尴尬和局促,揭示土家人在现代生存环境中生命的挣扎、扭曲甚至异化。反映生活、关注生存、思考生命使陈川的小说散发出较为持久的艺术魅力!
冒着地气的叙事话语
作为渝东南土家民族文学的一个代表,陈川的创作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一种诞生于这片土地上,有着浓郁地域色彩的叙事话语。这种语言既有着高原峡谷文化的怪异与奇崛,也有着与山相依的水文化的鲜活与灵泛;既有着与自然山水相接的灵气与飘逸,也有着民间烟火的平实与粗俗。“喂,为哪样哟?恁大的太阳,来洗澡吧,好凉快,好安逸哟”(《汪二》),“你默嘛,盖上又穷又苦,有哪点留恋头”(《那里,在远方》),“你下细默默,我哪里说走展了”(《心事》)……这是贴切形象的地方口语;“脸愁得变成核桃壳儿”(《酒瓶》),“包谷个子如盐荷包大小”(《那里,在远方》),“就你这鼎罐不醒事”,“喉咙像遭包谷芯堵住了”(《心事》),“太阳像被一种魔力送上天空的簸箕”(《太阳下》)……这是地道活气的鲜亮比喻;“正该”、“周遭”、“扯谎”、“包瞒”、“撵仗”、“赶闹”、“逛逛神”、“做活路”、“毛脚杆”、“老蜷了”、“挨拢去”、“花眉花眼”、“二不挂五”、“天才麻麻亮”……这是生动形象而又贴切的地方口语。这些语言虽然不及书面语正规、严肃甚至还有点粗俗野蛮,但正是在这一类话语中,我们读出了土家人民的语言智慧与民族本性。《民族文学》老编辑白崇人赞誉陈川“把根深扎在自己民族和地区的生活土地上”,从语言方面来说,陈川确实是扎根于民族生活的沃土,吸收、提炼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口语。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小说叙事话语。虽难免有粗糙、生硬之处,但他的这种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应当值得肯定、鼓励的。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陈川可谓是一位认真的作者,其小说散发着浓郁的地域和民族色彩。他以独特的民族历史、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传统做根基。表现出对民俗民习的关心和热爱,对民族民性、人性的关怀和思索,对民族话语的开掘和调用。他的作品值得我们去关注!(本文为重庆市教委科研项目“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SK004)
注释:
1、丁世忠:《重庆土家族民俗文化概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2、宋永祥:《关注生存
沉思生命——论土家族作家陈川的小说创作》,《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8),第51页。
3、陈川:《梦魇·序》,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编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