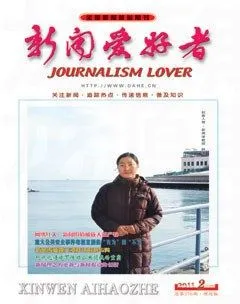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电视直播的“有为”和“不为”
摘要:本文对菲律宾人质事件媒体责任论进行分析,指出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在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进行现场直播时要充分考虑其报道方式对事件本身的解决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现场直播应在“有为”和“不为”间有所取舍。媒体从业人员应科学辩证地理解而非不加限制地滥用“新闻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媒体的商业利益不能独立于社会道德责任之外。
关键词:公共安全事件 现场直播 媒体责任 媒体“有为”与“不为”
电视直播在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无疑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新闻角度来讲,现场直播是电视媒介的最高境界和魅力所在。有专家对电视新闻现场直播下的定义为: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把新闻事实的图像、声音以及记者对事件的报道(包含现场采访、解释、评价)转化为电视信号并直接发射的报道方式。①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在欧美,直播节目已占新闻频道节目的70%以上,65%以上的突发事件都有直播报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场直播节目的比例也较5年前增加了4倍,40%的突发事件会有电视直播。②
媒体直播是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首选
近些年来,对各种自然灾害、恐怖、社会骚乱等突发事件,电视和网络的现场直播越来越频繁。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具有偶然性、突发性、恐怖性、不可预见和不可控制性等特点,而且其影响力强、涉及面广、持续性强,对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成为电视新闻媒体扩大影响、争夺受众、参与竞争的重要领域。第一时间对这些事件进行动态报道可以让公众清楚地了解事件发生的每一过程,关注危机事件发生中政府的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使公众形成公共安全意识,更好地预防和化解危机,而这正是媒体的职责所在。同时,对重大危机事件的现场同步报道对扩大电台的影响力、提高收视率也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因此现场直播是电视、网络报道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首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直播都是最佳的选择。
菲律宾人质事件媒体责任论
2010年8月发生在菲律宾的被辞退警察劫持香港游客的事件,造成8名游客身亡。菲律宾警方在解救人质中暴露的不足受到各界的批评,菲律宾的国家形象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大量媒体介入现场进行电视、网络直播的行为也受到包括菲律宾总统、菲警方以及众多网民的诟病。悲剧发生后,菲总统指责是媒体对事件进行的“全景式”(“bird’s eye view”)的报道直接导致劫持案局势恶化。菲警方总结教训时,一直把媒体的“现场直播”当做导致解救失利的重要原因。当时,菲律宾ABS-CBN、GMA、ANC、Tele-Radyo、Net21 and Q和ABC5频道,甚至连政府的频道都在报道这场人质危机。他们都报道了围绕在旅游大巴周围的警察站,包括突击队试图从大巴后面接近的行动。劫匪门多萨可以通过旅游大巴内的电视清楚地看到现场直播,掌握警方的行动。广播和电视的现场报道让门多萨在警察试图靠近时,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根据事后对三位幸存者的采访,门多萨是看了电视直播后情绪恶化的。之前他向人质保证不会伤害他们。直播警方野蛮地逮捕劫匪弟弟的画面显然激怒了他。事件的结果是在菲律宾警方发动攻击的过程中门多萨开枪打死8名人质。地方政府(DILG)大臣Jesse Robredo认为媒体的播报方式使警方在与门多萨谈判时无法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他说媒体应更多地考虑人质的安全,应当起到配合警方行动的作用而不应只考虑收视率。媒体监督机构“媒体自由和责任”在Twitter上链接了他们2007年就Armando Ducat Jr.’s的绑架师生案写的评论。其中提到因媒体参与而引发的恐慌及导致的人质安全问题。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事情,国会议员Luigi Quisumbing说他和其他法官考虑将提出议案提议在有军方和警方参与的敏感事件中要对媒体进行新闻管制。他强调说这并不意味着干涉媒体自由,一旦危机解决,媒体完全有权利进入现场对d22c0cda363154a02292dd559a76f382c676afef95688edd3991696bb5e270b3事件做详细的报道。③
从上述评论中不难看出,对类似公共安全事件的“无准备直播”对于事件的发展无法预期,难以有效控制节目内容,报道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人质或恐怖事件中,危机事件的直播会对各方主体形成巨大心理压力,很可能干扰危机的解决,同时播出的血腥场景也可能对观众造成心理伤害。④2008年11月,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95人死亡。这次事件也成为印度媒体的一场新闻直播战。一些媒体将一些十分敏感的行动计划曝光,当时电视画面上充斥着安全部队在各个地点进行部署的镜头。在印度警方切断事发地电视信号后,恐怖分子仍能利用手机上网实时了解反恐行动的情况。事后,印度人愤怒地称,这些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几乎成了恐怖分子的“情报局”。
媒体直播报道应在“有为”和“不为”间有所取舍
媒体直播报道重大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原则。此次菲律宾人质事件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媒体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现场直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大家清楚发生的具体细节;另一方面,它也为劫匪提供了情报。对于媒体而言,对此类事件的现场报道应当在“有为”和“不为”间有所取舍。“有为”就是要恪守媒体的职责,将事件的原貌呈现给受众;“不为”则是充分考虑媒体的社会职责和道德职责,考虑其报道方式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媒体进行这类事件的直播,应该和警方充分合作,有选择地公布某些信息,必须尊重个人隐私,考虑到事件的有效解决和受众的接受心理。⑤按照美国学者斯特奇的“危机传播阶段”理论,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该按照危机的进展采取不同的信息处理和报道议程。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在性命攸关的环境中,媒体采取全程画面直播的方式,的确有欠考虑,这使得歹徒通过车载电视能够随时掌握警方的部署,尤其是其弟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更是使其情绪失控。直播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在这次事件中媒体也应该吸取教训,是否应该对相关的画面资料进行些处理。比如,容易激怒劫匪的画面可以不播。或者,部分内容可以考虑以文字的方式呈现,这样,可大大降低激怒绑匪的可能性。⑥当然,最大的原则是不给恐怖分子帮忙。在2002年10月莫斯科轴承厂剧院人质事件中,俄电视现场直播节目时无意中使恐怖分子了解到剧院外的俄军行动。俄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对恐怖分子的攻击计划。事后,俄媒体汲取教训,并签署了自律公约,如不能直播对恐怖分子的采访,恐怖事件期间不采访受害人家属,不报道部队调动情况等。另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利用媒体误导犯罪分子。1997年,在日本驻秘鲁使馆人质被劫持126天后,秘鲁特警成功地解救出所有人质。实际上,秘鲁警方在对媒体披露信息时进行了有选择的管制,就在特种部队紧张备战的同时,歹徒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却是“政府正认真考虑劫持者条件”的“好消息”,并因此放松了警惕。⑦
政府和警方对媒体现场直播应有一定的管制。国际协议不鼓励对采访警方行动和其他报道进行直播。对于有军方、警方参与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只有权威机构、当事者直系亲属才有权进入现场。政府对媒体介入重大危机事件应该有所控制,应把媒体的现场直播纳入危机现场管理范畴。危机事件发生后,警方应设立明确的隔离线和管制区,摄影、摄像记者经批准后可以在管制区活动,但需遵守警方的管理。采用技术手段,屏蔽劫匪的一切电信信号,让他们不能看电视、听广播,无法通过手机、电话和外界联系。即使有媒体直播,也要有内容控制。例如在解救俄罗斯大剧院人质事件中,俄罗斯军方不允许事发现场范围二公里内的任何非官方媒体进入。由官方向媒体提供一些通过审查后认为不会产生影响行动的电视片段来满足媒体。俄罗斯特种部队突然发起强攻的时候,直播现场马上中止。管制不等同于限制新闻自由。它是为了将媒体参与现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媒体的商业利益不能独立于社会道德责任。媒体现场直播除管制外,还应强调媒体人的“自律”,媒体从业者应该牢记其服务的传媒机构掌握着传播资讯、引导舆论、左右公众思想的宣传机器,其肩负着比其他行业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所以应以正确的方式行使其力量。媒体从业人员科学辩证地理解而非不加限制地滥用“新闻自由权”和“公众知情权”。媒体的商业利益不能独立于社会道德责任之外。
西方新闻界有句俗话: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人类的很多灾难成了新闻报道的难得主题,但报道的方式却折射出个别媒体人道德责任的缺失。某些电视台为追求轰动和制造耸人听闻的效应,就把直播场景选择到最直观的、最悲惨的“第一现场”,不择手段地寻找最能吸引眼球的“瞬间”,甚至捕捉并放大当事人及其家属在灾难面前所表达出来的悲痛情绪。这实际上是把观看别人的苦难变成了一种娱乐方式。⑧1975年度“荷赛”最佳新闻照片《波士顿太平梯事故》,抓取了两姐妹从太平梯坠落的瞬间。1994年度获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拍摄了一名饥饿的苏丹女童被秃鹰眈眈欲食,这些作品的作者都遭遇来自全社会的道德追问。有人认为记者不该冷漠地、客观地记录眼前发生的事件,而应该采取措施去防止悲剧的发生。而《饥饿的苏丹》的作者虽然在拍完作品后将秃鹰赶跑,但最终还是无法承受社会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折磨而自杀。据菲律宾国家警察署发言人克鲁兹介绍,在人质解救的关键时刻,曾有一些媒体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了劫匪门多萨,但与其通话的目的却是怂恿劫匪“不要接受”警方的条件。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这些媒体已经完全丧失了新闻人的职业操守,毫无道德责任感可言。
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媒体必须始终恪守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论强调媒体不能滥用自由。自由是附带着责任的,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割的。⑨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切实关心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当危机事件爆发时,媒体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应该承担起关怀人、关心人、安慰人的社会责任,在“抢新闻”和“抢生命”的衡量中应该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这是媒体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文素质。在现代社会,一个不能维护人的生命价值的媒体是一个缺少人道精神的媒体,是一个缺少最起码的人类良知的媒体,在受众眼里就只能是一个冷酷的传播机器。那就意味着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触犯了公众和民意,必将损害媒体的社会形象。⑩当新闻职业与社会道德产生冲突的时候,社会道德责任高于新闻职业责任。美国新闻评论家约翰·赫尔顿(JohnHolden)认为“事实上,如果新闻工作者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
菲律宾人质事件悲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警方经验不足、指挥不力。不能完全归咎于媒体,况且媒体的报道暴露了政府、警方的不足有利于今后的改进。但必须强调的是,在涉及人的生命危险的突发事件中,不加控制、不考虑后果的直播有时的确会影响到事情的解决,以警方管制为主的“他律”和以媒体人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感为约束的“自律”,直播时的“有为”和“无为”都是非常重要的。
注 释:
①韩海钢、赵伟东:《浅谈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选题》,《新闻传播》,2007(10)。
②④⑦王传军、季双成等:《现场直播考验国家形象》,《环球时报》,2010-08-30。
③Kara Santos:《Media Take a Hit in Hostage Crisis》,《Asia Media Forum》,2010-08-28。
⑤章友德:《菲警方处理劫持人质事件表现遭质疑》,《新民周刊》,2010-09-01。
⑥《菲律宾人质事件中的“越位”与“缺位”》,《环球瞭望》,2010-09-01。
⑧⑩魏明革:《电视新闻现场直播中的伦理抉择——以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现场直播为例》,《新闻爱好者》,2009(7)。
⑨陈力丹:《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当代传播》,2007(10)。
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体育传媒系)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