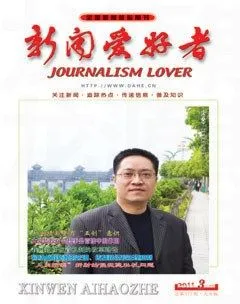迈克.摩尔的影像语言与精神特质
迈克·摩尔在纪录片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1989年的《科伦拜恩的保龄》获得了第7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以及戛纳55周年特别奖;2004年的《华氏911》获得了第5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2009年的《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入围了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他在赢得了巨大荣誉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好的票房,但是由于他全新的创作手法和激进的政治立场,也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批评。但在笔者看来,摩尔的纪录片并不能与纯粹的娱乐画上等号,也不能与流于欺骗的形式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对新纪录电影理念和精神的涂改和曲解。迈克·摩尔对纪录片表现手法的探索拓展了纪录片的表现力;他所彰显的反思历史和质疑权威的精神品质也值得肯定和赞扬。
作者政策:主体介入的意义生产与文化深描
真实是一个人人渴望却无法到达的彼岸,它永远保持着相对的面貌,更何况在这个模拟时代,“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①在这个五彩斑斓又子虚乌有的后现代社会,我们分不清哪里是实地哪里是幻境。直接电影所提倡的较为单一的纪实手法在挖掘真相面前似乎显得力不从心。迈克·摩尔作为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人物,秉承了新纪录电影的理念:拒绝终极的真实,认为对真实的追击过程比结果更有意义。他尝试采用虚构的表意手法对真实的过程进行干预和构建,旨在揭示“生活如何成为这样”。
迈克·摩尔的文本书写是主动介入、积极地运用视听语言进行的意义生产,而不是貌似公正的冷眼旁观。既然纪录电影的真实只不过是“关于现实的神话”,那么只有积极地对现实世界进行主观阐释才能展开真实的不同维度。由于纪录片不是对物质现实的机械复制或是简单还原,而是诠释了一个具有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体(它与制度、传统等社会因素相关联)。因为这一现实主体的复杂性,所以需要创作者对它展开文化深描。这样,文本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丰满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贫乏苍白的物质本身。这样的书写方式让观众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并引导观众怀着质疑的、开放的心态去看待社会和历史。
另外,摩尔的几乎所有纪录电影都采用了个人化的视角和个性化的解说,明显标示了这是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主观意见。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不具有欺骗性,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观众的认同。他还常常充当采访者的角色,出现在镜头前。他把个人形象作为影片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这个头戴棒球帽、不修边幅的胖子俨然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这样观众自然会对他产生亲切感和信任,他在影片中总是以个人化的口吻,态度诚恳,语言幽默,既不矫揉造作也不粉饰太平,使得观众对他的观点感同身受。比尔·尼科尔斯认为:“通过讲述包括影片创作者在内的‘我们’,影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亲近性,这种亲近性能够变得非常有说服力。”②
后现代意味的修辞手法
著名电影家布努艾尔曾经说过电影的潜能与成就之间严重的不均衡。迈克·摩尔似乎非常善于利用视听媒介的优势,发掘影像语言蕴藏的巨大潜力。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后现代修辞,对生活碎片的重构看似浮光掠影,实质上却是精心筹划。在摩尔看来,以艰深晦涩的方式来表现严肃复杂的政治问题显然是不明智的。在这个充满符号暴力的后现代社会,单一、乏味的纪实影像已经不能满足习惯了视听刺激的人们。于是,影片采用了故事化叙事,并将纪实段落与大量的娱乐元素(比如脱口秀、音乐电视、特技效果)拼贴,用解构的智慧释放了视听元素蕴藏的无穷潜能。
影片中那些家庭录像、电影片段、电视新闻、广告、音乐电视等不同质感的拾得片段与实时采访、真实再现杂交在一起,没有使影片显得浅陋而平面,反而使述说更意味深长。滑稽戏谑的表现方式,反而使得讽刺更为辛辣。正如鲁迅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