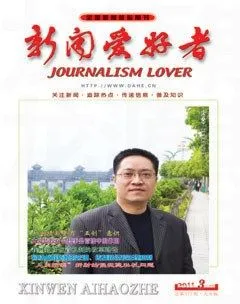“新锐”杂志的大众化趋势
摘要:近几年涌现的新锐杂志中,《新周刊》颇具代表性,通过大众文化视角对其透视,不难发现该杂志标榜新锐精英化,典型的小众定位背后却是大众议程设置,内容选择将交际话题、私人话题上升为大众话题。实质是遵循市场新闻学,拥有最大多数的社会主流消费者,消费文化议题,体现在新锐杂志中的是一种个性化的自我张扬,它是非功利的;而作为大众传媒的杂志又无可避免地成为消费文化的传播者。
关键词:新周刊 精英化 消费主义 分众化
自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与世界交流的日趋频繁,我国的期刊业在发展中逐步成熟,竞争也日趋激烈。从宏观角度看,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与读者需求的刺激下,期刊逐渐由“大众化”向“小众化”转移,刊物定位更加明确,读者群更为稳定。从微观角度看,精良的制作与时尚的包装也赢得读者的青睐。
诚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所说,一旦自我标榜“新锐”,就几乎等于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纵观21世纪的媒体,无论是纸媒还是电子媒体,“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都可以视为商业法则殊途同归的表述:自我设定特别的意义,进而获得某种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最大基数的社会利益交换,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其基本前提要素有三:最高端的精英定位(内容),最大的社会影响(人群),最大的价值回报(利益)。
新锐还是大众:一枚钱币的两面
创办于1996年8月18日的《新周刊》,经过12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这本中国第一本由本土传媒人创办、本土社会生活资讯为主体而真正具备国际水准的杂志,始终保持对社会潮流动态的高度敏感,张扬无情剖析的犀利风格,并创造出多种新型报道模式,成为中国期刊市场上最具代表性和舆论影响力的杂志之一。
打开《新周刊》主页,硕大的“锐”字全面占据你的眼球,一股精英之风扑面而来,仿佛在声称“我们倡导的便是新锐先锋的精英文化”,每期《新周刊》封底有“知道分子问卷”,旨在普及常识,扩大精英范围。如同一枚银色钱币,总有其正反两方,“新锐”和“大众”两个自相矛盾的字眼在《新周刊》成为可以随时翻转、各行其是的两面。新锐其实是典型的小众定位,小众意味着低发行量、低知名度甚至杂志的边缘化、非主流化,虽地处广州,《新周刊》编辑部同人们却避谈小众,不是上层读物(high-quality press),也不希望仅仅是对上层的影响。《新周刊》针对都市中产和小资人群,在意他们的购买力和公共话语,而这批“主流大众”,又恰好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主流人群,如果“主流”的界定仅仅是从人口基数上来说的话,在这点上,《新周刊》不动声色地偷换了概念。
新概念引领趋势,“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新周刊》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6~1997年底,时事新闻杂志阶段,内容为时事新闻综述;1997年底~1999年,内容已经开始逐步转向对社会时尚话题倾斜;1999年~2006年,内容从对时事新闻的报道,倾向于抽象和另类的新锐文化,进而开始策划制造概念。可以说《新周刊》是媒体同行和创意工作者眼中的“话题发源地”。“飘一代”、“她世纪”、“第四城”、“无厘头.com”、“80年代下的蛋”、“忽然中产”、“贱客来了”、“女人生猛”……《新周刊》众多经典专题以及一年一度的“大盘点”、“情人节特辑”等,至今仍在不断被人引用和演绎。当代中国庞杂繁复,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现象,《新周刊》的文章,就像人体切片,断流截出其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犹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
这份每期128页铜版纸全彩印刷、标榜所谓的精英杂志辟有“专题”“城市”“观察”“人物”“品牌”“文化”“设计”“写作”“卖点”“漫画”“图片故事”,封底设有“知道分子问卷”等栏目。从新周刊的栏目设置及其内容基本可以看出,在时事与生活之间,它更关注生活;在生活与时尚之间,它更在意时尚。它的目标读者群定位在25岁左右、关心时事时尚、追求个性表达、有主见、有思想、有一定消费能力的阅读人群,也就是都市中产阶层。“国际经验表明,当GDP处于1000~3000美元时,中产阶层在社会中会大量出现,生活方式会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这样,以往传播市场上同质化的共性需求主导模式将会转变为分众的、差异化的信息需求模式。”正如《新周刊》在161期的封面文章《人人都爱看杂志》中如是告白:“并不是所有杂志都对你胃口,但总有一份为你而生;关于你这类人的生活与生存、价值与信仰、情感与趣味、健康与保健。”有人说这是《新周刊》在受众导向时代依然我行我素的托词,也有人说,这是《新周刊》在个性化阅读时代里仍然可以无为而治的智慧。
兜售话题,贩卖意见,让“新锐”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时代,一方面,大众媒介飞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众,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杂志在这样一种媒介生态中,其生存有特殊之处。而《新周刊》以话题制造与引领者自居,设置中产阶级精英们热衷关注的议题,资源高度整合,将时事生活中最热门的海量信息进行收集、分类、梳理、判断,以独到的视角将资源性的信息进行加工、生产成为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产品,满足“资讯相对过剩时代”精英们的资讯需要,使之通过消费证实自己的价值。
不用策划,《新周刊》本身的封面艺术与大字报式的标题已构成绝对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周刊》任性中的韧性。寻找话题噱头、策划、做专题排榜、城市生活甚至遣词造句字里行间都透着小资精英的风范,《新周刊》不仅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贯穿始终,而且一度颠覆了中国期刊的办刊理念。当更多期刊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便归于寂寂无声之后,《新周刊》依然是中国期刊界鲜活的三叶虫。
所谓大众产品的生产流程
内容选择:将交际话题、私人话题上升为大众话题。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在这个张扬个性、崇尚包装的时代,虚拟的时尚,孕育了无数新生代事物的诞生。作为一份时事生活刊物,封面包装如同求职者给面试官的第一印象,先从心理上接受你,才能真正接纳喜欢你,从而养成每期的“约会心理”。《新周刊》新在打破旧有模式、新在视角和新概念,它对读者最大的冲击直接来源于视觉。张扬、先锋、生猛、独到,是其鲜明的特点。
麦库姆斯和肖恩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公众的议题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个人议题”、“谈话议题”、“公共议题”。选题最好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也就是所谓的“热门话题”。如果选题不能体现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不能对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进行有效的指导,受众的兴趣就会大打折扣,也就不值得在大众传媒中传播。大众迫切需要学术精英对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进行阐释和解决。选择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精心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提出真知灼见,最终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
话语权的重构。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时事热点,一向是《新周刊》所倡导和所长之处,轻车熟路背后是其对视角和话语的选择,平民视角与高端话语相得益彰,在不断的解构与建构中,《新周刊》完成了对自我的精神救赎。
受众的既有认识是诸多观念的有机结合,各种各样的常识是他们构建自己观念世界的基本骨架。其实常识原本就是既为公众普遍知晓,又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所谓重构常识也就是用新的观念来替代既有观念的常识地位。由于常识在公众知识的体系架构中具有这样的独特地位,使得对它的重构尝试必然会同时遇到双重境遇: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会招来质疑。重构必然意味着要有所颠覆,本身就足以引来公众的关注。以《新周刊》王宝强的框架为例——王宝强:不能人人都是许三多/我们都丢掉了,许三多没有丢/康洪雷的7个关键词/《士兵突击》群像社会人格分析/钝感力的时代风险与做老实人的代价/许三多身上的贵人学/10位年轻人眼中的人际法则/中国人的底层生存逻辑/真实的《士兵突击》影响系列。专题名为“顿感的力量——许三多:浮躁社会的反义词”。这令人不禁想起渡边淳一曾出版过一本名为《钝感力》的小说,这个时代不是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往往走得过快过急,失去了人本性最纯最真、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部分。《新周刊》“锐”与“钝”的强烈对比产生的舆论影响力,新知由此产生,成为街头巷尾大众热议的话题。
对既有常识的颠覆和新常识的建构在逻辑上有先后秩序,它们彼此相互提供支撑,但是在传播的时间上却是同步的,破与立几乎同时进行。在颠覆既有常识与建构新常识的同步推进中,《新周刊》不仅有效而持续地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愿意关注甚至不得不去关注的注意点,又通过对注意点基本完备的诠释增进了刊物自身的公信力;公信力的有效提升又使得它挑战、颠覆、重构既有常识的话语权力的持续攀升。各个环节循环作用的结果就是,《新周刊》不仅稳稳地在同类期刊中占首席地位,而且它提出的话题越来越容易直接而迅速地成为公共话题。
实质是市场新闻学:只有消费者
在中国传媒界,公信力是显规则,商业化是潜规则。一份杂志总与一代人或这个时代的蜕变紧密相连。《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曾经的诗人,上世纪80年代的传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那个理想主义,只是现在,指点江山成盘点江山。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时代变节之后,理想青年的指点江山变成了调侃,新锐不得不向消费主义靠拢。读者成了消费者,新闻成了产品,传播领域或曰信号领域成了“市场”。随着商业逻辑对新闻部门的渗透,新闻业开始为市场需求服务。为市场服务和为公众服务是否矛盾,成了关注《新周刊》等“精英”杂志的人们值得思考的两难问题。
诚然,一本杂志的好看,首先要锁定忠实的核心受众,牢牢抓住他们的收看口味还有腰包,读者的单一角色已然变化,他们针对的是具有消费能力的都市中产,广告插页更是大手笔,高端人群必备的几大件都有涉及,品牌效应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联通、OMEGA、凯迪拉克、各种笔记本、GE、汉莎航空等等。如果说《瑞丽》、《时尚芭莎》等如行走于水泥森林中的都市丽人,那么《新周刊》就好似身着POLO、手举高尔夫球杆的新晋城市白领,他们游走于主流与边缘之间,冷眼看热风,自得其乐。
消费主义新闻学。获得最大化利润的商业目标主导着新闻生产,以至于理性运作的新闻部门必须照此行事,展开相互竞争,尽力提供成本最低、受众最广的内容组合,为广告商获取其最感兴趣的消费者,并最终保护赞助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新闻生产的新闻理论:一个事件(议题)成为新闻的可能性,与事件的重要性成正比,与认为内容重要的受众规模成正比。市场观要求报道的倾向性有利于媒介企业、广告商、母公司和投资者,与之相反,新闻观则要求报道中的倾向性应当尽可能少。
不管新闻部门的选择逻辑是哪一种,新闻内容必须具有吸引力。因为新闻生产必须基于与消费者的自愿交换,没有人愿意被迫收看。吸引力是一种商业需要,但对于传递信息来说也是一种必要手段。
关于吸引力的两个维度,一项有关新闻之“使用与满足”的综合研究显示,人们基于两个基本原因消费新闻:第一主要是知识上的,第二主要是感情上的。当然,娱乐比引导能吸引更多的受众。
走向新闻重商主义。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万物因缘而动,需要跨界、跨域、打破时空,找到甲事与乙事之间的巧妙关联,发挥社会学想象力,联结小事件小人物与大背景以阐明观点,这正是杂志报道的长处,是电台、电视用话筒做不到的。当然电台、电视有自己擅长的“五个W”语境。直到网络新闻兴起,互联网方式——大规模协作的新闻写作——将终结所有传统媒体的报道方式。新周刊将来或许会步入这样一条多媒体融合的发展道路,步入实用性、商业色彩浓厚、综合媒体融合的趋势,开创属于自己独有的精英大众化杂志新风尚。
结语
一本《新周刊》,市价是15元;到了夜市地摊上,两元钱就可以出售。对于《新周刊》而言,它认可的交换是第一次买卖,而不是第二次买卖。其实,白领是一种大众化存在,但是相比于夜市收旧书的市民,后者更是一种大众化存在,社会基数更大的“普罗大众”。在这里,《新周刊》出售的是意义,白领消费的是意义,而只有市民,可能是在阅读。《新周刊》日益成为一个“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杂志读物的提供者,它从白领“大众”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在底层大众手中回归真正的阅读。
《新周刊》就这样在“新锐”与“大众”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它一方面进行的是物的生产,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概念,开掘最大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完整的人的生产——生产出一批很大众的都市新中产、新白领,来消费它的意义。在这个双重生产流程中,“新锐”杂志的读者已不复存在,只有主流的消费者;它的产业链决不会仅此而满足,意义消费必然会形成更长的利益链条,会在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中继续延长,将生产概念进一步大众化。
参考文献:
1.李幸:《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莫林虎:《以“概念”引领趋势——论〈新周刊〉的生存策略》,《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月第10卷第2期。
3.喻国明:《中国期刊业: 蕴蓄着爆发式的成长》,http://post. baidu. com/f? kz = 10578455.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新周刊》杂志社:《新周刊2007年度佳作》,漓江出版社,2009年版。
6.《新周刊》杂志社:《向中产看齐,一个阶层和他引领的生活》,广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刘玉清:《精英文化借传媒走向大众》,《传媒》。
8.《新周刊》,《2008中国电视节目榜》,http://ent.sina.com.cn/f/v/nwtvchart2008/
9.李幸:《大众立场 李幸电视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约翰·H·麦克马那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 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