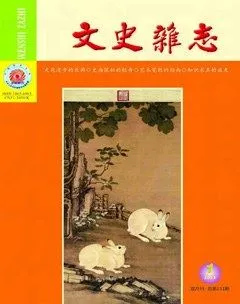胡世安和《译峨籁》
有关峨眉山的志书,流传至今,最早的当数明末清初胡世安编著的《译峨籁》[1]。
胡世安(1593—1663),字处静,号秀岩,又号菊潭,四川井研县人,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顺治初年入清,官至一品。胡世安博学多识,工诗文,著作有《秀岩集》、《异鱼图赞笺》等三十余种存世。
胡世安一生喜好游览名山大川。他曾于明末三次(分别是1619年、1624年和1639年)游览峨眉山,深深地为峨眉山秀美的风光所吸引,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并且对前人所著有关峨眉山的志书进行详细考证,搜辑唐宋以来诸人之诗之纪,加上自己所作诗文,“汇成帙,题曰‘译峨籁’,盖一家言也。”[2]
关于《译峨籁》刻印成书的年代,1997年出版的《峨眉山志》收录有陈具庆《译峨籁序》载:“丁亥(1647)秋初……先生(胡世安)于是发其旧集,广以新收今古艺文。”又王铎也为《译峨籁》作序,而王铎卒于1652年。故《译峨籁》刻印成书当在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
胡世安是抱什么观点编著《译峨籁》的呢?印光法师在《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中讲到:“当明季时,胡世安公好游山而言佛。”实际上,胡世安信奉的倒是道教。他在明清两朝都为高官,自然与厌弃世荣无关。
胡世安虽然在清朝仕途显达,但清人对他并不重视。《清史》中《贰臣传》有他的传,仅寥寥三四行,看不出他的思想脉络。在《井研志·胡少师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赠公(即胡世安的父亲)尝病,公蔬食,诵道经三稔乃已。”他的父亲病了。若他们父子是信佛的,为了祈祷父亲病愈,必然就会诵佛经而非道经了。可见胡世安的家世是信奉道教的。
峨眉山自先秦以来,就以“仙山福地”著称于世,是道教的第七洞天。千百年来,为许多道教徒所向往。胡世安在《峨山图说》一文中讲:
余既集众言以测厥蕴,先兹图以晷厥仪,三百余里郛郭,直欲尺寸规之,以引游绪,可谓操约而愿奢矣,世有崇域外观者,小中见大,略处稽详,则第七洞天法界,可决皆纳之矣。[3]
这段文字,实际已把胡世安先后三次游览峨眉山的原因挑明了,也把他写作《译峨籁》的动机交代了。在民国许止净的《峨眉山志》中,为了宣扬佛教,把上段文字中的“第七洞天法界”改成“普贤愿王法界”。同样的情况还有,谭钟岳的诗作《萝峰晴云》“峰庵到此学仙余,太史虎臣曾结庐。跨鹤飞凫踪又渺,晴云一片卷还舒。”[4]这首诗在许止净《峨眉山志》中被改为“境幽正好学无余,太史虎臣曾结庐。佛圣来迎踪已渺,长空万里日光舒。”以致于印光法师不察,遂以为胡世安是“言佛”的了。
胡世安是道教倾向甚重的人,必然要将其信仰载入其著作中。因此,《译峨籁》在保存材料方面,尤其是道教材料,是有贡献的。胡世安虽然信奉道教,但并不排斥佛教。他在明崇祯乙卯年(1639)所作《题喻广文峨眉山志》中说:“峨眉既不以普贤显,亦何必黜普贤以显峨耶?”[5]甚至他很赞同仙佛同宗。《译峨籁·道里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庵前左上,为吕仙祠,祠前重楼瑰玮,奉大士于上,弥勒居中,嗣又增修新殿及静室、香厨,以栖僧众,于是仙佛同宗。
这说明在明末这一时期,峨眉山道教仍在活动,只不过是在同日愈兴旺的佛教的和平共处中力求生存而已,并非印光法师所云:峨眉山“道教绝响,已千余年。”[6]
胡世安生于明后期,那时朴学尚未兴起,明人治学不够谨严,甚至空疏。《译峨籁》也难免存在一些考证不实的问题。如该书中载有“隋智者大师于危子石建呼应庵,日游神水,夜宿于斯三年。”智者大师一生从未入蜀,怎会在峨眉山修建呼应庵,并且住了三年?又如讲“唐三藏法师自西域还,至峨眉山九老洞。”玄奘法师西去印度取经,历时十七载,功成回长安,一直从事佛经翻译,没有译完就圆寂了,何得有暇来峨眉山九老洞?无怪印光法师要批评胡世安“未息心研究”,以致“殊多讹谬”。[7]
胡世安为一代显宦,大文人,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他编著的《译峨籁》,一经刊印流传,立即引起世人的注目,而其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也随之显示出来。该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读者直观地了解到峨眉山之奇胜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正如王铎在《译峨籁序》中所评价的:
今观菊潭公纪载之文,批根像末,探络百匿,有衍蓄,无禁材,若俎豆之列几席也。异哉!峨之据西南也,为中国分界,黏天无壁,盘古之雪,伏羲之洞,造物者固私之,守以奇狒、怪彪、龙马,不肯为人耳目近玩。是故,沉溺富贵者自穆其色,往往憎猩鼯之群,不欲与泉壑邻也。人踪寂寥,即宦游于蜀,亦鲜至焉。菊潭好奇山,数登跻斯,集邃剔险拾,众胜有基,各得其嗣。从奚囊中,携一参天两地之峨眉,而柳子黄溪、钴姆咸为臣妾。往翕道光,近事刻新,岂非斯山平生一大幸欤?[8]
这表明该书作为“助卧游”之著作,是非常出色的。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译峨籁·道里纪》,详细地记述了胡世安在明末游览峨眉山的见闻。它随登山路径的延伸,逐一记述了沿途所见的大小寺庙,数量达八十余座;又围绕一座座寺庙,将相关的自然风光、历史掌故、文物古迹、民间传说等有详有略依次道来。该书对于一些重要的胜景奇观,或具体记述,或形象描绘,或叙议结合,尤其是对佛光幻境,还能探究其源,虽然文字不多,却给人留下了身临其境的深刻印象。它所涉及的内容,比王士性、袁子让、曹学佺、尹伸等人所做的游记,更为详细、具体、全面、系统得多,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展示明末峨眉山的历史画卷。
作为记述峨眉山的专志性的著作,《译峨籁》后来成为清康熙年间蒋超编著《峨眉山志》的蓝本,被一字不遗地收录进《峨眉山志》中。
注释:
[1]《译峨籁》原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1986年由峨眉县志办骆坤琪、郑必辉二位先生手抄回峨,后由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铅印面世。
[2][5][6][7]许止净:《峨眉山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293页、296页、5页、5页。
[3]《峨眉山志》,清康熙二十六年刻印。
[4]《峨眉山十景图咏》,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
[8]《峨眉山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页。
作者单位:峨眉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