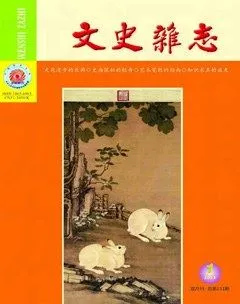谈谈中国小品画
2011-12-29 00:00:00陈沫吾
文史杂志 2011年1期


中国画的创作一般有两大类型的作品:一是精心构思、画面形象较多、结构复杂的宏篇巨制,惯称大件作品;二是从形象到笔墨非常简练而意趣神情鲜明的即兴之作,一般称为小件或小品。相对大件作品而言,“小品”不求深沉、严肃,但求清新、活泼,即兴而作,笔简意深。但小品不小,它能透射和印证一个画家的功力、灵性和才气;而这灵性、才气又折射出画家相较于大幅作品更要着力把握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小品画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因画家个人的艺术思想、学习路径、兴趣爱好不同,创作方法也就各异:有人注重情思的宣泄,有人注重笔墨的挥洒,多则二三个形象,少则三五笔成形;即便如此,也非常讲究形式美感和艺术的完整性。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小品画,可以说它是介于速写、素描和创作之间的过渡和桥梁。画速写、素描是为了掌握造型的规律,小品画练习则主要是研究掌握笔墨的规律。它更注重整幅作品的意、雅、趣。
“意”的内涵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是比较宽泛而多义的。“意”除指画家的主观意志、情意、情思,画的意旨、意蕴外,还指神似、神韵;当然也指艺术表现上的含蓄和精练概括,更指作品的意境。中国画在追求“意”的表现上,是从对具体形象的表现发展为对作品画意的表现;随着主观描写的增加,从塑造形象和追求自然浑成,进而表现画家自己的思想、情意和主题内容的“写意”。但是无论是表现具体形象的神、意,或是为表达画家思想感情和画中主题的“写意”,其基本方面都是相同的,“以意写之,不在迹象”。“不在迹象”并非不要依据客观“迹象”,而是说,依据“迹象”,但不为“迹象”所牵,化客观迹象为主观迹象。表物象之“意”是画家在他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为了创造足以“达心”、“适意”的艺术形象,可以不受客观对象拘束;当他创造“达心”、“适意”的艺术想象并进而表现自然景色和社会事物时,不仅不受客观对象的拘束,而且既可以“运实入虚”创造“画内意”;又可以“运虚入实”创造“画外意”。
中国历代画家、文人也从画中“造意”,这和他们的绘画观、审美理想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绘画不仅仅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怀、追求个性发展;而是把绘画看做和诗文一样,也是直抒胸臆的一种形式。他们之所以重“意”,正是为了用以达其心、适其意。唐代王维的画,更带有较强的主观抒情的性质。“笔纵潜思,参于造化”。王维画中所潜之“思”,是通过诗意来体现的。同时,中国画的意境,不仅受道家和魏晋玄学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唐代佛学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当时的人们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在活泼泼的生命中,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去体验那无限的、永恒的、空寂的宇宙本体。这种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中国艺术家的形而上追求;表现在美学理论上,就结晶出“意境”这个范畴,意境的理解,形成了意境的理论,也让后人对意境有着无限的期待和理解与思考。
“雅”是相对于俗而言的。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意思是只有阅历才会带来人的气质变化,只有多读书才会给自己的作品带来书卷气,才会有作品格调的高雅。但阅历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其增加是累积性的。读书是人一生的修为,不可能一蹴而就。读书三五年而解决一辈子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有不少急功近利者。有人临几幅古画,学了一点笔墨技法,便急于拿出去卖钱;也有人听说水墨为上,彩色多了俗而不雅,乐得少花颜料钱,学洋人用水墨涂鸦,再写上几个字,就算万事大吉了。谁知人俗气了,无论用什么,画出来的画是不会自动脱俗的。技法失去了书卷气,技巧失去了文学气的依托,是不能免俗的。文人画于俗气势不两立。古人云,唯俗气不可沾染,一惹俗流,万劫不复。要想脱凡免俗,只有读书一径。多读书,自然就能免俗。
历代文人所称的“俗”,实际上是指绘画中取媚于人、装腔作势和附庸风雅的绘画作风。这些人的作画习惯是由于缺少“澄怀”而导致的。《石涛话语录·脱俗章》云:“愚者与俗同机,愚不蒙则智,俗不溅则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达,不能不明。达则变,明则化……天地山川万物而心淡若无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这里所说的俗最主要的不是大众化、普及化的下里巴人的俗,而是指画家心地不干净,人俗而导致的画格之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民间画以至院体画,只要画工做到了“心淡若无”,只求艺术的表现与情感的抒发,也一样会去愚而生智,去俗而至清的。齐白石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早年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匠人,但其好学,绘画取材也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象,又去除了杂虑,以优雅之心与超逸的笔墨赋之,到晚年以至于超于象外,达到了大师的境地。
人生活在俗的世界里,自然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这就是为什么绘画四品中逸品的可贵。大隐隐于闹市,大俗之中方有大雅。大俗大雅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模仿得来的,甚至也不是学来的,只能是悟出来的。白石老人所创红花墨叶派是大俗大雅的一个范例。这种方法可以学来,其效果可不一定就能大雅,还需要好诗好文好书法,甚至还需要一枚好印章才能有些许雅趣。不读书无意境,直如看图识字一般,那就只有大俗,没有大雅了。何况大俗大雅还不止红花墨叶派一条途径。
现在的人们身处市场经济当中,要大俗容易,要大雅又不愿下大工夫读书,要提高自己作品的艺术品位,实属不易。学一点画技,就想当做立身之宝,以此养家糊口,急于挣钱,就必须苦心钻营,揣摩买主的心理,投其所好,这样的作品要免俗也就难了。即使是名家要吃饭要养家,也会拿出来一些很俗的作品,其代表作却一定不是这种俗物。大半靠画画吃饭的人生活清苦,在所难免。因此,靠画画吃饭我认为不是一个好职业。
现代社会技术不值钱,艺术更不值钱,唯名气大什么都值钱了。社会的浮躁使人不惜重金去追逐名气。为了出名,为了出人头地,使艺人屈服于一切卑鄙的潜规则。媒体的炒作使一夜成名不再是神话。为了一夜成名,为了迎合潜规则的需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这种功利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氛围里,廉耻都没有了,高雅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地。廉价的逗乐搞笑大行其道,绘画作品不再需要高境界,不再需要文雅的书卷气。春宫既不需要高深的学问,画家在画纸上开起了窑子,自甘堕落当了王八;还要盗用水墨画的名号,摆起一副高雅的面孔,打出创新的旗帜,却没有什么文雅可言。可见笔墨技巧并没有多少雅俗之分。人雅画才会雅;人俗了,笔墨技巧再怎么纯熟,还是不免一俗的。
“趣”不等于“意”,它与意是紧密不可分的。一个形象,一幅画,缺少“趣”,就会影响“意”的创造和表现。因为“意”多是富有“趣”的。明代屠隆说:“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意”是构成神似、神韵的重要条件,“趣”又是表“意”所不可缺的。所以前人说:“写意画必有意,意必有趣,趣必有神。无趣无神则无意”,那更无意境可言。
“趣”在中国古典绘画中主要指什么呢?有人说“趣”是艺术的“形式美”。这样说总嫌有点笼统,而且不易说明“趣”在中国古典绘画中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表现是什么。“趣”如果作为一个单独的审美范畴,我很赞同意袁宏道的解释。他说“(对于趣)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其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并非袁氏故神其说,“趣”本来就不易言传。不过我们从“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和童子的“无往而非趣”,可知“趣”如果表现在画上,当是一种不加雕饰、毫无作意、朴素自然的“自然美”。这是符合中国艺术的审美要求的。中国古代画论强调“自然浑成”,有“天趣”、“物趣”之分。“天趣”就是指的这种质朴、自然的机趣,才有独特的意境。“趣”是构成“意”的条件,不是意的本身。而“意”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到之到”。清人查礼在他的《画梅题跋》中论画梅时说:“画梅不要像,像则失之刻。要不到,到则失之描。不像之像有神,不到之到有意。”中国画“不似而似”则似在“神”,“不到而到”则到在“意”,这就是艺术的高境界。
一个画家,不管你是追求盎然烂漫的生命之趣、灵动淋漓的笔情墨趣、凝彩如梦的清纯逸趣,还是追求空间疏朗、情意蕴蓄的诗味韵趣……凡有这些理趣、雅趣、纯真天趣的追求和表现,就成就了你画面某种生命力的支撑,从而透射出你对绘画的理解和表现所具有的那种于自身素养和审美情操上的求索。
画家应该把自己所思、所见、所闻的东西画出来,不要为展览而沉没于展览创作,为获奖而沉没于获奖追求。当年在法国沙龙,徐悲鸿获了奖,他的老师达昂对他说:我教学生不是为了获奖,我要学生做大事,要有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去迎合某种东西;迎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俗气。所谓高雅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小品画的笔墨不在层次丰富,而在于笔墨轻松活泼,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小品画也需要构思,从形象、构图到笔墨表现,不是信手涂鸦。大家所见到的顺手拈来,几笔挥洒,那只是画家创作表现时的得心应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似轻松,实则不易。所以画小品的取材范围相当广泛,一人、一头牛、某一生活情景,或一首小诗、一个动作,都可以成为小品画的表现题材。人物不求多,景物不求全;取材不求大,但求情趣生。只要是生活中某一感人的瞬间动态、表情,或者一抹朝霞、一轮秋月引起的情思,都可以进入小品画的创作天地。
作者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