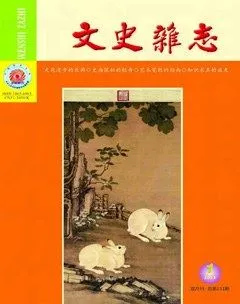谈谈先秦时期的三峡经济文化带
2011-12-29 00:00:00管墨
文史杂志 2011年1期


先秦时期的三峡地带,是当时中国的一大著名经济文化带。在长达一两千年的时间里,其出产的泉盐、丹砂及铜矿,成为邻近各个部落—部族—国家势力较智较力、争相角逐的重要生活资源乃至战略资源。
一、三峡地区的“世外桃源”
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云:
天有五气,是生五味。润下作咸,王访箕子而首闻其义焉。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四海之中,五服而外,为蔬为谷,皆有寂灭之乡,而斥卤则巧生以待。
宋应星刊刻《天工开物》时,已是明崇祯十年(1637)。其时食盐来源多样(如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崖盐、砂石盐、树叶盐等),产地可谓遍布神州大地,所以宋氏才会发出“而斥卤(指食盐)则巧生以待”的感慨。可是由此上溯至三四千年前,尤其是夏商周之世,食盐却堪比作今日的黄金珠宝,十分难得而弥足珍贵。仅就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来看,那时的食盐来源就只有泉盐一种。泉盐即地下盐岩层溶化于水,涌现于地面者。任乃强先生认为:
四川盆地原是侏罗纪内海,沉积有将近两万年的盐质,其上部的白垩纪岩层,亦还夹杂有部分含盐层(最上部地面岩层本也含有一定的食盐,由于多雨,被水流失)。川东地带的九处盐泉(包括地面盐泉与水下盐泉),也都只是侏罗纪岩盐层被地下水溶解,在复杂的褶曲地层内,有机会涌出地面来的。[1]
这九处盐泉分别是:奉节县长江南侧的白盐碛,云阳县的云安井,开县的温汤井,万县的长滩井,忠县的井、涂井,长宁县的安宁并以及巫溪县的宝源山,彭水县的郁山镇(以上九县,除长宁今属四川外,其余今均属重庆)。前七处盐泉,“都是从地面淡水河底涌出来的。最初是盐水与淡水混合流行,不为人类所觉,所以发现得很晚。它们的被发现是巴民族开始的”[2],时间大致是在殷末至周初。而三峡地区发现得最早的盐泉则是巫溪县的宝源山和彭水县的郁山镇两处。它们都是从山麓陆地涌出的。这大约也是人类发现得最早的盐泉,“因而由它所形成的文化核心也最早”。[3]它们的被发现与开发的时间大致是在虞夏时期。这一时期,还在瞿塘峡—巫峡以南的今鄂西恩施市东的盐阳发现了盐泉。它们连同今湖北秭归丹阳与重庆铜梁山—铜罐驿,均以长江为通道,由东向西,形成一条以泉盐为主要特色,兼及丹砂和铜矿的三峡经济文化带。
巫溪即今大宁河,它从渝、陕、鄂交界处的大巴山发源,经今巫溪、巫山两县,蜿蜒200余里,南入长江。大江由巫溪口上溯100里至瞿塘峡口,有源自奉节县的大溪河入江。这大溪口(即瞿塘峡东口)与巫溪口(即巫峡西口)之间的百里地带,河谷开阔,依江傍山,多耕地。它们与巫溪河谷、大溪河谷相连,构成一块小盆地——任乃强考为《山海经》里的“巫臷之国”。[4]
长期以来,在不少学者眼里,都将《山海经》看成是南方长江中上游流域的上古神话作品,甚至竟直指为巴蜀文化系统的神话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是蒙文通先生的认识。他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以巴、蜀、荆、楚地区为“天下之中”的,其《海内经》和《大荒经》则是以今日的四川西部地区为“天下之中”。在此基础上,蒙先生提出《海内经》可能系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可能系巴国作品,《五藏山经》可能系接受巴蜀文化以后的荆楚地区作品。[5]现在,我们来看看被认为是巴国(确切地说,当为巫巴山地)作品的《大荒经》是如何记载巫臷之国的:
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肦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郭璞注:“言自然有布帛也”);不稼不穑,食也(郭璞注:“言五谷自生也;种之为稼,收之为穑”)。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更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任乃强言:“丰沮,显然指的盐泉”)。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袁珂按:“灵山,疑即巫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大荒西经》
按《山海经》的描述,这个虞夏之际形成的巫峡—巫山地段的巫臷国(应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极乐世界了。请看,这里的人们不耕不织,不狩不猎,却衣食丰足,成天生活在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环境中。巫咸、巫彭等十巫神仙于此采集长生不老之药,于此下凡上天……
据任乃强考,《山海经)里的这段关于盐泉的描述,大约指的就是今巫山山系中巫溪县的宝源山麓的盐泉。这里的原始居民,“有了宝源山这眼盐泉,便转为原始社会的极乐世界,地方繁荣,民族强盛,形成长江中游川、楚之间文化突出的巫臷之国了。”[6]
浏览巫溪县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巫溪流域有不少以“白鹿”命名的地方。原来这里很早就流传着一个白鹿舐盐的美丽传说,说是宝源山麓的盐泉本不为人知。有一天,有一部落民在山中追赶一白鹿至此,发现白鹿却突然停止了逃命,如饥似渴地狂舐一泉水渍地。这人趁机捕杀了白鹿,也尝试着去捧饮白鹿依恋之水,竟咸而回甘,顿长精神。于是便呼引族人就此聚居,与盐泉相伴相生。以后他们又开始伐木煮煎泉水,用所得晶盐向四方居民进行贸易交往,得以富庶强大,形成以盐立国的巫臷国。
巫臷国里的大溪沟(大溪河)的“大”字,当地人读作“黛”,与“臷”同音。在巫臷国民族形成时期,这里是巫臷部落的核心地带,“大溪”应是“臷溪”之讹。[7]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发现大量鱼骨。对此,任乃强在《四川上古史新探》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第一,这表明这里有大量的巫臷部落民聚合,且有用鱼殉葬的习俗。第二,鱼是易腐之物,为了保鲜,非用盐腌制不可;大量鱼骨,说明殉葬时使用了大量食盐。在当时四川地域,这只有盛产泉盐的大溪—巫溪一带居民甚至是居民中有地位者才可能办到。所以,大溪—巫溪地区乃巫臷文化的核心地区,大溪沟是臷溪沟的音变。
任乃强还根据著名的“巫山神女”神话以及《山海经·海内经》里“太昊(皞)生咸鸟”的记载,提出巫臷族乃羌族东徙的一个支族。[8]其形成时期同巫盐的发现与外销时期相当,初时的地域仅限于大溪—巫溪河谷。这个时期与中原的黄帝部落的形成时期相一致,亦在5000年前。后来巫盐通过夔峡畅销于四川盆地,通过巫峡畅销于云梦盆地以及汉水流域和黔中高原等广阔地区,推动着长江中上游沿江诸部落、诸部族、诸古国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而在这个推动过程中,巫臷族自己也相应进入其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在殷末至周初的600年间。[9]巫臷部落—巫臷国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开始形成,至春秋中叶衰落消失,约莫存在了二千七八百年之久。
二、巫山与郁山的丹砂
巫臷国不但产盐,而且亦产丹砂。丹砂即朱砂,属于辉闪矿类,主要成份是硫化汞HgS。它生在石灰岩中,成块形、柱形、板形、马牙形、箭头形。最好的天然丹砂表面光滑如镜,后人称之为镜面砂。丹砂色朱红,是炼汞(水银)的主要原料,也可制作颜料。《天工开物·丹青》有载。早在旧石器时代,居住于今中国中西部的原始人就开始用它来作装饰性颜料和涂料。以后,人们又发现了它的医学价值,以为其内服可以镇心养神,益气明目,通血脉,止烦懑,驱精魅邪思,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症,也可用于外治,故而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托名神农氏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当在战国或秦汉之际)称丹砂为药之上品。当然,那时人们对它的那诸多疗效尚无法做出科学解释,因而认定它为长生不死甚或起死回生的仙药。所以《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即拒死复生)。”郭璞注云:巫彭等“皆神医也。《世本》曰:‘巫彭作医。’”袁珂亦按曰:(前引)《大荒西经》中“十巫与此六巫名皆相近,而彼有‘百药爰在’,此有‘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语,巫咸、巫彭又为传说中医道创始者”。
这救活窫窳的不死神药就是丹砂。它出产在灵山即巫山。而巫山因出产神药丹砂又被《路史·后纪十三》之注言为丹山。在早,《山海经·大荒南经》即有云:“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郭璞注曰:“天帝神仙药在此也。”袁珂按曰:黄鸟即皇乌,专守于巫山以防玄蛇“窃食天帝神药也”。任乃强根据前引《山海经·大荒西经》里关于巫咸、巫即、巫肦等十巫去灵山(巫山)采药的记载,推想巫肦就是到巫山采药,从而改进巫泉煮盐和开采丹山朱砂的祖师。[10]不过,这神奇的丹砂在夏虞之时的秦岭与王屋山可能就已被发现和应用,所以《尚书》里帝尧的长子被称做丹朱。只是上述二地的丹砂大致不易开采,且采之易尽,很是供不应求。在这种背景下,大约在殷周之际,巫山的盐工们又可能在采制食盐之余发现了丹砂,于是外地的丹工闻讯而纷至沓来开采,使得巫山之丹砂名声大噪,几同于泉盐。
由此看来,殷周之际的巫臷国因为出产与当时人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泉盐和丹砂而引起世人瞩目。所以,泉盐和丹砂便成为巫臷国国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特别是泉盐),成为三峡—巫臷文化的主要物质元素。
处于三峡—巫臷文化带上的今彭水县郁山地区也盛产泉盐和丹砂。这一地区的大江主要为郁江和乌江,郁江为乌江支流。郁江上游的郁山镇所在的伏牛山区,古有盐泉自山麓涌出,成为三峡—巫臷文化带甚至于三峡经济文化带内的第二大泉盐出产地。
郁山地区的丹砂也很有名。直至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时,还记秦始皇时期这一地区有一位名叫“清”的寡妇,因为“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这里的丹砂,亦同食盐一样,藉郁江—乌江—长江航道而行销峡外各地及成都平原。大致又因为郁山的丹砂相对来说,比食盐出口多(因为其食盐主要用以供应后来被楚、秦相继吞并而称做“黔中”的广大地面),所以由郁山入郁江、乌江,经枳(今涪陵)入长江之前的这段水道,后来便被称做“丹涪水”。《华阳国志·巴志》有云:“从枳南入丹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另外,根据《逸周书·王会》“卜人(即濮人)以丹砂入贡”及《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的记载,被称为濮人的郁山—黔中的土著居民大致早在商周之际就已与中原交通,所以被列于《王会》。而《尚书·牧誓》中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濮”,也当是郁山—黔中濮人。其时由于他们拥有丰富的盐泉和丹砂而强大起来,并跻身于“牧誓八国”之中而参与周武王伐纣的义举,使得中原华人亦不得不刮目相看。
三、盐水女神和巫盐南下
处于三峡南边的恩施盐阳(夷城),有著名的盐水(建始河)由北而南注入清江(即古夷水)。其盐水女神的传说使人扼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荆州图副》云:
夷陵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元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县西一独山有石穴,有二大石并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为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
夷陵县在今恩施市一带,亦即前引《后汉书》中所称的盐阳或夷城。李贤引注《世本》原文,称冷峻的廪君在袭杀盐水女神时,曾“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汝俱生,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明”。这里的“阳石”,与前引《荆州图副》相合,表明廪君斩断情丝(即“青缕”)、射杀盐水女神之处在盐水之滨、巫山之阳(南)、夷陵县西的温泉(实为盐泉)附近。故此处的盐泉即有盐阳之称。据张希周先生介绍,这里的“盐池温泉”,在当地又有“盐水”、“盐池河”、“盐井寺”、“咸池河”等多种称呼,符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此地广大,鱼盐所出”的特点。其盐水水温常年保持在摄氏42度,含盐比重高,一直产盐。冬季来临,盐气升腾,附近群众常年在此沐浴,颇健肌肤。[11]
恩施盐阳也处于三峡经济文化带上。据任乃强考,溯盐水翻越七曜山,经巫山县大庙坝、大溪沟,沿长江至今巫山县城,有条大道,乃古代巫盐南下恩施盆地的“盐道”。《后汉书》等古籍关于“盐水有女神”的记载,系用宋玉《高唐赋》的写法。以“巫山神女”来比喻食盐的魔力,表示巫山地区的盐商招诱廪君,劝他也依附巫山,吃巫盐。“盐神暮辄来取宿”,亦是《高唐赋》神女自荐枕席的手法,表示巫盐主动地运销入恩施地区。[12]当然,盐阳盐水女神的传说,不应仅止于上述寓意。倘联系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此地广大,鱼盐所出”的记载,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出,在殷周之际,恩施盐泉与郁山盐泉同巫臷盐泉一样,应是三峡—巫臷文化区内鼎足而立的三大产盐地。当然,恩施盐泉与郁山盐泉的发现与开发可能晚于巫臷盐泉。就三大产盐地而言,巫臷盐泉无疑处于主导地位。巫臷盐商和盐工们很可能在沿着任乃强考出的那条“盐道”南下贩盐间隙,发现了盐阳盐泉并帮助当地居民开发之。此外,恩施盆地又可通过若干河谷(如忠建河谷、唐岩河谷、郁江河谷)与郁江盆地相连。这样来看,郁江很有气势的食盐、丹砂的开发与出口,亦当是郁江居民通过恩施盆地为中介向巫臷居民学来的,或者是巫臷人前去手把手地教导出来的。
大致在巴人于三峡地区立国并发现南、北集渠的水下盐泉(即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长滩井盐泉和云阳彭溪的朐忍盐泉)等七处盐泉(时间约在殷末周初之际)之前的长时期内,整个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的食盐供应都仰仗于三峡—巫臷文化带。这之中,由于巫臷国的泉盐产量最大,且最靠近大江,得舟楫之便最多,因而向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供给食盐最力——向西于峡内径达成都平原,向东于峡外直抵云梦盆地(两湖平原)。不仅如此,巫臷国的食盐还通过巫溪上游的若干支流河谷而翻越大巴山,供应汉中、安康和房山、竹山这些汉水支流上的各个河谷盆地。
注释:
[1][2][3][6][7][8][9][10][12]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221页,221页,227页,228页,235页,231、232页,251页,270页。
[4]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223—232页。在该书第226页,任乃强还释“巫臷”之“臷”说:“臷字,以至为声,实即原始的铁字。铁、台、垤、绖,都是以至为声的字,皆与黛字声近。《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世本》把巫臷写作‘巫诞’,足见臷字与黛字相近,是可以肯定的。今川楚间人,与往来长江的舟人,都把瞿塘峡口的大溪沟,读如‘黛溪沟’。那里近年发现新石器、中石器以至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甚多。可以设想,那就是古所谓巫臷民族的遗址,它可以代表上古的巫臷文化。”
[5]参见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张希周:《试论古代巴人发源于湖北长阳佷山》,《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