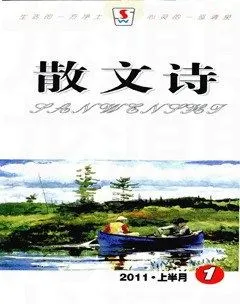名理前的视境
2011-12-29 00:00:00龙彼德
散文诗 2011年1期
“名理前的视境”,是叶维廉从中国古诗提炼出来的一种艺术,不仅用在他的现代诗里,也用在他为数有限的散文诗里。
所谓“名理前的视境”,按他本人的话说,是“在水银灯的照射下,景物自然发生与演出,作者毫不介入”。也就是说让万物本相自然罗列,而不加以“名”的识别、“理”的分析,以达到无言独化、不落言诠的境界。
请看他于1973年7月过香港所作《香港素捕》的第三首。维吉尔(公元前70一前19)是古罗马诗人,但丁(1265—1321)是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他俩结伴同游香港,做了作者超现实的借代一维吉尔胸有成竹,“也不说什么,就领着但丁进去”,尽管“我不入,谁人!”使人联想到佛家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在这里并没有佛教的概念和色彩。呈现在但丁眼前的,是高耸的墓石(指高楼大厦),陷落于墓石间深坑的人群,虽有“无路可走的郁结”却不自知,他们一味地欢乐、追逐、穷吃(“兽类的五脏”牵涉到环保),使但丁赐爱与光的愿望落空。作者不作解说,只是呈现,让物象自主演出,而读者白明:物质社会对人性的挫伤,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扰,回归自然、崇尚精神的必要……都在维吉尔的歌唱与但丁的悲悯中了。
叶维廉在《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中写道:“这种诗抓住现象一瞬间的显现(epiphany),而其对现象的观察,由于是用了鸟瞰式的类似水银灯投射的方式,其结果往往是一种静态的均衡。”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对此作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