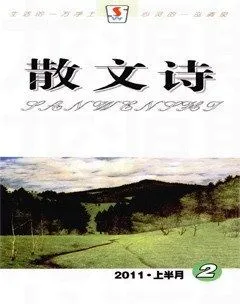《伊犁短章》及其他
一切
来不及惊叹的瞬间,天山便已猛然扑面而来!水墨一样的雄浑与苍老的浮云铺天盖地,成为舷窗外的一切!
一切!让你只可噤声或膜拜;
一切!让你只会听见灵魂在躯体里瑟瑟地抖颤与惊悚。
银色飞机迷失一样地盘旋,仿若不能逾越这一切的博大。小如一片雪。一片雪在天山的肩头晶莹、轻盈地飞过。而白发天山,沉静犹似一位身披麻衣的智者,沉都不动,闭目冥想,昏昏然早已阅尽世间之一切。
它连一棵可做佩饰的树都不需要,因为它已是一切;
它连一只可供消遣的鸟都不需要,因为它已是一切!
大天山
尽管我是透过飞机的舷窗向下望你,但你还是在高处!这一刻,不得不让我重新思考世间“仰望”这个词的意义。
仰望——不是从低处向上望吗?不是渺小者望伟大者的姿势吗?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抬头仰望,甚至被强迫着,将高贵的头望向卑鄙或强权,望向腐烂或无耻!
而你巍巍然静立在那里,允许我们低着头指指点点地仰望你,允许我们坐在飞机上一路轰鸣着打扰正在思索的你。
这就是世间的大!大到极致,才可以包容所有的小,所有的无知,所有的误解和苦难!
天马
青铜天马扬起前蹄的一刻,我忽然有见了辽阔的天空。
青铜天马的长鬃被风旋起。它要挣断身上的羁绊,去寻找自由的天上草原了。
它不属于怯懦的骑手。
更不属于喑哑的皮鞭。
它胸怀的大志。只有天空知道。
但此刻,它却要被一双双油腻的手来抚摸,被不懂得自由和天空的人用照相机的闪光灯晃它高贵的眼睛!
青铜天马的眼神里已经有了厌倦和忧伤,已经有了鄙视和惆怅!
天空上种满了樊篱,自由,究竟在谁的手上?
青铜天马扬起前蹄的一刻,我忽然看见,它又轻轻地放下。
只有它的目光穿透屋顶;只有它的头颅,昂得高高——高过周围无形的铁墙。
杯子寻找水
将松散的土,一粒粒粘合在一起然后,一双灵巧的手,将它捏成一只杯
软软的杯,红红地赤裸着新生的陶土婴儿一
还是那双手,轻轻地,轻轻地把它放进黑黑的窑里,点燃火。
熊熊的火焰,顷刻间开始起舞——火,化成无数双陌生而炽热的手,疯狂地驱赶陶泥里不知所措的水。
水,纷纷离去
水的离去并非逃跑,而是为了那个陶土婴儿可以站立,哪怕,就站成一只杯子!
后来,它成了一只真正的杯子
坚硬,脆弱
它开始不停地去寻找水它渴!被火烧灼得太久。它要喝掉天下所有的水!
还有,它要找到最初的水,找到把它粘合成形,给了它骨与血,给了它名字的水,在起焰熊熊的窑里和它告别过的水!
但已经无法找到了。
绝望的杯子,从高处跌落在地一世界都听到了那一声悲伤的碎裂。
尸体的碎片,被拥有它的人遗憾地扫进垃圾筒里。知己的骨肉相碰,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一没有血。
静夜里的声响,如同寻根问祖的哭泣!
擦肩而过
楼道里没有灯只听到走过去的声音,我蹒跚而下,你轻盈而上。
你不会是一只鸟吧?
探索着打开楼门,站在月光下,看自己站不起来的影子我已经很苍老了是不是(不知你住楼上哪一间房子,从前我们是否见过)?
楼道里还是没有灯,只听见你擦肩而过的声音,我喘息而上,你快乐而下。
找到不会有人抚摸的门牌,锁孔早已锈迹斑斑了。空荡荡的屋中央,兀立良久,喊一声,墙壁撞不出回声,只有缕缕灰尘自岁月的额际飘落
从此不再出门。
会有人按响门旁的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