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晴雨表”更精准
2011-12-29 00:00:00李而亮
中华儿女 2011年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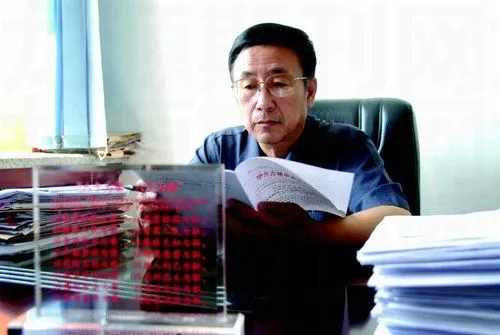




今年1月24日,农历大寒刚过,京城洒水成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国家信访局,与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这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共和国总理第一次与来京访民当面交流,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群众疾苦的入微体贴和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
信访工作,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制度,并非中国独有。可是,像中国上访民众数量之大,上访内容涉及之广,接待上访机构之全,从事此工作专职干部数量之多,却毫无疑问为世界之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很形象地描绘信访工作的重要功能。他说:“信访”这两个字很有特点,“信”字由“人”和“言”组成,“访”字是“言”字加“方”。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设立信访局,就是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讲话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能反映执政党执政特色的部门。
因此,有人将信访工作好坏视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
提起群众的上访现象,没有人会不知道;而要说到信访部门和众多的信访干部的工作性质、工作状态,他们在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搭建起什么样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在化解访民冤屈与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也许,从媒体广泛宣传吴天祥、张云泉等英模人物事迹中,我们感受到了信访干部的崇高精神和对群众的深厚感情;也许,从更多访民的呼喊中,我们又了解到百姓求“青天”的渴望,听到过他们连年累月、风餐露宿,而又求告无果失望备至的故事。全国35万信访干部,他们在群众寻找“包青天”的渴望中到底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面对访民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诉求,如何替他们排忧解难,为党和政府化解矛盾?
本期专题,我们专程采访了几个不同层面的信访干部,听听他们的心声。
信访告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备受欺压凌辱的百姓,总期待自己的冤情能为明君好官所知道,御笔一挥,官威一震,扬善惩恶,拨云见日。于是,拦路上书、击鼓鸣冤,成了拼死一搏的常见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信访工作。早在1951年6月,政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对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信访机构的设置及性质、信访原则和相关工作制度等作了详细规定。1957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信访工作会议,起草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草案)》,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自此以后,由于政治运动接连,直至“文革”10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处于不正常状态,信访工作大大削弱了。
打倒“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掀起了信访的高潮。不仅各级党委政府、公检法机关要专设信访部门,连新闻媒体也承担起繁重的信访任务。更由于许多冤情、错案是通过领导批示、过问才得以解决,又进一步助长了群众对寻找清官“断案”的习惯性路径选择。为保持党和政府与群众申诉联系的窗口,使得信访工作和大批信访干部走向专职化、专业化,建立起与法治化建设并行的中国特色信访体制。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法制建设日臻完善,民众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社会进步越来越快的形势下,信访工作与信访干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一方面,是群众自身权益维护的诉求增多,一方面是信访部门涉及司法的权力无法僭越;一方面是群众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在激化,一方面是群众反映的问题还得依赖政府来解决;一方面是大规模群体上访呈上升态势,一方面是党委政府对维稳“一票否决”施加的压力……重重矛盾,层层限定,令信访工作逐步陷入一种被动尴尬的处境。他们既要接访,又要截访;既要同情,又要劝阻;既要合理引导,又要严防死守。信访部门,成为党委政府机构序列中被认为最无权力和实惠的部门;信访岗位,被认为是最苦最累的工作。
无权无利,再苦再累,在现阶段里,信访部门依然是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弱势群体对话交流最直接的窗口;信访干部依然是接受群众申诉、感知群众疾苦最直接的人。尽管形势变化,社会发展,但总还需要这样一批干部坚守在信访的岗位上。在现实中,也确实有这样一批干部,他们不管多么清贫和苦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对人民群众朴素的感情和感人肺腑的人格魅力,破解一道道难题,化解一个个矛盾,担负起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神圣使命,维护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他们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更加精准,倾洒了自己的满腔热血。
本期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点滴故事。
责任编辑 张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