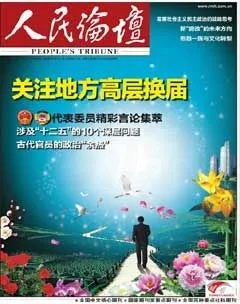从“革命的”到“中国的”:路有多远?
为什么说当今法律体系是“革命的”
当今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革命的”法律体系,是在革命后的政治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法律体系。第一,这一法律体系的建立基础,是通过推翻旧政权的暴力革命途径获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领导的政权(而国民党政权也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的)。在“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情形下建立的法律体系,与旧政权体制内延续情形下建立的法律体系是有根本不同的。第二,这一法律体系是以彻底废除“旧法统”确立新法统的方式建立起来的。1949年新中国宣布废除“伪法统”,废除“六法全书”体系并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就是这一新法律体系的起点。所谓“法统”,就是法律制度“正朔”(正统性、合法性)传承脉系。我们宣布彻底斩断自辛亥革命开始逐渐建立的一个自称上承尧舜禹下效欧美日的“法统”,而宣布“一边倒”地绍传(续接)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形成的一个域外苏维埃新法统,这才有了今日中国法律体系。第三,这一法律体系的内容,无论是精神原则,还是具体规范,都贯穿了彻底革命(直至灵魂革命)以“脱胎换骨”改造中国的理想。这里的革命,近指对康梁孙黄以来的“旧民主主义”路线的革命,远指对儒家纲常仁政思想为灵魂的“中华法系”的革命。
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中国法律体系。如果说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那主要是从“革命”意义上讲的,但不一定是从“中国”的意义上讲的。
从“革命”的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是今日才形成的。可以说,自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始建之日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法律体系就开始形成或已经形成。1931-1935年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司法程序》、《裁判条例》等一系列部门法典或单行法规,还有以党的政策纲领指示等形式发布的一系列关于行政、司法、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宜的国家强制性规范,贯穿了工农革命或社会主义精神,其内容互相配套,其内在逻辑关系或逻辑体系也十分清楚,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尽管不完善)。从那时到今天,这一法律体系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从粗到精、从初级到科学。
要制定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也许不一定是最难的事。真正最难的,是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之后再建成一个“中国的”、“民族的”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为何要“中国化”
中国法律体系当然不能从精神上“非中国化”,在保存弘扬民族文化精粹的前提下应当仍然可以实现法制革命。但是,要以实际的法制建设行动回答这两个问题,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最艰巨的历史任务。
呼吁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国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法制建设必须尽量诚实地面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不回避,不矫饰。新中国几十年来,我们发现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那就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紧迫的问题,往往可能是法律管不着的问题。比如当今中国人们最头疼的刚性维稳责任及超高维稳成本问题、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争议问题、司法判决难以执行的问题……都是没有正式法律规定或在立法上仅有原则规定无法实际操作以解决的问题。在上位一些人的一般心理是:宁可凭借灵活机动的政策因时制宜地解决这些问题,以掌握主动权。若制定正式公布可供人们据以随时对照“争权夺利”的一般法律规范,则会造成官方的被动。在上位的这种心理,导致了在下位的人们对法律体系的不信任。
只有诚实针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紧迫问题尽快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哪怕是暂时不完善的法律规范),诚实针对这些现实问题用足法定权威和法定救济程序,那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中国的、本土的法律体系。
第二,法制建设方案必须尽量尊重中国的国情现状,正视国情所造成的限制。针对上述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紧迫问题的法制解决方案,当然应该尊重或照顾到中国的现实国情,不能脱离国情。具体地说,立法方案必须特别因应中国人口众多而平均教育程度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大、国家财力强而民众财力相对弱、中央集权体制惯性较大、市场化程度低、社会自治程度较低等等国情。我们的未来法制建设,一方面要正视国情造成的客观限制,不幻想通过立法“人定胜天”地快速改变国情;但同时也要通过理性的立法诱导某些国情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渐进变化,如:限制人口发展、提高教育程度、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地方权力、扩大社会自治、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之类。这样尊重国情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形成真正“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