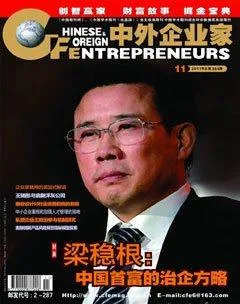西部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激励机制构建
2011-12-29 00:00:00王保林郭凌峰
中外企业家 2011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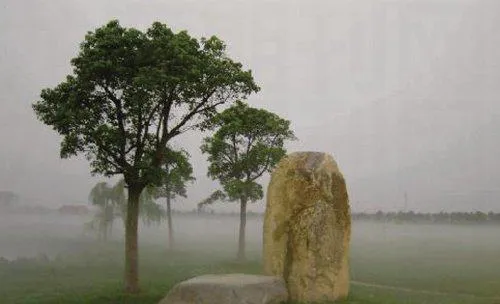

通过分析西部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过程中面临的矛盾,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指出,市场化进程中解决生态破坏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益激励兼容基础之上的制度,并从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出发,构建了有利于西部生态建设的激励机制。
一、导言
中国部分地区自然资源的退化与农村人口的贫困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源退化导致贫困,贫困又加剧对资源的掠夺,这种恶性循环日趋严重。在中国目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保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走脱贫与自然保护相结合的路子,对于保护区以及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中央的意图,西部省区明确了西部开发的主攻方向: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保护、结构调整、科教与人才培养。其中生态建设和保护则指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荒山绿化、防风固沙等。
从狭义来讲,开发是指“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力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之目的”。事实上,美国历时百年的西部开发,正是旨在充分利用西部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资源和落基山脉丰富的矿藏资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我们能否据此也强调自然资源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呢?显然不能。然而,不少人至今仍陶醉在以下数据之中:约占国土面积57%的西部地区只有占全国23%的人口居住,还有8亿亩土地尚待开发利用;西部拥有160种矿产资源,其中钛、铜、汞、铅、锌、钾等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并储存较为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似乎只要将铁路、公路修通并将东部人口迁移到那里,便会带来无尽的财富。殊不知,在这片广袤的西部大地上,巍峨耸立着生存条件极为严酷的青藏高原,横卧着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腾格里等大沙漠和风吹石走的茫茫戈壁。毫不夸张地讲,这仅占全国23%的人口已经充斥在近乎所有可供人类生存的地方。相反,倒是人口的过于拥挤(相对于给定的自然资源)与土地的过度开垦,已使塔里木河下游干涸、大片胡杨枯死,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荒漠化程度日益严重。所以,对于西部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与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而言,与其说要实施开发,毋宁说要加以保护和修复显得更为贴切!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解决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如何运用行政、技术、法律、经济等手段去遏制,其基本的特色是“堵截”。笔者认为,市场化是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成果与生态环保并非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而我们应另辟蹊径,通过理论分析来揭示西部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和机理,进而探索促进两者良性互动的对策体系。其基本的考量是建立在利益激励兼容基础之上的“疏导”。笔者认为,欲使中国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中国西部农户投入生态环保的积极性可持续。没有第二个“可持续”就难以有第一个“可持续”。而这第二个“可持续”一旦实现,则实现第一个“可持续”的成本(包括有形的可计量的成本和无形的难以计量的成本)将是较低的,将是“经济”的。
二、西部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面临的挑战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退耕还林(草)、荒山绿化、封山育林等,不失为针对性较强的生态建设和保护策略与措施,这些措施对于改善整个西部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措施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却面临挑战。
由于禁止砍伐天然林、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森工企业纷纷转产或破产。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农民收入下降、农户生产生活困难,以森工企业为支柱的整个西部林区的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以四川省为例,2006年实行天然林禁伐,使四川省的木材相关产业财政收入减少7.4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19%。四川省甘孜州农民纯收入减少13%,人均减少200元。马边县因此有6.8万人失去就业机会,减少收入1亿元。另一方面,四川省80%的农户是以木材为燃料的,对林木的保护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这类问题导致的结果是,西部生态建设与地方农民的利益产生矛盾,农民为解决自身生计问题,便会选择诸如乱砍滥伐林木,违法开荒、放牧,非法采矿等对当地资源环境产生强大压力的行为,仅靠行政性禁止也未必能有效制止。这使得上述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究竟能否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持久的效力,成为一个变数。
另外,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决策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地方政府的直接参与和运作下,增加了环境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的可能性,出现“政府失灵”。在美国,除《宅地法》、《育林法》、《荒地法》等旨在实现“公地出售”和鼓励私人植树、兴修沟渠的法律由国会颁布之外,土地耕作、矿产开发等均由私人或民间实施,甚至铁路的修建也靠公司来完成。而我国却恰好相反,国家规定,每退耕还林一亩,补贴粮食300斤,连续7年,这本是一个正确的办法。但是,如何补却大有文章。现在的作法是,完全由政府操作,即国家把粮食调往退耕还林的地区,各级政府官员由下逐级上报退耕还林情况,由上逐级下拨补助粮食。于是,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了大量基层官员与农民合谋欺骗上级的事情:退耕还林的补助拿了,地照样在种,甚至还有某地“超额”完成了数十万亩的退耕还林任务,殊不知每退耕还林一亩地可得150公斤粮食,而每公斤粮食折算为1.4元钱,只要能从中央财政的口袋里掏出钱来,多搞些“空饷”也足以让地方新建的办事机构买车买房了。上述例证是要表明,在特定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受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驱使,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目标的实现,这已被有关“计划失灵”的理论所阐明。市场化是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成果与生态环保并非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此,西部开发中生态建设最终取决于采取计划手段抑或运用市场机制,取决于采取排斥性政策还是参与式政策,取决于能否变单纯的政府行为为政府支持和引导下的民间行为。
三、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激励机制构建
经济主体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经过成本—收益比较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一种制度的施行,只有能够改变经济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比较才能发挥作用。因此,生态效应所具有的公益性和外部性,需要对具有正面环境效应的行为予以相应的补贴,由此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
比如,由民间成立一个组织,政府通过拍卖特许权或财政贴息贷款方式,把用于退耕还林的粮食放贷给这样的民间机构,由民间机构与农民签订退耕还林的商业合约进行实施。这样,就建立了与政府行政操作完全不同的制度框架。农民面对的是商业机构,不是基层官员,商业信誉会对其形成约束,不会再去欺骗对方,否则就会受到违约制裁,受到乡土社会的舆论谴责和道德制约,政府对民间机构的监督也易于进行和较有保障。首先,改变评估的标准,从退耕面积变成林木成活的面积。其次,对于守法经营和确有成绩的,政府可以免其利息甚至可以少回收或不回收本金,以资鼓励。对于违法经营和不退耕还林的,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进而给予制裁。第三,对于违约的农户政府也有办法处理。这样,退耕还林的一整套商业经营模式就会逐步形成。政府从退耕还林中会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民间组织也会在经营中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农村中一个重要的市场主体和重要的经济力量,农村的市场制度也就会建立和发展起来,政府行为也会规范化。与此同时,依托于民间组织,可以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林木市场,使得林业的经营真正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将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实现环境保护与消除贫困的良性互动。
再从产权的界定与保护角度来看,在经营的自主权与自利的合理性被认同以后,土地、山岭、草场等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产权的界定与转让等)并未与之相配套、相适应。当一群利己的人要共同利用某种稀缺的公共资源时,这种资源终将被耗尽,这一机理已近乎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常识。试问,当看到邻居家的山羊在集体拥有的山坡上啃吃草根与树苗而未被施以严厉的处罚时,这家农民怎能安然将自家的羊只圈在院内而不加效仿呢?植被破坏与草场退化的症结正在于此。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产权制度作保障,无论退耕还林还是修复牧场,其效果极有可能是短暂的,除非在高成本条件下施加某种强迫和管制。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导出,稀缺资源最优配置与利用的先决条件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宁夏南部山区私有水窖的长期合理存在便是一项有力的例证。所以,面对西部大片的荒漠化土地,通过立法确立和保护事实上的私有产权安排,并非不可考虑。
(内蒙古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