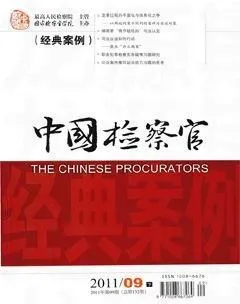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审查判断
本案张某故意伤害犯罪事实清楚。但在该案审查中出现张某年龄如何认定的问题,张某户籍证明记载其出生于1991年6月2日,张某一直称自己出生于1991年6月2日为农历日期。对应公历为7月13日,如按张某本人供述出生日期为农历,其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如何认定张某的年龄成为本案的焦点。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年龄证据的审查判断不仅要依据正确的司法理念。还要运用证据判断规则科学理性分析,从而得出公正的处理结果。证据的审查、判断就是指司法人员对于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找出它们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找出证据材料的证据力和证明力。从而对案件事实做出正确认定的一种活动。下面结合本案分三种情形对未成年犯年龄问题的认定进行分析。
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年龄提出异议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人对于自己的出生日期提出异议的情形,在审查判断未成年人的年龄时应当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甄别。
(一)未成年犯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提出户籍记载年龄有误
在公安干警对其讯问之初就提出出生日期与户籍记载存在出入的,如果此时没有律师介入,外界因素不足以影响未成年犯口供时,其提出户籍上的年龄与实际年龄存在差错的情况下。应及时向未成年犯的监护人进行核实,调查未成年犯就读小学、中学学校的学籍档案资料,调查相关证人证言,如果上述事实能够得以互相印证,应当采信未成年犯本人所述出生日期,如本案张某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一直称自己出生于1991年6月2日为农历日期,经调查其在广东打东的母亲,也证实张某出生日期为1991年农历六月初二,另外本案有相关证人证实张涛出生日期为农历。当地村委会也出具证明,证实当地农村一直有按农历纪年、孩子户口也按农历上报的习俗。且本案在诉讼各阶段无律师介入,因此应当采信未成年犯供述的出生日期。
(二)未成年犯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审判阶段提出户籍记载的年龄有误
此种情形要发挥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予以甄别和判断,首先要查清未成年犯在公安机关侦查时有没有提出自己的年龄问题与户籍记载不一致的说法,是未成年犯已经提出侦查机关没有理会、及时记录还是其本人根本没有提出。如果是属于公安机关没有及时记录的情形,需通过其他证据进一步判断未成年犯供述真实性、客观性。如果其他证据能够得以印证。应以查实的出生日期来认定未成年犯的年龄。如果未成年犯在侦查机关根本没有提出年龄问题,而后又提出的,需查明此时是否存在外界因素的影响,如律师介入、父母会见、同监室人员教唆等情况,对于此种情况如无充分、合理理由及确实充分证据一般不宜采信犯罪嫌疑人的说法。应当以户籍证明记载日期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对年龄提出异议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对于未成年犯的户籍记载出生日期产生异议。因未成年犯监护人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证言的双重矛盾属性,一是直接性,监护人大多是未成年犯的父母,其对未成年犯的出生日期应是最为清楚的关键证人。二是倾向性,未成年犯的监护人又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监护人对未成年犯年龄产生异议。其根本目的即是要减轻或免除未成年犯的刑事责任。这必然导致其证言可能影响其证明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其证明效力较其他证据要低。基于未成年犯监护人证言特点。不能以此证言单独定案。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一)要结合书证来认定
此种情形下书证效力是判断证人证言真伪的有利武器。如有的未成年犯父母提供结婚证。想以此证实未成年犯的出生日期填报有误,不可能未成年犯出生日期早于结婚证登记日期,但此时要查清是否存在先结婚办仪式后领取结婚证的情形。其次,要调查有无医院的出生证明。再次,要搜集当地人口普查统计表、计生办育龄妇女表及学校入学时登记年龄信息资料。如果仅因户籍登记错误。其他原始书证会在不同场合体现正确的信息,如果相关资料能够体现并能印证未成年犯监护人说法,一定程度上证实其证言的证明力,反之,则要慎重处理。本案中张某的母亲提出张某的户籍登记出生日期为农历,当地村委会也出具证明,证实当地农村一直有按农历纪年、孩子户口也按农历上报的习俗,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张某母亲的说法。
(二)要结合证人证言来认定
审查此类证人证言,一定要注意审查证人提供证言的背景、途径,即此证人是否由未成年犯监护人向办案机关提供,如证人系未成年人亲属、邻居等人,是由未成年犯监护人向办案机关反映未成年犯年龄存在问题之后,又向办案机关提供几名证人来证实,此时对证言的真实性要慎重考虑;如果证人提供证言系办案机关独立获取。事前证人与未成年犯监护人无串通之机。那么此背景下证人证言具有可信性。本案关于张某的出生日期有其姑姑、邻居的证言,因当时张某的父母均在广东打东,公安机关系自行前往张某的湖南老家调查取证,被调查人员事前并不知情,但均证实张某系出生日期为农历六月初二,此背景下获取证言内容具有客观真实性,且能印证张某及其母的说法,因此,对张某的年龄应当认定户籍记载日期为农历日期。
三、对年龄提出异议证据不充分的处理
此类情况是办案实践中遇到较多的情形,即未成年犯及其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的户籍证明记载年龄提出异议后,但经过办案机关调查又无法获取确实证据,如无出生证明、因农村学校合并、撤销等原因学籍档案无法获取。当地计生办、村委会又不能提供原始登记未成年犯出生日期的书证,有些知情证人因打工去向不明。只有一些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实践中处理此类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按户籍证明记载日期来认定犯罪嫌疑人年龄,理由是公安机关是法定的户籍登记部门,其所出具的书证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证人证言。根据1991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被告人犯罪时年龄问题的电话答复》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认定被告人的年龄应当以户口登记为基本依据……如果有足够证据认定户口登记册上记载的年龄有误,就应以查明的实际年龄来认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可见。上述两种观点的焦点在于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不同及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按第一种观点的证明标准是先行确认户口登记的证明效力,而无相反优势证据则不能对抗户籍登记。第二种观点确定的证明标准是以查明的年龄为依据,无事前确定哪种证据的证明效力,指控证据存在疑问。即如果控诉方不能提供优势证据指控认定年龄的正确性,即视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而应以证据存疑原则处理,这是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因为检察机关对犯罪进行指控,既是行使法定的职权,又是履行法定的职责,所以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承担提供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成立的义务。…检察机关按户籍登记指控犯罪嫌疑人犯罪时已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同时负有举证责任,但当辩方提出异议,经调查后无充分证据证实指控主张的。就应当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来处理,如上述张某对于户籍证明记载年龄提出异议时,且又有相关证据支持,据此精神应从充分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按照“就低不就高”原则推定张某犯罪时系未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