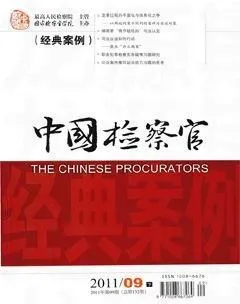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司法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虽然解决了绑架罪起刑点过高的问题,但又引起了新的争议,检法分歧较大。应以认定“情节较轻”所依据的事实要素为基础,避免解释的随意扩大,防止绑架犯罪的轻刑化和量刑的不均衡问题。
[案例一]2009年3月27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赵某伙同郭某(在逃)将在一网吧上网的蔺某叫出,开车将其挟持至某镇清水塘浴园。并控制在305房间内,二人对蔺某进行恐吓、打骂后,蔺某被迫答应拿钱了事。当日晚7时许,二人逼迫蔺某向家里人要钱。并与蔺某一起,编造蔺某偷走同事的项链需进行赔偿的谎言,蔺某以此为由给其姐姐蔺学某打电话索要人民币1万元,在蔺某和其姐姐通话中,被告人赵某抢过电话直接与蔺学某通话,谎称自己是那个被偷的同事,威胁如果得不到赔偿就向公安机关报警,并扬言如果拿不到钱就把蔺某弄到唐山去,蔺学某被迫答应给钱。8时许,由被告人赵某驾车带蔺某到县医院住院部门前。从蔺学某手中取得邮政储蓄卡一张,被告人赵某挟持蔺某到镇商业道邮政储蓄银行支取10100元现金后,蔺某把钱放在车上驾驶座旁的手抠内,后在县医院附近将蔺某释放。
2009年5月10日21时许,被告人赵某伙同郭某、赵玉某(均在逃)到某镇斯文网吧,将在该网吧上网的许某叫出后,乘出租车挟持至镇天宝洗浴中心,将许某控制在3019号房间内。以许某父亲欠郭某等人钱为由进行恐吓、打骂,向许某要钱,许某答应出钱后,赵玉某看守着许某在房间内休息。次日4时许,郭某、赵某等又编造许某玩六合彩欠黑庄钱。勒令许某以此为由向其家里人索要人民币7000元。郭某还直接打电话给许某的母亲索要,扬言如果不给钱就把许某拉到唐山去。其间多次打电话给王某要钱。王某报警并关闭手机。当日10时许,因害怕事情败露,当车行至镇天宝大酒店附近时,被告人赵某等将许某释放。
一审法院认定赵某的行为构成绑架罪,因其在参与绑架过程中,未使用极端暴力手段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仅在较短的时间内采用恐吓、打骂等胁迫手段控制被害人,且多是采取编造谎言等方式向被害人的亲属施压索要财物,尤其在第二起绑架中还主动释放被害人,认定其行为属于“情节较轻”,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后检察机关以本案不属于“情节较轻”,量刑畸轻为由提起抗诉,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了原判决。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基本与一审法院相同,只是增加了家属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表述。
[案例二]2007年11月至12月期间,曹某与施某、贾某、郝某等分别预谋绑架王某勒索钱财,并准备了作案工具。2007年12月25日16时许,施某伙同韩某等人在市内一浴池附近将王某绑架,其间,由韩某驾车,施某等对被害人进行捆绑、蒙头,在本市滨海国际学校附近将被害人交给了曹某、贾某、都某。三人将被害人带到了郊区一事先租好的房子内。向被害人勒索2000万元,其间,对被害人进行威胁和殴打,并让被害人给亲属打电话要钱遭到拒绝。2007年12月27日23时许,在王某答应付100万赎金后,将其释放,并限期5日内交出赎金。2007年12月27日至2008年1月3日间,被告人等多次打电话要钱,并最终约定交付30万,其间,被害人家属已经报警。2008年1月8日,公安机关将前来取钱的施某当场抓获,曹某、贾某逃脱,后主动投案。
一审法院认定五人的行为构成了绑架罪,由于被告人在绑架被害人后,未对被害人进行较熏程度人身伤害。在被害人表示交付赎金后释放了被害人,其行为属于“情节较轻”,并依据自首、立功、累犯等情节,分别判处五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四年、四年、三年六个月、三年六个月。此案,检察机关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没有再提起抗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6条对《刑法》第239条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增加了一档刑罚,对“‘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规定实施后,以“情节较轻”为由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处刑的司法判例屡见不鲜,但具体如何理解“情节较轻”则多有争议,作为认定“情节较轻”依据的各种事实情节也多有不同,已经影响到了罪刑的均衡和司法的统一。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新的理论争议点,此问题亟需解决。
本文两个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成为了检法争议的焦点。从案例来看,不同的法院判处“情节较轻”的理由也不相同。那么该案中面对众多事实如何认定“情节较轻”呢?
二、绑架罪“情节较轻的”理论分析
在具体界定“情节较轻的”之前,我们再来看两个判例。这两个判例刊载在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中,都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之前,都是最后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之下进行量刑的个案,应该说依据当时绑架罪的规定都是应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但是最后都突破了法定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量刑来看,这两个案例应该都属于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但是关于对此的理解。各级法院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量刑差异可谓天壤之别,尤其是第二个案例,从十一年到五年最后到适用缓刑,差别不可谓不大。
[案例三]2007年3月的一天,被告人俞某驾驶面包车途径某市内一十字路口时,看到被害人魏某(女,8岁)背着书包独自站在路边,因其无力偿还所欠他人债务顿生绑架勒索财物之念。于是俞某以送其上学为由,将魏某诱骗上车。后驾车途径该市下属乡镇及相邻的某市。期问俞某通过电话,以魏某在其处相要挟,向魏某的父亲以“借”为名索要人民币5万元,并要求将钱汇至自己用假身份证开设的银行卡内。当日10时许,俞某出于害怕,主动放弃继续犯罪,驾车将魏某送回梧桐街道,并出资雇三轮车将魏某安全送回所在学校。
俞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该判决最后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鉴于俞某绑架犯罪属临时起意,绑架人质采用诱骗方式,控制被害人时间较短,在控制期内未实施暴力、威胁,且能及时醒悟,主动将被害人送回,未对受害人造成心里、身体上的伤害,犯罪手段、情节、危害后果轻,对其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法,核准了该判决。
[案例四]行为人程某从其舅舅家偷走一步传呼机,因舅舅将此事告诉了村里人,程觉得无脸见人,产生了报复动机。一日,程租用“面的”车到其舅舅儿子聪聪上学的学校,将放学的聪聪骗上车拉走。而后程给其舅舅打电话索要6000元现金,限两小时交到。程给聪聪买了一些小食品之后,开车到约定地点等侯。程舅报警,程父获悉后与公安人员一起赶到现场。当时程与聪聪正在车上打扑克,程父走到“面的”车边搂住程的脖子,程见有公安人员,就把碗片放在聪聪的脖子上说:“你们不要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在其父夺碗片时,程划伤聪聪的脖子(表皮伤0.05×K3.0cm)。公安人员随即将程抓获。
该案一审判处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二审改判法定刑以下量刑,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量刑仍然过重,鉴于本案发生于亲属之间,犯罪情节较轻,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改判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
从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规则:(1)绑架犯罪分子对被害人控制时间较短,没有对被害人进行殴打、伤害、威胁的,并且主动放弃获取赎金、放弃犯罪,将被害人安全送回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可以适用“情节较轻的”规定;该项规则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放弃犯罪。(2)绑架犯罪发生在亲属之间,为了小事报复亲属的动机,主观恶性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可以适用“情节较轻的”规定。这两个案件确立的处理原则对本案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三、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的修订保持了法律适用的足够弹性,但这也给司法者留下了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直接导致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跨域两个量刑档次,从最低五年到最高无期徒刑的范围内自由裁量,权力太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情节较轻”进行解释,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五年到十年有期徒刑之间,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之间,缩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判定是否属于“情节较轻”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第一,危害行为之犯罪手段。绑架犯罪是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之一,其严重侵害性主要体现在犯罪行为手段上,一定程度上说,犯罪手段决定了社会危害性。具体到绑架犯罪,犯罪手段有严重暴力、威胁、一般暴力、威胁、威胁但未使用暴力、既未威胁亦未使用暴力之分。在拘禁时间上有长时间拘禁、短时间拘禁和被害人不知道自己被拘禁之分。这些因素均决定了绑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第二,危害行为之是否主动释放人质。不主动释放人质即可能有以下几种结果:杀害人质、人质逃跑或被解救。在大部分的绑架案中,犯罪分子要么杀害人质要么释放人质,杀害人质就是死刑,如果只要主动释放人质就认为“情节较轻”,而不考虑是否已经取得赎金以及赎金的数额和对人质的伤害情况,那么量刑肯定会失衡。
第三。危害结果之人身伤害。除去造成被害人死亡,确定判处死刑外。造成被害人的伤害结果有致人重伤且造成严重残疾、一般重伤、轻伤、轻微伤和没有造成伤害的程度之分。当然也存在造成被害人严重的精神伤害的情况。这种伤害结果是评判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方面。
第四,危害结果之财产损失。绑架犯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了人身权利,还侵犯了财产权利。因此,取得赎金的数额也是考虑其社会危害性的因素之一。取得赎金数额可以分为数额特别巨大、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和没有取得赎金之分。没有取得赎金又分为放弃勒索赎金、勒索赎金后放弃取得赎金和客观上没有取得赎金之分。
第五,人身危险性之是否主动放弃犯罪。上述提到了主动释放人质,释放人质并不一定放弃犯罪,有可能是取得赎金后的释放人质,主观恶性仍然较大。因为绑架犯罪控制了人质即构成了既遂,而此时放弃犯罪也不构成犯罪中止,不能减轻处罚,因此这种主动放弃犯罪的行为应认定为“情节较轻”。主动放弃犯罪是指绑架人质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放弃犯罪,如放弃继续勒索赎金,或者在获取赎金之前,自动放弃对被害人的人身控制,并将被害人安全送回。此时,犯罪分子主动放弃犯罪,其人身危险性已经很低,社会危害性也已经消除。
综上,我们认为应将“情节较轻的”认定为主动放弃绑架意图,恢复被绑架人人身自由,并且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和财产损失的情形。
认定“情节较轻”是一项综合的工程,应该从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两方面综合考量,而不能抓住其中一点不放。具体到案例一,法院的判决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情节较轻”。(1)“没有使用极端暴力手段控制被害人,主要使用打骂、威胁等胁迫手段”。怎样算极端暴力手段?拳打脚踢算不算?况且叶r已经属于暴力手段。而且胁迫并不必然情节轻。本案中被告人威胁其家属“如不付钱就将被害人拉到唐山去”。在本地人看来,“拉到唐山去”就是扔到矿洞里,属于死亡威胁。(2)“控制被害人时间较短”不成立,两起犯罪拘禁人质分别长达18小时和13个小时,18小时都算“较短”,那么多长时间算“长”?(3)二审法院认定“家属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该条属于单纯的量刑情节,不是认定“情节较轻的”依据。(4)第一起犯罪取得了赎金1万元,仅有取得赎金1万元这一点就不能认定“情节较轻”。理论上,三位专家的观点都认为不应取得赎金,或者取得较小数额赎金,l万元显然属于数额巨大。(5)虽然赵某认罪态度较好,但是赵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实施了两起绑架犯罪,主观恶性较大。(6)主动释放被害人不是认定“情节较轻的”依据,只有主动释放被害人并放弃犯罪才可以。
具体到案例二,被告人的行为亦不属于“情节较轻”。法院的判决理由同样不能成立。(1)“被告人在绑架被害人后,未对被害人进行较重程度人身伤害”,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拘禁被害人长达55小时,期间对其进行殴打和威胁。(2)“在被害人表示交付赎金后释放了被害人”,主动释放被害人但是并未主动放弃犯罪,被告人勒索赎金达2000万之巨,后降到100万元、30万元亦是非常巨大。释放人质后,仍威胁被害人并约定地点交付赎金。在现场被抓获。社会危害性大。(3)被告人对绑架被害人进行了多次预谋,并积极进行了分工,准备了工具,主观恶性较大。综上,我们认为案例一、二的情形均不属于“情节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