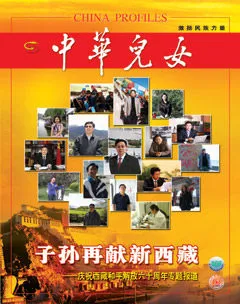格桑 一脉忠诚在高原
2011-12-29 00:00:00华南
中华儿女 2011年10期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格桑,是十八军进入西藏的第二代。上至父母、下到子女,格桑家扎根在雪域高原半个多世纪、跨越三代人。在格桑心里,祖籍四川、出生地北京,似乎都不如高原西藏亲切,充满了赤诚和情感。
父母的进藏故事
1951年初,格桑的父亲计美邓珠在四川康藏地区加入了解放军,正式成为十八军进藏部队中的一名藏族小战士。就在这个时候,家在四川康定地区的姑娘卓玛也光荣地入伍准备跟随解放军的队伍进发西藏了。
彼时这两个四川藏区的小战士相互之间还没有什么交集,或许更想不到跟随解放军的队伍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之后,所改变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生活,使两人结为终身伴侣,更将他们一生的事业和命运,与雪域高原的新发展紧紧相连。
其实早在1949年,计美邓珠就已经是一名进步青年,他参加了“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康区的外围组织。因为一直要求进步,计美邓珠于1951年初,解放军进藏前,先期被派到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进行简短培训,主要就摄影方面的技能和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学习培训。
卓玛的出身和经历似乎更富有传奇色彩。卓玛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蒙藏委员会藏文翻译官。在九世班禅转世和十三世达赖转世的过程中,曾担任藏文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1949年7月,震惊中外“驱汉事件”发生,国民党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卓玛的父亲,也在这事件中被逐出西藏。不过,他并不反对女儿再次进藏并且为了国家的统一而解放西藏。卓玛在重庆进行进藏前培训时,他还曾去看望女儿。
后来,卓玛也被送到北京学习。两个人在北京相识,携手一生。因为计美邓珠的工作原因,卓玛带着全家几次辗转北京、拉萨两地,最终留在雪域高原。直到退休,老两口才回到成都安度晚年,却仍旧把所有孩子都留在了高原上。
“父亲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西藏的变迁”
计美邓珠是新中国第一代藏族摄影师。身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高级摄影记者,计美邓珠大半辈子的时间里都在西藏进行拍摄,全藏区73个县,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现在所能看到旧西藏最野蛮、最残忍、最血淋淋的农奴制、新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的很多新貌,都是通过他和泽仁、扎西旺堆等几个同事一同记录保留下来的。
这是艰苦卓绝的工作。
西藏刚刚和平解放时,艰苦是所有进藏干部最为深刻的记忆。前苏联的嘎斯69汽车,已经是最高级的汽车,只有自治区领导才能因公使用。而拉萨之外的地区,条件更是难以想象。在格桑的记忆里,父亲每次下乡拍摄,都要准备很多很多工具,包括摄影器材、反光板,小到绳子、修理工具都不能缺。他跟同事的公务用车就是一辆破吉普,他们既要当司机,又要当摄影师,还有兼任修理工。藏区路况本来很差,高原地区气候又变化无常,车在路上抛锚是家常便饭。更有时候,因为当时西藏刚刚和平解放,叛乱分子和境外派来的特务仍在不时骚扰新生的县、乡政府,情况十分复杂,每到一地,当地人员都对外来者十分警惕。1960年,计美邓珠和同事到日喀则谢通门县拍摄《高原短途运输》新闻主题。因为两个人都只带了记者证,没有带地区的介绍信,加上整天骑马走路,样子十分狼狈,而且为了防身,每人还背着一只长枪和一只短枪,自然引起当地干部的注意。到了县城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走了两天,又饿又累,一顿吃了一百多个饺子,更引起他们的怀疑。计美邓珠和同事怎么也证明不了自己,当晚就被软禁在一间又黑又小的房子里,直到县里与地区、拉萨电报联系核实,明确他们的身份后,才配合拍摄工作。
这也是一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囿于通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们镜头所对准的,都是国家建设中的新变化、新经验,计美邓珠他们所拍摄的更是如此。每次电影之前所播放的新闻简报、祖国新貌,就成了全国人民了解国家进步的窗口。因此,即便再苦,计美邓珠也从未想过放弃。
已过半百,格桑仍旧感念于父亲留给自己的这种精神与情怀。
2010年12月15日,西藏墨脱公路控制性工程——嘎隆拉隧道顺利贯通。2012年,通往墨脱的等级公路将正式建成通车,墨脱不通等级通路的历史将就此终结。而今,已经有两条季节性公路通往墨脱,越来越多迫不及待的好奇的游客探访这朵“白莲花”,然而当年,揭开墨脱真实面纱的就是计美邓珠和同事。
“他们是步行进入墨脱的,背着摄影器材,边走边拍。”1981年,计美邓珠和同事次登,踏上了墨脱采访之旅。虽然行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和物质准备,进入墨脱之难还是超出他们的想象。进去的时候已经是5月,虽说是进入墨脱的最佳季节,但是徒步从米林县境一个叫派的地方出发,翻越多雄拉雪山,走路三天多,到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江畔的八崩乡,再从八崩顺江而上,进入墨脱县城,这一路地势险要,气候变化无常,经常发生雪崩或被雪风阻挡,没有当地熟悉情况的向导,没人敢去。途中,还要有几天时间是经过无人区,大量的蚂蝗叮得人鲜血直流。
那时条件艰苦,经济上也很紧张。拍墨脱,计美邓珠和同事他们只有5000元的拍摄经费,两个人手上总共才有20多盒30米的16毫米胶片,再多的美好,也要精打细算,节省拍摄,精心策划之后,才能开机。5月进入墨脱,8月出山来,历时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成首部忠实记录墨脱的纪录片《绿色墨脱》,第一次较全面完整地向国内外展示了西藏高原迷人的风光和独特的民俗,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对于宣传西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白莲花”墨脱终于将自己的风采向世人展示了出来。
在西藏摄影站工作的几十年中,计美邓珠拍摄了大量的有关西藏的新闻主题,用真实可信的镜头向世人展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百万农奴悲惨的生活和民主改革后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的喜悦之情,不少影片和新闻主题获得了各种奖项。
198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授予西藏站计美邓珠等四个老同志嘉奖,表彰他们在新闻电影事业上所作出的优异成绩。
“我用忠诚守卫国家的安全”
1961年,格桑出生在北京。
一岁时,父亲计美邓珠正式到新影厂驻西藏站工作,格桑也跟着父母进藏了。至今,格桑已在西藏度过了自己的半生。
格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计美邓珠共有兄弟姐妹13人,可是由于旧时生存条件实在太恶劣,最后只活下来三个。计美邓珠是个十分孝顺的人,在参军有机会走出牧区的时候,就主动把两个姐姐的四个孩子带出来读书,辗转北京、拉萨,共同生活。因此从记事起,格桑就是在大家庭里跟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生活着。
从1962年到初中毕业,格桑在西藏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记者父亲总是下乡采访拍片,格桑印象中,母亲的身影格外忙碌。母亲卓玛也是十八军进藏的小战士,进步青年,入伍后先在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学习汉语,后来当上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为数不多的几位汉语老师,当时很多上层进步人士都是她的学生。后来,卓玛又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要随驻站的丈夫进藏,才调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改学电影剪辑,后来就随着丈夫进藏了。应该说,为了丈夫的事业,卓玛将更多精力花在家庭中——照顾一个大家庭,周转生活,负担他们的衣食保暖和思想教育,但她从无怨言,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大家庭,对姑姐的四个孩子也视如己出,并将他们逐个培养成人。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物质生活普遍贫苦,西藏更是如此。格桑在家里排行第七,在格桑的记忆中,那是家庭条件还算不错,但兄弟姐们的穿着总是补丁摞补丁。可是父母无声的教育,父亲对工作的执著、母亲待人的善良诚恳,还是给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和最甜美的人生记忆。
而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格桑也在父亲这样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下做出自己的选择。
1976年,格桑即将初中毕业,“文革”尚未结束,高考尚未恢复,求学无门成为格桑他们那一代青年人内心中最为苦闷的事情。恰好,一天上课时,部队来招小兵,说是招到部队后要送到南京政治学院深造。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招考很严格,阵势也很大,“当时全校的男同学都被叫到操场上进行身体素质测试和才艺展示,同时还要参考学习成绩。”格桑样样都排在前列,而且学习成绩优秀,成为那一批被招入部队的藏区仅有的10个小兵之一,而且是唯一的藏族。
然而之后不久,因为种种原因,格桑他们这批战士不能去南京军校学习了,而是要跟普通战士一样充大兵进部队。条件肯定更艰苦了。“当时母亲有点心疼我,不想让我去了,可是父亲不让,他说既然组织上选中了你,就必须去!这是锻炼,也是组织的信任,更会为你的人生留下最宝贵的经历!”在父亲这位十八军老战士对部队的情结和对党、对国家的崇高信仰,将自己的儿子“撵”进了部队。
四年之后,格桑退伍,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干过很多工作,甚至包括宾馆房间整理,觉得有滋有味,大有作为,但是学习欲望从来没有消退,得知可以高考了,格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当年,格桑考中了西藏民族学院。“原本打算学英语专业,结果那一年因为招生太少没法开班,我们都转到了历史系。”回顾自己的生活,似乎总跟最初的打算不合拍。不过格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心怀的信念与理想始终如一,“这绝对来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又是一个四年。
1984年,格桑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回到拉萨。现在回想起来,他似乎从未想过留在内地,一门心思要回到拉萨,建设新西藏。这个问题他跟很多同样经历的人交流过,几乎所有像一样的“第二代”们都是这样想的。他把这归结为一种情怀。
最初,格桑想回到旅游局工作,但是他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宗教局。“当时我在局领导家里从晚上八点一直坐到半夜十二点,他也不同意放人。”领导给他的唯一理由是在西藏工作,民族宗教十分重要,要干好这一行可以大有作为。年轻的格桑那时并不是很理解,心里难免嘀嘀咕咕,但是知道领导是为了他好,也就踏踏实实地在宗教局里埋头工作。
时值“文革”结束不久,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工作正在进行,西藏地区寺庙众多,而“文革”时被保留的仅有9座,其余全部被毁,拨乱反正工作任务繁重。格桑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跟着时任局长赤来深入各地区对被毁寺庙进行调查摸底,“那几年跑了五六十个县,几乎去了所有的寺庙,对寺庙和西藏宗教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几年的学习过程,几乎决定了格桑日后的工作。
他开始站到反对极少数宗教分子分裂、保护宗教仪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线。十几年来,格桑先后参与到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等几个重点寺庙的整顿工作,还多次驻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很有效果。而在格桑的心中,最为难忘的还是参与对十一世班禅金瓶掣签的工作。这项工作差不多持续了两年,1995年12月8日凌晨五点,在拉萨大昭寺释迦摩尼佛像前,按照历史的宗教仪轨,进行金瓶掣签,由佛祖来神断第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在党中央、国务院、西藏自治区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44位佛教界高僧大德及各界代表的共同注视和见证下,“5点20分,喇嘛的诵经声停了下来。一个身着浅绿色藏装的藏族青年男子,从金瓶中取出如意头的象牙签牌,放在手中的托盘里,端到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面前,这是著名记者刘伟在《十一世班禅坐床记》一书中对当时格桑请各位领导验签时场景的描述。之后,格桑拿起用藏、汉文写有坚赞诺布、贡桑•旺堆、阿旺南索三个候选灵童名单的纸条,仔细地各贴一面在签牌上……格桑将名单逐一在签牌上贴好,放进托盘里。
格桑端着托盘从国务委员罗干开始,依次让生钦•洛桑坚赞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波米•强巴洛卓活佛、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喇嘛•次仁和三个候选灵童的父母等先验看并核察名签,他们首肯无误后;然后又依次让在座的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验看名签。
最后验看名签的是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他验完签后,拿起托盘中细长的黄缎封套,将名签套上。可能黄缎套过于细瘦,封装每只签,叶小文都用了一定的时间。这期间,整座大殿寂静无声,人们的眼睛都紧张地盯着叶小文的手。终于,叶小文镇定地将三支名签都装进了黄缎封套,他抬起头来,神色明显轻松了许多。
江村罗布大声宣布:“经审核,三名候选灵童的名单验签无误,请封签。”
后来只要谈到此事,格桑总是万分感慨:“能亲历西藏最高级的佛门盛事,终身难忘”。当然,重要的是此前多年在宗教局的积累。“没有之前的积累,后面的那些工作都是拿不下来的。”在政府部门的不同岗位上工作这么多年,格桑总是部门里被借调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很多突发事件,都是派他出去处理。工作的时间多了,陪伴家人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不过对于格桑来说,做好工作义不容辞。
责任在三代人之间延续
计美邓珠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西藏当摄影记者,没有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没有记者的职业道德,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绝对不行的。这话,也是格桑听父亲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在他眼里,父亲不止是这样说说,更是在几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恪尽职守地实践。
小时候,格桑看到的,几乎都是父亲背着器材下乡拍摄的背影。上到初中,格桑觉得自己也长成了大小伙子的时候,就主动要求跟着父亲工作。“其实就是想给他们打打下手,跑跑腿。”直到若干年后,父亲退休回到成都,一家人仍旧将工作放在第一位。格桑家里有不成文的规定,每到周末全家人必须要聚一聚,而逢年过节,更是要到父母家里报到,一家人在一起聚餐,其乐融融。母亲特别爱吃格桑做的菜,他自己也笑称自己的前世可能是厨师。要是谁不来,父亲要生气,不过要是谁有工作缺席,父亲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撵”他走。“我这没事,工作要紧!”格桑无数次听到父亲这么说他。
在家里,父亲是表率。“理想和信仰总是决定着前辈们的追求和坚守,在他们那一辈人身上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情怀。从他们一生的工作与奉献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触摸到、学到、体会到。”格桑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和岗位上,有的从文、有的从理、有的从军,也都在父辈精神的感召下为新西藏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工作后,格桑在与各族干部之间的交往和学习中充分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和敬业精神。1985年,格桑入选第一批藏族统战干部培训班,到北京中央统战部脱产学习一年。而西藏民主改革之后,在不同时期都有大批进藏干部、援藏干部为新西藏建设出力流汗,格桑跟他们在一起,多年来感悟更多。
“比如李作明, 他可以在同一个笔记本的左右两面同时做笔记,一边是藏文一边是汉语,会开完了会议纪要也做完了,而且真的是艺术。”让格桑时隔多年仍旧念念不忘的还有国家铁道部原部长屠由瑞,论证青藏铁路时他专门来沿途考察轮涨,他的笔记本真是一绝,一路下来记了六本,图文并茂,画的图就像小人书一样,地形、冻土和涵洞等等十分准确。
“这些老领导、老前辈的能力和作风,真是不得了。”格桑也努力地学着。国务院办公厅和秘书局的同志来援藏,他总同他们一道工作,并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工作方法。总之,他总是在学习。汉藏之间的交流多,隔阂自然就少了。而且在他看来,不论在藏干部还是援藏干部,还是像他们一样老革命留在西藏的第二代,大家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建设一个新西藏,责任感统一、目标一致,还有什么委屈呢?
现在,这种作风也被格桑遗传给了女儿。女儿尕美卓美厦门大学法语系毕业后,恰逢西藏自治区公安部门特招,经过考试,女儿成了一名公安战线上的战士。初入队伍时8个月的军训,格桑没有心疼,让她去充分锻炼。加班是家常便饭,爱人心疼女儿,经常抱怨,格桑很坦然,她只要在工作,就让她去忙吧。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格桑的父辈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和责任将一个新的西藏交到了格桑他们这一辈人手上,格桑说,他要继续把这种使命传承下去。他们的下一代,必须能扛起责任,肩负使命。
2010年上海世博会,格桑是世博西藏馆(网上西藏馆)副馆长、西藏馆驻上海世博园区办公室主任,半年多的时间里,格桑亲眼看到游客们带着好奇走进“天上西藏”的大门,乘着模拟青藏线奔赴雪域高原,再看着他们被兼具雄浑壮美和珍奇秀丽的风光所震撼,被西藏的日新月异发展所惊叹,“这是真实壮美的新西藏、幸福生活中的新西藏,发展变化中的新西藏。”半年多时间里,西藏馆迎来了超过800万的游客,格桑在场馆里看着川流不息、面带惊喜的人们,回味着父辈和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觉得怎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直到现在,上海世博会的纪念奖杯被格桑精心挑出来摆在办公桌显眼的位置,可能不止意味着付出,还是对“新西藏、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的期许。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庆之年,格桑分外忙碌,身为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他受命任大庆办活动组副组长,正在与各方共同忙碌着办大庆。大庆,不只是庆祝,更是回顾,是展望;是憧憬,是激励;是传承,是发展,“要画好一个句号,再翻开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