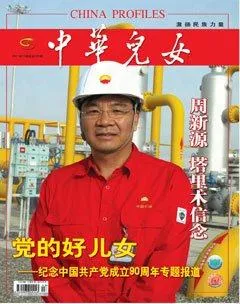金一南:我与《苦难辉煌》
一部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中共早期历史的史诗性作品《苦难辉煌》,于2009年一经推出,反响强烈,引发了中国全社会对自身历史与信仰的反思。作者金一南,1952年生人,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副军)、教授。
一部思辨性的理论著作何以会吸引众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眼球?算得上是与共和国基本同龄的金一南何来如此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应本刊之邀,常年处于“工作太忙,空余也已安排满”的超负荷状态下的金教授,这一次,按时完成了本刊的命题之作。
缘起
我是在国家最混乱、个人最狼狈的时候开始认识我们这个党的。
国家最混乱,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个人最狼狈,指从全优学生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3年国庆节,我作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前组成的方阵。游行结束,举着鲜花跑向天安门。事前老师一遍又一遍交代:如果鞋子被踩掉,一定不能弯腰去提,否则会被后面的人挤倒踩伤,而且还会弄乱前进队伍,让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大家互相叮嘱:哪怕就是光着脚跑,哪怕钉子扎进脚里,也一定不能停下来——其实天安门广场哪来的钉子?但当时这些少先队员的决心就是如此——不能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
当我们跑到金水桥西侧,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正好向这一侧走来,向少先队员挥手致意。那一瞬间深深嵌入我脑海。教室中间那幅毛主席的标准像,梦幻一般化为眼前的真人!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知怎么回事,眼泪像泉水那样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颊无节制地往下流淌。周围几乎没有例外,不管男孩女孩,个个在抹泪,个个在发出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呼喊。
那个年代已经被归入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年代。当时我这样一个11岁的少年,知道什么叫个人迷信?什么叫个人崇拜?在哪儿学的?谁强迫的?似乎都没有。那种敬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并不迷信,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用烈士鲜血染成。少先队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当红太阳迎面升起的那一刻,那种空前强大的磁场,还是让人觉得看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神——不管是醒来还是梦中,都是心中向往已久、敬仰已久的太阳神。
万万没想到时间不到6年,这些神圣东西在心中坍塌得所剩无几。
最初感受的冲击来自家庭变故——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投入“牛棚”,整天挨批挨斗,自己也由优秀少先队员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处遭人白眼。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于社会的震荡。印象最深刻的是1969年初送哥哥赴陕西插队。当时北京火车站外面正修建地铁,风沙漫天,尘土遍地。车站内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送别的人们开始还能把持住,大家相互拉手,强作欢颜。尖厉的汽笛突然拉响了,与此同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整个车站突然爆发出“呜——呜——呜——”似江河决堤一般的呜咽和大恸。我从未听过数千人像这样不约而同的集体失声痛哭。送的哭,走的哭,车下的哭,车上的哭,招手的哭,挥旗的哭,有的使劲压抑着哭泣,有的放声大哭……发自肺腑的集体悲哀像一柄灼热的利剑,再坚强的人也会被一下整体穿透。
后来又有过多次车站送行。每次都像全体约定好了一样,列车汽笛响起那一刻,车站内会发出整个站台为之颤抖的恸哭。没有到过现场的人们,想像不出那种声音给人以怎样的冲击和震撼。1969年北京车站送行那种渗入骨髓的集体大恸,已经聚集足够的能量,让人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场“革命”无论表面怎样轰轰烈烈,在普通大众的内心中已经被摒弃。
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问号。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半夜睡不着时想,早晨醒来想,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的路上也想。我开始看书。不再像以前凭兴趣看《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而是开始寻找能够回答脑中问题的书。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
就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混乱年代,我被“毛选”中那种真实、那种质朴、那种睿智深深吸引。特别是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给我以至今思索不尽的启示。
我常常想:这个命题让我们来答,将会是怎样?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英明的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其它四条完全围绕这一条展开。分析环环相扣,严密透彻。
结论让我吃惊。并非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的红色政权就必然存在。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就很难有边区红色根据地,就很难有红军的发展;没有各个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不知还要增加多少艰难险阻、还会承担多么重大的损失。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道难题,就这样在毛泽东面前变为一层窗户纸,一下子就捅破了。我与其说是被其中的冷静解剖和深刻分析所震惊,不如说被当年毛泽东那种实事求是、那种对中国社情和国情的洞悉所震惊。
我开始隐隐感觉到,这个党及其领袖,并非像当时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带着不解的思索走向社会,满腹狐疑地打开毛选。合上毛选时,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在内心出现。我感觉似乎已经触到了这个党最具生命力的那些元素。如此有力的东西一旦能够恢复,不愁胜利。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在那段最让人压抑的日子里,我趴在连队的铺板上,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长文:《我爱中国》。其中一些想法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对恢复我党光荣与力量的渴望,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可以说已经跃然纸上。当时连队一个绰号叫“大胡子”的战友按捺不住,半夜一个人偷偷爬起来,去撕连队墙报上“批邓”的大标语,被起来上厕所的人看见。那个年代谁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帮他保密。但消息不免还是漏了出去。后来机关的人跟我们说:幸亏很快粉碎了“四人帮”,否则你们连队已经被列为调查重点了,你们几个都是调查对象。
几十年过去,原部队早已撤销,“大胡子”也转业回山西老家,退休下岗,过着并不宽裕的生活。每当接到他的电话,我都能回想起湖北老河口那个冰冷的冬天,他裹件棉大衣溜达到墙报底下,环顾左右、一把扯下墙上“批邓”标语的情景。那是我心中一幅恒定的图画。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它依然在描述30多年前,多少个像“大胡子”这样赤诚的中国人,以可贵可佩的内心良知和使命自觉,强烈要求国家变革、强烈盼望民族富强的图景。
以上这些,后来都成为我写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思考
我是在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很多人问我: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化,写了这本书?我也多次这样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有人认为有没有信仰无所谓,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人说过去的信仰和理想,今天看来都是谎言和欺骗。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机遇与偶然,利用了对手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执掌政权也没有经过投票选举。
有人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甚至连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样的话中国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实现建设和发展,速度比今天还要快,早就已经繁荣富强了。
面对这些思潮,我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法国的德军士兵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今天的历史回音壁上震响。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放眼全球,哪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如此起伏跌宕的波折?要认识与对待我们自己这部千曲百折的历史,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没有思想的力度,无法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纷繁烟云。没有力度的思想,每经历巨变,都不由自主全盘否定过去,企图推倒重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容易看成一部不断从这个极端跳向那个极端、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抛弃的历史,到头来只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种只见断层、不见积累的思维方式,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成熟。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动荡混乱的日子里产生一种坚定的,认为只要这个党恢复自身拥有的健康力量,仍然能够胜利。在国家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今天,一种思虑反而越来越重。如果不能深刻地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如果认为腰包鼓起来就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可以抛弃掉那些使我们获得力量、从而变成虎虎有生气的真老虎的东西,前面等待我们的,真的是伟大复兴吗?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