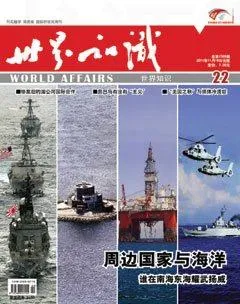G20:议题置换与权力之争
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济结构出现了巨大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全球治理中心”的七/八国集团(G7/8)从世界经济舞台上迅速后撤。由G7/8创立的二十国集团(G20)却由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会议,并于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第三次金融峰会上正式“自我加冕”,取代G7/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G20由G8成员国、11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简称E11)以及欧盟组成。鉴于澳、韩两国已被列为经合组织成员国,真正的“新兴经济体”在G20中并不占据数量优势。
在G20成立后的几年间,G7/8一直试图操控。G20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透明、善治和开放等观念,都明显具有G7/8的价值特色。在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后,G20也没有延续此前部长级会议的轮替制度,主办权被牢牢操控在美欧手中。前四场峰会由美、英、加三个G7国家操办,第五场和2012年的第七场才转手韩国和墨西哥。这使不少论者认为G20只不过是G7用来提高自己合法性和支持基础的工具。
不过,作为G20内平等的成员国,E11重塑这一机制的前景也相当明朗。在G20会议上,E11国家同样拥有三项关键权力:发起和设定议程、修正政策提议、批准和否决政策。第一项权力可以将E11国家关注的议题提交会议讨论,后两项权力则可阻止G7国家滥用权力。由于G20是基于成员国的共识来做出协同行动,这就从程序上保证了E11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
1999年G20成立后,在部长级会议上,几个主办的发展中国家印度(2002年)、墨西哥(2003年)、中国(2005年)、南非(2007年)和巴西(2008年)即利用议程设置权有效发挥了影响力,尤其是中印两国。印度将发展和援助纳入了G20的视野范围。中国则强调“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并促使其关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问题。
没有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这个议题更能吸引E11国家的注意了。自2005年中国在自己主办的河北香河部长级会议上将其作为重点议题讨论、并最终发表《二十国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声明》以来,如何对该体系尤其是对对危机负有重要责任的IMF进行改革,成为此后E11关注的焦点。
在“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下,这一体现G7绝对主导权的体系开始重构。被称作“金融富国俱乐部”的金融稳定论坛(FSF)率先改革。2009年3月,FSF吸收了G20中所有未加入论坛的E11国家为其成员。次年10月,韩国庆州召开的G20部长级会议就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超过6%的份额被重新分配。世界银行则提前一步,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至47.19%。其中,中国在IMF和世行中的投票权分别从3.72%和2.77%升至6.39%和4.42%,成为两家机构的第三大股东国,仅次美、日。印度和巴西也将继中国和俄罗斯之后,跻身十大股东之列。此外,G20还就取消关于世行和IMF总干事分别来自美国和欧洲这一惯例、改革执董会的构成达成意向性共识。
发展问题是E11国家关注的另一重要议题。在前三次领导人峰会宣言中,提及这一问题的字数从2008年华盛顿峰会的651字增长到2009年匹兹堡峰会的2292字。2010年的多伦多峰会体认到“缩小发展鸿沟、消除贫困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成立“发展工作组”。此后11月的首尔峰会又首次将发展议题确定为会议主题,并就旨在消除发展中国家贫困和缩小发展差距的“首尔共识”达成了协议。
在G20会议上,E11还有效发挥了“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身份,为其争得巨大实惠。比如2009年的伦敦峰会决定,“通过全球金融机构追加8500亿美元可用资金,……从而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支持由各多边开发银行(MDB)大幅增加至少100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贷款,并确保所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安全,包括拥有适当的资本。”这两个条款特别照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一些由“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外围机制纷纷涌现,为更好协调发展中国家在G20里的立场和政策提供了重要舞台,比如IBSA(印度、巴西、南非)、BRICS(金砖国家)、BA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中俄印三边会议等。这些机制里,BRICS发展速度最快,目前也最为成熟,已在G20框架内建立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晤机制。
南非作为非洲国家在G20中的惟一代表,除了加入一些新兴组织外,还联合一些非洲国家成立了“非洲十人委员会”。他们每次在G20峰会前后召开会议,为非洲国家参与G20预先确定目标和战略。
当前,G20正不断稳固和扩大自己在国际经济治理当中的地位,与此同时,E11国家的实力和相互协调能力也在迅速增长阶段。这一双重演进格局,将深刻改变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