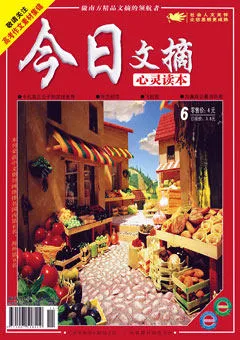寻找离你最近的广州
历史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是,打扮小姑娘是要花成本的,没有回报的事情谁也不会干。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微博还是同城媒体,都不约而同纷纷开始打捞广州的历史。无论是照片还是文章,关注点都不再是唐宋元明清,而是民国以来了,虚无飘渺的西关小姐东山少爷也在这一轮的关注热潮中踪迹难觅,取而代之的是民国以来的建筑人文,广州的市井图像,甚至有媒体还挖出民国时期广州的生活成本,结论是彼时的广州房价便宜,打电话贵。对广州历史关注的眼光已经开始收拢,这是个好现象。由远而近,由传说而实证,不再为商业利益和政绩而穿凿附会,只是为了认识一个真实的广州,只是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
当传统成为了商场和官场的时尚,我们真的有必要去反思这传统和那传统本质上的区别。城市当然是越老越荣耀,哪怕只是比别的城市年长一岁。但是在言必称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拆掉100年前的建筑,这城市荣耀的逻辑何在?
说实在话,不管是南越王那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剑,还是北京路厚玻璃下那一层层朝代不同的马路,这些只有专家才看得懂,老百姓再热情,看的也只是热闹。对于现实的广州而言,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才是从依稀可辨到硕果仅存的。而从教育角度看,民国史一直比较苍白。现在,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开掘民国以来的广州历史,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好事情。当年我们在书本上得知陈济棠是大军阀,下乡时又听老贫农说“陈济棠时代是广东最好的时代”,当时真是大吃一惊。几十年过去了,定惊的药还没有出来。只能够说无法真诚地面对历史的城市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未来的。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广州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从工业大道的崛起,到两县一郊的变迁,从城中村的兴亡到天河新区的成长,更不要说当年火车站附近的由乱而治,番禺的鱼米之乡变身如今的华南板块……超过半个世纪的广州当代史,只有零星落索的记叙,没有系统的梳理记载。很多东西天生天养,风不留痕,昨天的广州曾是什么模样?昨天的广州对今天的广州意味着什么?统统早已无从考究。连五六十年的历史都搞不定的城市,有何资格奢谈两千多年历史?
有句名言说,历史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人干吗闲着没事干去打扮小姑娘呢?也许小姑娘养眼,也许小姑娘可以揽客,总之打扮小姑娘是要花成本的,没有回报的事情谁也不会干。广州这座老城也给打扮了好多年了,现在人们终于觉醒要自己去寻找这座老城过去的一切,前提是真实的一切。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欣慰的。这是这座城市的一次文化觉醒。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必定会被夹带私货,这个也属正常。食住上,商人的惯技而已。
有一个很怪的惯例:无论是一个破碗还是一座建筑,清朝以前的东东才叫历史,民国以后的就什么也不是了。从现在开始倒推百年的这一段只能叫过去,不能叫历史。过去不值钱,历史才值钱。历史要保护,过去则要摔就摔要拆就拆。历史要研究,拿着放大镜刨故纸堆,过去则由他去吧。哈哈,什么逻辑?大家都懂的。
倘若真的爱广州,倘若真的想要认识一个真实的广州,不妨从寻找离自己最近的历史开始吧。包括时间的最近和空间的最近。
(自维然荐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