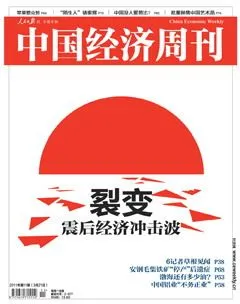东亚经济不会“海啸”
“3·11”强震不仅是日本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面对饥寒的灾民、破碎的家园,还有可能的核辐射危险,日本步履维艰的经济能否负担起灾后重建和快速复苏的重任?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所面临的伤痛是否会波及四邻乃至全球经济?
全球的目光,聚焦于这个在灾难前坚韧顽强的民族。
不应低估日本灾后恢复能力
尽管截至目前“3·11”强震的损害情况还没有最后的定论,但综合考量灾害烈度、受灾地区和影响人口几个方面,“3·11”地震成为日本自近代以来最惨痛的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二战前的关东大地震死难人数远超此次地震,但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不及此次地震,1995年的阪神地震经济损失巨大,但死难人数和波及地区却肯定远逊于此次)。
目前的日本经济陷入了巨大的和全方位的困境。按照瑞信银行的估算,仅震区直接损失一项,就超过了1710亿美元。此次地震及由此引发的海啸集中于日本的“京滨工业地带”,地震不仅造成了大量企业的直接财产损失,核泄漏风险和大规模停电还造成日本制造业、半导体的大规模停产。日本国民经济赖以维系的国际进出口贸易已经陷入巨大的混乱当中。
宏观经济的损失还可以慢慢消化,救灾本身所需发生的巨大费用与政府预算的捉襟见肘,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14日已经表示,本财年预算中剩余的约2000亿日元都将流向地震及海啸救灾和重建工作。
考虑到灾情的严重,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够的,日本政府修改年度预算筹集更多的款项已难以避免。可是,作为国债规模已超过GDP200%的发达国家“第一债务大户”,日本政府再筹巨款谈何容易?继续借债呢,势必加剧偿债风险;超发货币吧,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前景。
一个如此巨大的灾难突如其来地降临到岛国日本头上,政府目前处境艰难是肯定的。但是,某些分析机构据此就断定,灾难会对日本经济的总体走势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为时过早。
以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为例,那次大地震给日本造成了2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日本当时经济总量的2%。但是日本在地震发生的当季度就实现了经济环比增长,地震后第二季度甚至完成了5.1%的高增速。由于日本在那次大地震后V字形恢复很快,1995年的全球经济实际增长指标和年初的预期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中国的汶川大地震这样的超级自然灾难,都没有给受灾国和全球经济带来显著的伤害。由此可见,过分高估自然灾害对受灾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这一是由于全球金融、物流和工业网络的发展使全球经济的敏感性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这增强了恐慌情绪造成全球经济短期波动的能力;二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在某些方面是不可预测的。统计损失经常要面临事无先例、标准匮乏等问题,相应部门对灾害评估也总是要“就高不就低”好给自己足够的伸缩余地。
至于如何解释自然灾害后迅速的V字形恢复,很多经济学家都将它归功于大规模灾后重建工程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自然灾难发生之初,受灾地区和国家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与全球生产和流通链条脱节的现象。
这种流动性的突然中断在全球化时代显得格外突出和严重,但它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实质性损害却并不大。只要实体性的国民经济没有被灾害摧毁,一个国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网络的步伐会很快。更重要的是,国际物流恢复所需的海量成本中,很大一部分还会由急于购买该国商品和服务或急于在该国重建工作中分一杯羹的其他国家承担。
今天的日本,虽然大量制造业工厂停工,但是即便震区里绝大多数企业的设备厂房也没有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熟练的技术研发和制造队伍也保留了下来。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具有很大的不可复制性,只要经济混乱不持续太长时间,产业链中的上游和下游国家没有必要、同时也找不到替代者来填补日本留下的空白。而在这个灾害处置体制完备的国度,经济恢复正常运转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太久。
统计显示,“京滨工业地带”在此次强震中损失掉的工业设备,绝大多数是日本本土就可以生产和补充的。可以说,只要实体产业的“元气”保留了下来,只要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实体经济遭受破坏对金融、期货等产业的影响就是可控的和低风险的。
这,才是我们对日本宏观前景报以乐观态度的原因。
中长期影响:世界经济会感受到余震
虽然依据现有信息,强震不至于对日本经济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但是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不确定性确实增加了。目前,起码有两个变量会严重影响到日本乃至东亚区域经济未来几年的发展态势。
第一个变量就是核泄漏风险对日本能源供应政策造成的长期影响。
应该说,“3·11”强震与以往全球历次自然灾害最大的区别其实在于核能电力所造成的二次伤害究竟有多大上。福岛核电站的连续爆炸,已经构成了此次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尽管福岛变成第二个切尔诺贝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核能安全在巨大灾害面前的脆弱性已经展露无遗。日本自2006年5月公布《国家能源新战略》报告草案及《核能立国计划》以来,短短几年已经变成仅次于美、法两国的世界第三大核能利用国。
但是,大地震不仅证明了日本比美、法两国的根本劣势在于地理条件的高风险性,更使整个世界清楚地看到,核能带来的社会恐慌情绪有多大,现有技术水平在应对核能风险时有多无力。1995年的阪神地震引发了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革命,“3·11”强震会不会带来日本能源政策的巨变?日本是否会继续延续核能立国的政策,是否会对核能利用采取更为苛刻的管理,由此推高的成本是否会导致日本能源自给政策走回头路,是否会导致日本转变新能源开发的方向?
日本的强震,对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和新能源开发的中长期走势的影响,可以说是难以估计的。
第二个变量就是日本财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目前经济学观察家们多将目光集中在灾后重建的沉重负担是否会迫使其开放严苛的基础设施建设门槛。其实由此引发的问题更有价值,那就是:民主党内阁是否必须放弃“不要混凝土、要人民福利”的财政体制改革?
今天的民主党内阁似乎别无选择,灾后重建、恢复灾民正常生活的任务都是刚性的,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尽管极度缺钱,但它必须同时做到“要混凝土、要人民福利”。已经迟到了15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出现了再次熄火的苗头。
从灾后这几天日本朝野双方密集的协商还有前后不一的表态来看,日本现在还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日本财政体制的改革一旦停滞,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将更加模糊。东亚乃至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都将感受到经济余震。
起码,现在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需要为日本新一轮增发国债、超发日元做准备了。尽管世界似乎已经习惯了日本15年的蹒跚不前,但是日本对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灾难再次使日本脱离改革的方向,这对于正处于发展十字路口的东亚经济圈而言,自然不是什么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