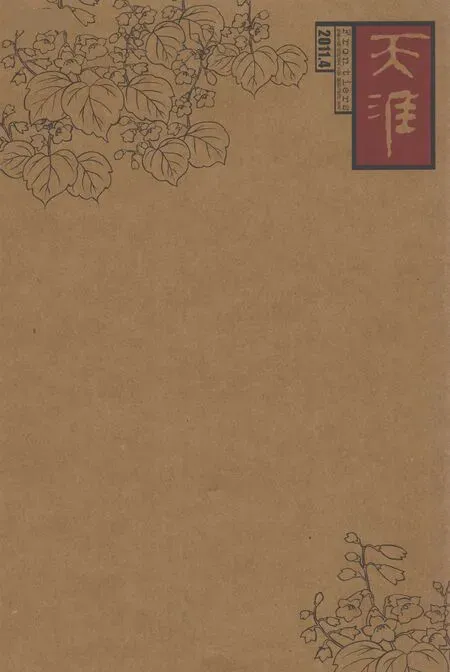经验,在最深处
东西
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是刷牙、洗脸,第二件是吃早餐,第三件就是上网浏览新闻。如果电脑摆在床头,那第三件事很容易就变成第一件。开车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周末,我会看看纸媒的深度报道。尽管我还没“织围脖”(开微博),但《手机报》每天必看。我关心利比亚动荡的局势,关心日本福岛的核辐射,为美国国会差一点没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捏一把汗……坐在家里,搜索天下,我像海绵吸水那样吸收信息,生怕自己变成瞎子和聋子。必须承认,我已经被媒体绑架,并且被绑架了还快乐着。
为什么我对消息如此着迷?是老爸的基因遗传,抑或是害怕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身心的反应可以证明,当我获得有价值的消息时,会本能地产生愉悦感。这种“愉悦”解释了我为什么会有好奇心,为什么会有求知欲和窥视癖,也就是说,打探消息是人类的本性。媒体高度发达和网络海量储存,正好满足了我对信息的需求。我不用经历枪林弹雨,却可以看到真实的战争;我不用顶烈日流臭汗,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动物;我不用办签证,却能欣赏外国风光。那些昔日必须亲临现场才能看见或知道的,现在都由别人的摄像机免费供应。记者在冲锋陷阵,探险者和旅游者在边走边拍,上帝和政治家在导演。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令人目不暇接,新消息源源不断地到来。
基于以上的媒体环境,一个美国作家和一个中国作家很有可能同时关注一个事件,比如“9·11恐怖袭击”,比如“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除非你对这个世界不闻不问,否则很难逃脱消息对心灵的影响。利比亚动荡的局势刺激我对权力的反思,日本的核泄漏影响我的生死观,法国戴高乐机场屋顶忽然坍塌砸死两个中国人引发我对偶然的感叹……只要我们连线,全球资讯都可以共享。遥远的事情变得很近,愤怒和同情延伸得很远。这就是中国唐代诗人张九龄描写的状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正如毛泽东的诗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样的信息当然会喂养出相似的思想。为了所谓的世界视野,我们可能已经牺牲掉了自己独特的经验。就像移栽到城市里的树木,虽然它们各有故乡,但移栽到城市之后,它们享受同样的阳光,吸收相同的养分,经历类似的风雨,于是也就呈现出相似的表情。过去在写作上竭力强调“不重复自己”,但在信息共享的今天,我们却尤其需要警惕“重复别人”。
清醒的写作者早就呼吁作家们走出象牙塔,直接面对太阳、风雨,贴近大地,直接与人交流和恋爱,回避媒体提供的二手生活。这当然是获得独特经验的一种方法,也是避免“同质化”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在西方,一些作家坚持不看电视、不上网、不拿手机。他们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用皮肤感受,只写自己的体验。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生在法国,长在非洲,求学英国,在泰国服兵役,在美国执教,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热爱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印第安部落,拥有毛里求斯和法国双重国籍,是一个旅行者、流浪汉。他在小说《诉讼笔录》中塑造了一个反现代文明的角色亚当·皮洛。此人独自呆在一所荒废的空屋里,整天无所事事,不是光着身子晒太阳就是到处闲逛,除了关心吃喝拉撒,对现代人的政治、经济、交往、文化、娱乐、信息、知识等均不“感冒”。他腾空脑子,过着近乎原始人的生活,把自己降为非人,模仿狗的动作,渴望像狗那样自由地撒尿和交欢,甚至力图物化自己,恨不得变成青苔、地衣,差不多就要成了细菌和化石。勒克莱齐奥认为人们的生活都千篇一律,好似千万册书叠放在一起,每个人都丧失了个性,只有亚当·皮洛才是世界上唯一的活人。
这是勒克莱齐奥绝对的个人经验,也是他天真的梦想。人类已经回不去了。让一个“被文明”的人接受亚当·皮洛那样的原始生活,和让亚当接受现代文明的难度几乎是一样的。对于亚当来说,文明的过程就是吸毒的过程。他拒绝吸毒,保持着自然人的特性。而我,或者说我们,已经一头扎进了现代文明丰满的胸怀,正美滋滋地享受文明带来的诸多便利,当然包括享受信息便利。由于媒体高度发达,信息爆炸,判断难免会被干扰。在我的脑海,有一个媒体塑造的美国;在你的脑海,有一个媒体塑造的中国。但是,当我们脱离媒体,去亲历去体验的时候,突然发现对方原来不是媒体上描写的那个对方。媒体的塑造和真实的经验发生了偏差。“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各大媒体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报道。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多次向媒体保证:没有隐瞒核辐射事故的任何事实。但是,2011年4月3日,距离核辐射二十四公里远的南相马市市长樱井胜延通过视频向外界求助时却说:“由于我们从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获得的信息非常少,我们被孤立了。”以上三方,我不知道哪一方的信息诚实准确,就像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那样,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谎言,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他们在报道地震的时候,为了不传播消极情绪,镜头和文字尽量回避残忍的死亡、失态的呼号和过度的泪水。而这一切正是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作家们最愿意描写的段落。为了不使国民心理产生太大波动,媒体有意或无意会过滤掉一些细节,遮蔽掉部分经验。如果作家只从媒体上照搬生活经验,那他的写作内容很可能在源头处就已经弯曲变形。
警惕媒体,又离不开媒体。这是全媒体时代作家们的宿命。作家在需要个人经验的同时,还需要宽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新鲜的材料。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如果完全抛弃媒体,那他的视野也许就受到限制。所以,我离不开媒体提供的经验,甚至在写作时需要二手经验对一手经验进行补充。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基本都生活在网上,从网上获取经验已是他们的常态。我不能否定这种生活,也不敢妄言来自网上的经验就一定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有时候,媒体视频播放的画面,比自己的亲历更靠近目标,更接近本质。我就在慢镜头里看到过眼镜蛇毒液喷出时的形状和曲线,这是肉眼根本没法看清的事实。二手经验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眼睛的前方尚有一个镜头的存在?新闻报道的后面还有记者的大脑、媒体的企图?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拨开迷雾的过程。拨开得越深,也许就越能看到有价值的经验,就像珍珠在蚌壳里,就像思想在大脑深处。面对媒体海量的信息,作家必须学会用减法。比如用一支香烟的重量减去烟灰的重量,你就能算出烟的重量。用人体临死前的重量减去死掉一分钟后的重量,你就能算出人类灵魂的重量,有人说答案是二十一克。如果我们能算出镜头过滤掉的温度,能算出记者大脑的用意、媒体的企图,那一部伟大的作品也许就产生了。作家的作为就在这轻轻的二十一克里,他们在信息与作品之间设立了一道复杂的工序,那就是作家心灵的化学反应。这个反应过程就是写作过程,真的被保留,假的被抛弃,正好与食品造假的工序逆行。有了作家的心灵检测,我们就能从小说中读到真正的中国经验或美国经验。这也是作家存在的理由。他们可以从假的信息里提炼出真的信息。他们一次次证明虚构比现实更可信。
所以,经验在媒体的里面、在生活的深处、在心灵的底层。如果我们没有灵魂引导,没有追问需求,没有开采能力,那就有可能永远触摸不到真实,那一本本砖头似的作品所呈现的,也许都是经验的表皮,也许就是货真价实的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