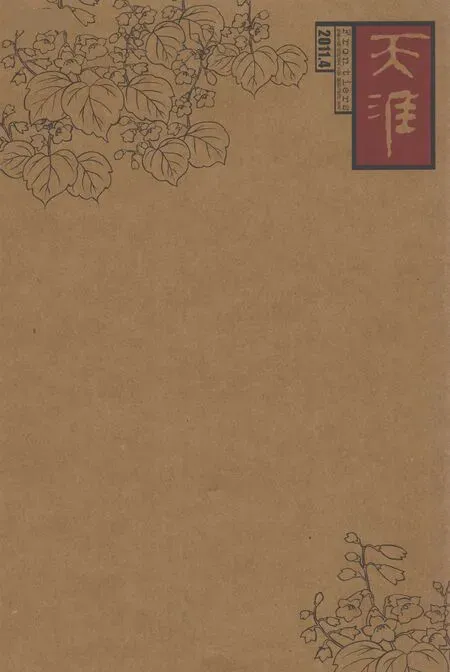百年排湾:一个头目吟唱的生命史
李娜 吉娃斯·阿丽(高金素梅)
百年排湾:一个头目吟唱的生命史
李娜 吉娃斯·阿丽(高金素梅)
荣耀家族
话说台湾光复初期,国民政府要山地同胞登记汉姓,广财的外祖父来到户政事务所,却拒绝抽签抽个张王李赵。他问办事员:你们汉人最大的头目姓什么?
答曰:蒋。
外祖父说:那么我就姓蒋。
至于名字,“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你们汉人怎么说?
天明喽。
于是,“蒋天明”,就成了广财外祖父的汉名。身为玛家乡玛家村的头目,身为太阳神、百步蛇的子孙,即便不得已委身于异族姓氏,他以此彰示平等,铭记家族。排湾族,用汉人学术的话语,是社会阶层最分明的一族;而排湾人亘古的记忆里,部落是一个各守其分的“大家庭”。头目便是大家长,族人把小米田里最丰硕美丽的收获献给他;他则要负起保护部落、照顾每一成员,尤其是老弱孤独者的责任。因此,在头目家族中,世袭的不只是荣耀,亦是责任,是品格。
1961年出生于屏东县玛家乡佳义村的林广财,族名Negerenger,属于kazangiljan家族。他的成长岁月,见证了头目文化的荣耀与式微。伴随头目制度的解体,并不只是“贵族”的衰落,而是整个原住民族在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被席卷而入社会底层的命运。
头目广财十六岁离家到平地,做过搬运工、绑铁工,跑过远洋,进过林班……在都市流离的生涯中,广财唯一葆有的头目家族的特殊财富,大约是那自小缭绕耳边的古调,在各种祭典上,在自家的石板屋里,母亲与族人们悠扬的吟唱,如种子酣眠在广财的记忆里,等待着有一天,被唤醒,被拭亮。
文字之前,歌唱毋宁是人表达和记录生命的本能。人们用歌谣表达悲欢缱绻,用歌谣描摹人与自然的依存生息,也用歌谣传递祖先的叮咛。古调就是原住民的史诗,传颂古调,因而是头目家族的重要职责之一。广财无疑得天独厚,何况,少年广财已经有清亮辽远的歌喉和令人赞叹的歌唱才能。但在1960年代末期便开始进入部落的电视机前,炫目的现代社会和它的时尚,早已俘获了部落少年的心。都市夜晚的工地上,与朋友们弹着吉他纾解乡愁的广财,唱的是流行歌曲,是林班歌。在加入因1999年9·21地震救灾而成立的“飞鱼云豹音乐工团”、将音乐与原住民运动结合之前,广财几乎没有想过唱古调。
多年后,因一曲《来苏》而成名的广财回到部落,重新跟父母和部落老人家学习古调。有一天,他听到母亲和族人谈论家族故事,人届中年的广财,怦然心动,在外的沧桑,使他回头思考部落族人对父母的期许、父母对自己的期许,领悟头目家族与部落命运的息息相关;或许,也领悟到半个世纪前,外祖父“蒋天明”宣示的族群尊严,与排湾族无法抵抗的同化命运。《荣耀家族》那充满力度、庄严、骄傲,却又有着某种莫名的悲怆与紧张感的旋律,就这样从心底流出。
我们是kazangiljan家族,名满四方。
我们是kazangiljan家族,至高无上。
这是广财唯一的自创曲,也是《百年排湾》的序幕。广财仿佛是站在遥远的山上歌唱,引我们循歌声而去,歌声愈来愈亮:荣耀的kazangiljan家族,带我们回到排湾族自由自在的往昔。
一声Lumi响起时,仿佛是广财呼唤着族人,来到他们中间,在丰年节上,领唱这首古老的歌谣。从前,七八月小米收获,部落要举行十天左右的欢庆仪式,这是岁时最大的祭仪,也是部落“历史教学”的现场。Lumi是起调的虚词,围绕着丰收的喜悦,对祖先和神灵的感念,歌词即兴而发,在一人唱、众人和的反复吟咏中,劳动与生存的诗性得以最自然的呈现。
来吧,我们来唱祖先的歌谣,
一唱再唱,多美好。
不要忘记今天的歌声和欢笑。
让祖先的故事,永远流传。
啊!情人!那些模糊的历史面影
日据时代,部落的丰年节慢慢变成了“运动会”,这是殖民政府移风易俗,炼成“皇民”的手段之一。仪式上的许多歌谣,逐渐失去它的生活基础、它的传唱领域,开始成为老人家才会唱的“古调”。与此同时,其时流行于日本民间的演歌也漂洋过海,来到原住民乡;接触到现代音乐的部落青年,如卑南族的陆森宝、邹族的高一生,开始尝试将日本或西方音乐与传统歌谣结合的创作。高一生写于1950年代的《春之佐保姬》和《移民之歌》系列歌曲,是为典型,在他的歌中,东洋风与部落风的温婉结合,不仅烙印着时代的面影,也记录着早期原住民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求出路的柔韧心志。
本专辑里的《啊!情人》和《奈何》,是散发着日本演歌风味的排湾情歌,一首流传于屏北玛家乡,一首流传于屏南狮子乡。日本演歌那种淡淡又悠远的哀愁,与排湾情歌特有的千回百转的韵调相结合,被广财演绎得如此动人。情歌向来是先民音乐的大宗,而一个崇尚猎人、勇士的民族的情歌,是侠骨柔肠的极致表达。
想起你呼唤我“哥哥”,
声音忽远又忽近。
啊,你去了哪里!
怎能忘记,
你曾这样呼唤我。
这两首歌,广财从妈妈那里学来,创作人不可考,年代是光复初期,他只知道,“这是上过日语学校的那代人唱的吧”,总之是日据年代留在部落的印迹之一。日据时代留给排湾的,当然不只是醇美的歌谣。或说,这醇美歌谣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被殖民的伤痛与抵抗。在战后台湾史上,他们只有模糊的历史面影。
排湾族的盲诗人莫那能,偶然得知祖母背上的长长疤痕是为抵抗日本人所伤,竟然大吃一惊,从小他只在教科书上学过“雾社事件”,原来抗日的不只是莫那·鲁道!原来自己的族人,也有过壮怀激烈的抗争史。从“牡丹社事件”开始,点燃导火索的排湾族已经置身一个风云诡谲的世界格局,置身整个古老中国在东亚近代史中的命运起伏。而这些,在光复后的教育体制下,是看不见的,讲述原住民历史的,是吴凤与吴沙。
记载祖先和历史的歌谣,失去了传唱的空间;教科书里,没有原住民自己的声音。部落少年无从了解自己的来处,无从确立“我是谁”,更无从建立一个民族的生存自信与发展意志。当他们在本该成为出色猎人的年龄,却为台湾出口加工浪潮挟持,漂流到都市,怎能不被文明的机器碾压窒息,怎能不被所在皆是的“歧视”刺得遍体鳞伤!
于是,一曲又一曲、至今不歇的“流浪者之歌”,是思乡的慰藉,是青春的怅惘,是未必自觉的反抗,是原住民族群处境的真实写照……
珍重!流浪的猎人!
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后期,二十余年间,台湾原住民社会与乡村有着共同的遭遇,原有经济模式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积累的需求,把一批批原住民和乡村子弟送入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1979年,在台北的夜市上有卷“卖疯了的”的录音带《可怜的落魄人》,陈明仁唱着“你可以戏弄我也可以利用我……”,看似失恋之人的自我戏谑,实则正是原住民与乡村子弟在都会的落魄写照。这才是它风靡的社会心理基础。无论当年还是现在,大概很多会唱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一首原住民的歌,一首典型的“都市林班歌”。
“林班歌是一群山上的神仙,因为每天劳动,回不了家,在一起哼哼唱唱,编出来的歌。”汉人的传说,山里总是住着神仙。1950年代至今,原住民始终是林务局林班地雇佣的主要劳动者,白天,他们除草、整地、造林;晚上,大家围火取暖、唱歌、排遣寂寞。这些神仙来自各族,布农、泰雅、阿美、卑南、排湾……甚至达悟,也有汉人,于是各族的旋律混在一起;国语慢慢成为主要的歌词;思乡和思恋,是当然的主旋律。
广财说,少年时在部落里和朋友们玩,会唱大哥哥们唱的林班歌;服役退伍后一度跟着爸爸去林班工作,意识到音乐是另一种语言,不同族的人,听不懂话,却可以用音乐唱和。诚然,林班歌就是这样从高山林班地传回部落,又被年轻人带去都市,不断地流传、修改、丰富、再创作,成为流落在外的原住民各族共同的“音乐之声”。
《珍重》与《凉山情歌》,都是产生于1970年代的都市林班歌。它的另一个名字是,《流浪者之歌》:“别了故乡,别了情人,当你明晨醒来,我已流浪在台北。”其实流浪者挥之不去的哀愁,不只因为离别。猎人的后代置身水泥的丛林,那里有某种源自文化记忆、流浪者自己也未必分明的错乱和迷惘。的确,原住民与乡村子弟一样在资本结构的驱动下进入都市,但对于原住民少年,出走,还隐藏着猎人本能的冲动,也因此产生更为复杂的悲剧意涵。
一个部落少年,十五六岁了,意味着什么?要出去,打猎也好,出草也好。要用猎物,或敌人的人头,来宣告自己的“成人”。“在这个年龄,不出去不行。”就像《珍重》这首歌的内容一样,在过去,原住民小孩国中一毕业(或没毕业),背起行囊加上一袋白米,就上台北去了。到了台北,找一位较年长的族人投靠,奉上一袋白米换得一席睡觉之地,开始外出找工作。卡车捆工、工地搬运工、板模工、搬家工……幻想着有一天衣锦还乡盖房子成家(爱人),获得幸福(猎人地位)。
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就是狩猎文化,一个原住民的小孩,从小孩、少年到成为青年,其实就是一个猎人的养成教育过程。不管是从卑南族的少年猴祭或是布农族的射耳祭或是泰雅族的少年训练,都是一样的猎人养成教育。一个原住民小孩成为猎人之后,从他猎取的猎物到回部落分配猎物,形成了一种完整的部落价值。当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社会被外来入侵而限缩了活动范围,他们的狩猎文化开始被瓦解,货币价值逐渐取代了狩猎价值。但是,原住民的文化价值却还残留在血液里,于是,外来的教育体制与原住民的文化价值产生冲突与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原住民学生的中辍率特别高、教育程度特别低的大原因。
“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其实潜意识里就是“过了少年阶级了,该去打猎了”。只是,传统的狩猎文化闯进功利的都市丛林,悲惨的故事就会一直发生,从汤英伸或是莫那能的故事里,都看到这样遍体鳞伤的原住民悲歌。
流浪到台北的原住民,在鹰架上和矿坑里拼掉了青春,1990年代中期开始,开始返乡了。靠劳动力赚取外汇的时代快要结束,残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外劳,被一脚踢开的原住民,不得不重回部落。广财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二十年。
在原住民社会,1990年代无疑是最难捱的年代,经历了1980年代经济、文化全面解体的部落,此时要容纳从都市回流的群体。贫薄的保留地,还能给予最低限度的生活。只是,这样凋敝的部落,这样身心俱疲的返乡者,该如何整理二十余年来的流离经验,如何寻找、重振属于原住民自己的价值?
《凉山情歌》也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台湾很多红歌星都唱过,而广财,以他对族群文化传统的思慕,以他所亲历、见证的原住民一代青年的命运,唱出“走了一步眼泪掉下来”,唱出了,这眼泪的重量。
寻找回来的古调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广财加入由原住民和汉人共同组成的“部落工作队”,到南投县仁爱乡山里的部落去救灾。救助工作告一段落,大家商量着举办一场部落音乐会来鼓舞士气。既然是部落音乐会,何不唱母语的歌?谁会唱呢?就有了云力思的《泰雅古训》和广财的《来苏》。云力思为母语教学需要,多年在部落做母语采集,从众多老人家那里整理出这首古训;广财则是源自头目家族自小的熏染,而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在正式场合唱过古调!“没有想过要唱。”
两首古调,在音乐会举办的部落引起轰动,引来驻留灾区众多纪录片、影像团体的拍摄;进而走入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广场音乐会,为城市观众和唱片公司瞩目。
广财回忆那时的盛况,“我们唱古调,为中原部落一位独居老妈妈织的布义卖,结果卖了三十几万”。一位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爬到灯架上看他们唱。
人们从古调里听到了什么?古调被“发现”了,然而它原本就在那里,老人家用他活生生的记忆在唱,年轻人即便很久没有在听了,也不曾真正切断这条通往他们所来之处的精神脐带。
面对唱片公司的穷追不舍,部落工作队思考古调的命运和未来。是让古调被娴熟的商业化操作,成为被都市人把玩和追捧的一种时尚“异文化”?还是让它回归到原住民的身心与生活,让它重新成为他们表达生存感受的语言,成为自我激励和抵抗的武器?
他们选择后者。寻找回来的古调,直接促成了“飞鱼云豹音乐工团”的成立。团员上山下海采集古调;在全台湾的部落举办了大小数十场音乐会;用工作坊的方式,制作了“黑暗之心”的系列专辑,然后在台北街头卖。“从音乐上所赚得的一分一毫,除了维持音乐工团本身必要的开销之外,便是回馈到原住民族运动去。”
在广财的家乡,很多人以他为标杆,来跟他学习古调。许多小学,开始有了以唱古调为主的学生合唱团。孩子们通过学习古调衔接文化之根,也以此走出家门,与外面的世界交流。古调,凝聚了原住民孩子的民族自信。
有次,在泰雅瑞岩部落的聚会上,云力思唱起了《泰雅古训》,一位老妈妈当场掉了泪:这是小时候听过的歌,再也没听过了!后来,有些泰雅部落时常用广播播《泰雅古训》,给晒太阳的老人听,那是他们的安慰。而一些泰雅小学校把《泰雅古训》编入教材:怎能不震撼,这是泰雅族失落的族群迁移史!
如今,部落工作队依旧致力于推动、支持原住民学校的古调、传统技艺的教习。古调,真的成了原住民再出发的文化基点。对音乐工团和部落工作队来说,这是十年坚持的最大成果。
而对于广财来说,寻找回来的古调,何尝不是为他开启了通往自我、家人、祖先和族群的生命通道。那年的台北街头,音响播放着《来苏》,在旁边卖“黑暗之心”的广财,“哦!听了怕有一千遍”。
此后,广财开始跟随父母和老人家重新学习、采集古调。在很多音乐人的眼里,广财歌唱的天赋之高,是不世出的,这一才能,当他遇到古调时,得以最淋漓尽致地发掘和展现,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天赋与其诞生、滋养的土壤的重新相遇。
广财一直是个体力劳动者,真正的素人歌手,不会记谱,很多即兴而发的动听旋律,因此很可惜地散失,但或许也因此,他的歌唱不曾被商业化地“清洁”。他演绎的古调,保留着部落草木烟火的气息,保留着思之久远的祖灵之光,也保留着面对现实的沧桑与沉重。
风华再现
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荒井说,广财叔叔的歌声本身就是故事,即使听不懂他的母语,只要是个对歌声有感悟力的人,他就会引领你。
二十七岁的音乐人荒井,对音乐的感悟和理解,似乎有着超出他年龄的丰厚。作为一个极出色的全能打击乐手,2008年与部落工作队合作奥运会开幕式暖场演出之前,他已经慢慢进入了台湾原住民的世界;在台湾一起排练、共同生活的日子里,让他觉得“好玩”的,一定不只是令人惊叹的原住民传统音乐,那布农的八部和音、兰屿的舞蹈、卑南的跳跃,也不只是原住民在音乐领域里的自如、生趣和率真,他几乎是直觉地把握到原住民音乐里深重的社会内涵,这内涵并不只是“唱歌跳舞的快乐民族”。
而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十八岁加入中国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读书、定居于北京,又做了台湾泰雅族女婿的日本人,荒井的国际主义显然不只在音乐的无国界。走进原住民族部落,探索原住民文化,他将音乐对真与善、对正义的期求,实现在自我的行动中。
对飞鱼云豹来说,并没有很多制作经验的年轻的荒井,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制作人。“广财叔叔唱得这么好,应当有一张自己的专辑”,只是基于这样简单的想法,荒井主动请缨。
根据对每首歌的感觉,他分成这样的几组:荣耀家族与Lumi,是广财的自我介绍,是序幕;日本风的两首情歌;1970年代的都市林班歌。这已经构成一个基本的、音乐变迁讲述的排湾族历史。
而后,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怎么重新“做”古调?广财的歌声和演绎之美,以及古调本身之美,是这张专辑的核心,因此配器是简单的;所有的配器和编曲,都是烘托,是为了更加有力地展现古调里的排湾往昔岁月,更准确地将广财、将我们这些现代人,从古调中获得对古老价值和当下生活的理解,表达出来。
《荣耀家族》和Lumi完全不用配器。日本风的两首情歌,只用木吉他,林班歌用钢琴。《采花生》是一首劳动之中唱的歌,曲调虽是自古以来流传,歌词却看个人的即兴才能,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充满了谐趣。在录制现场,来做广财和声的排湾族人,一唱起这首歌,立刻进入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感觉,“唱着唱着会自己笑起来”。《颂赞歌》则是年轻人聚会时互相的夸耀和打趣,同样有许多即兴。那天在现场的,除了排湾族的朋友,还有卑南族卡地布部落的智伟,于是在广财的歌声里出现了“卑南族人多帅气!卡地布人最勇猛!”荒井和广财多次合作演出的默契,得以创造一个生动自由的歌唱空间。许多小即兴,都被不加修饰地保留下来。
同样,在录制过程中,广财的声音,荒井也没有作太多修饰。在他看来,这些声音的变化,是十年岁月的刻痕,是广财生命的构成,是他最真实、最美丽的音乐人生。
最后三首经典古调,《咿呀伊》、《战歌》和《来苏》,荒井称之为《古调三部曲》,“好像交响乐的三个乐章。”在这里,将前面所有歌曲的味道,以及广财的音乐带给荒井的感受,重新统合。
《咿呀伊》,只用人声,一个排湾青年在歌唱美丽又惆怅的恋情,给我们重温排湾情歌的千回百转与韵味悠长。配器是很小的、隐隐的打鼓声,是为了后面《战歌》的鼓声作铺垫。隆隆战鼓响起时,来到了《战歌》那山雨欲来、剑拔弩张的古排湾战场。“头目过世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跑到他门前哀悼的勇士。”头目过世时,有人在山上发出某种“呜——”的声音报讯,每个听到的排湾战士,会立即装备自己,佩刀出发,跑到头目家集合。头目是被敌人杀死的吗?那么头目的死讯,就意味着一场战争的警报!在这首歌里,有着排湾族人所崇尚的机智、勇猛和保卫部落的责任感。
第三乐章,《来苏》,广财的成名曲,是让荒井,也让广财备感压力的歌。《来苏》是一首表达思念的歌,“啊,那个寂寞的人啊……怀念你的心情,就像山上的老藤,紧紧缠绕在大树上。”也是一首对人的体力和才能要求极高的歌。十年前广财的演绎,将人的深情、自然的空灵、宇宙的生息,统统自如地容纳到歌声中,如天人合一的完美,被以“天籁”形容。而十年之后,广财的声音多了沧桑,对长音的控制时有力不从心,一度给他很大的挫折感。总监说,何不试试交响乐?而荒井也愈来愈感到,这首《来苏》,不但承载着古老的排湾文化,也隐喻着当下排湾的现实,更伴随广财和部落工作队走过十年风雨。它思恋和惆怅的,不再只是一个姑娘,而更是那自由与荣耀的过往,是在今日情境下传承的艰难,是即便如此也要“来者可追”的坚决和苦涩……
于是,荒井与编曲反复讨论,被他称作“很天才”的北京的编曲人秦四风,根据荒井的讲述和对广财歌声的把握,找来亚洲爱乐乐团的几位首席合作,编出这版异常饱满、丰富的“弦乐来苏”。
“以前是用他的人声,完美的人声,把感受表达到极致,现在是用人声和配器,再创一个世界”。当你听完最后这首《来苏》,你并不会得到一个圆满的感觉,反而可能变得沉重和纠结。这正是荒井和飞鱼云豹音乐工团要讲的:
百年排湾,这不是一个开心的故事。
这是一个排湾头目吟唱的生命史。
这是飞鱼云豹的足迹。
这是台湾原住民族为了更勇敢地承担未来,所铭刻的记忆。
李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台湾的二二八文学》。
吉娃斯·阿丽,台湾泰雅族人,汉名高金素梅。
小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