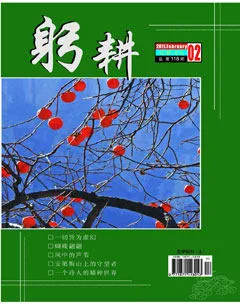诗意寒冷
冬日赏读宋代文彦博的题画诗:“梁园深雪里,更看范宽山……云愁万木老,渔罢一蓑还。此景堪延客,拥炉倾小蛮。”古人亲历而又描摹下来的诗情画意,启发笔者联想到,历代那些“诗”诸造化的篇章,就像书写在大自然这幅画面上的题画诗,将遥远年代的寒冬诗意彰显天地间。
《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四序更迭,暑往寒来,“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较之陶潜这一观察角度有变的秦观,却于山山寒色中细腻地观察到“草上霜花匀似剪”的美象。杨万里的目光则投向了人:“轻寒正是可人天”。诗眼之“可”,是天地人的和谐。
苦寒之时,诗人又于看上去很无诗意的景象中吟出了极具诗味的文字。精采之作有魏武帝北上太行山的《苦寒行》:“艰哉何巍巍……悠悠使我哀”,有孟郊“冻吟成此章”的《苦寒吟》:“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若细细检索,诗人笔下虽然呈现着周天寒彻的冷峭之色,但也不乏宋诗描述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之暖人景象。
迨至三阳开泰,“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转眼之间,便是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九尽杨花满路飞……的一幅幅欣欣向荣图了。这些与时俱进的诗篇,历经岁月磨洗,愈见光彩熠熠,独树一帜的唐代边塞诗,是瞩目的亮点。
很具代表性的岑参于轮台送往诗中描绘了“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大景观,并于时空大视角中捕捉到“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的特写镜头。活跃于大历间的才子卢纶,那首雄壮豪放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历代相传,极负盛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却提出了“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的质疑。值此开发大西北之时,旅人走边入塞,不妨亲临体验,或许能解华老之疑。
细品如此多彩的寒冬诗意,无不掩映着诗人那分浓浓的感情色彩。有例可证。贾岛倚杖晚望雪晴后,“溪云几万重”,“寒日下危峰”,“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让后人“wf0RVDzdQ7uA1klWjy8dgQ==推敲”出来的是少年为僧、后又还俗、屡试不第、仕途偃蹇而顿萌的诗人归念之情。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时间折竹声”,看似随手拈来的大雪冬夜之静寂,实在着意地透露出谪居江州的孤寂心情。战乱中回居长安的杜甫,在“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中,《对雪》愁坐愁吟愁书空,则隐现着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
若置换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诗品》的角度,解读寒冬诗意,又可发现严寒中特有的万“物”,就像对于人类有着特殊效应的“激素”,激活了诗人的激情,也激化出有别于春花秋月的寒冬特殊美。
典型的是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的梅。百花凋谢的隆冬季节,“万花敢向雪中开”,铁干虬枝,傲然挺立,枝头怒放,灿烂芬芳,“个个团冰雪”的“花魁”,“冰枝不怕雪霜侵”、“凌厉冰霜节愈坚”,“雪虐风饕愈凛然”。明丽的诗情画意,暗喻也赞誉着“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的“高标逸韵君知否”?
走笔至此,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天寒地冻中,欢喜漫天大雪的梅花似乎与雪结下了奇缘:或雪中竞开,或雪后绽放,或雪海一片,“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虽然,“梅湏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但对于“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的雪,诗人却另有一番情爱。
爱其洁,爱其白,爱其瑞兆丰年,爱其“天地无私玉万家”。生花妙笔下也就描出了“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的观雪图。而陈羽的那首“红旗直上天山雪”,俨然一幅壮美的风雪行军图,让人不由不想起革命战争年代中,“红旗漫卷西风”的六盘高峰和“更喜岷山千里雪”的伟人咏雪诗。
毛泽东爱雪,一生中的七十来首诗词,就有六首写到了雪。而写于一九三六年,经传抄后,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的《沁园春》──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情景交融,气韵兼备,气象雄浑,大气磅礴的壮丽画卷,将“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雪”,推向了至高境界──“江山如此多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