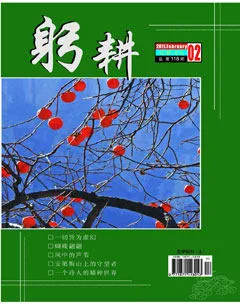关天培祠前的思绪
对民族英雄关天培,作为生在楚州(老淮安)长在楚州的我,既听过故事又看过书,还瞻仰过遗像遗物。尽管如此,最近又一次走进关天培祠堂时,英雄关天培仍在我的思绪里涌动。
关天培,江苏淮安楚州人。1834年10月,他受命广东全省水师提督,镇守祖国的南大门。1839年3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抵达广州禁烟,关天培成为林则徐的得力助手。他一面积极协助林则徐收缴英商鸦片,一面认真布置海防,督造排桩,设置铁链,准备抵御侵略。他的就任,尽管是因为道光六年(1826年)春的河运改海运的漕运给皇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受到的重用,但他要面对的却是刚刚发生了震动清廷的口岸——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率两艘兵船突然蛮横地闯入虎门,一边向虎门炮台开炮,一边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黄埔。虎门炮台虽然开炮阻击,但仅击毙英军两人、击伤七人,轻伤英舰,自己却损失惨重。所以,在赴任时,他就安排妻子陪同老母返回家乡,只带三个随身的家丁去广州。在牺牲前特地委派家丁将他的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还在战前遣人将一只木盒送回老家。他殉难后,家人打开木盒,仅见“堕齿数枚、旧衣几件”,清贫之状,“观者无不落泪”。记得谢晋导演的大型历史巨片《鸦片战争》,有一个细节可与此相印证:钦差林则徐甫抵广东,即破掉一个鸦片走私集团,起获一本行贿“黑账册”,个中所记,触目惊心。林则徐手举“黑账册”问两广百官:“谁自问没收过黑钱的,请站前一步。”堂下衮衮诸公顿时面如土色,有人甚至当场晕倒,只有一位须眉皆白的老将军昂然而出,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老英雄关天培。
由于关天培在广东沿海的严密布防,使英国侵略者在这个时期的一次次挑衅与袭击都被挫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义律率兵船二艘、货船三艘到九龙山口岸以索食为名,突发炮火,进行挑衅活动,遭到清水师猛烈反击,狼狈逃跑。两个月以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阻挡英国商人开商船具结,破坏中英正常贸易,挑起穿鼻之战,实际上这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开始。此次战斗,关天培亲临督阵,虽手臂受伤,仍奋不顾身,执刀屹立,督令弁兵,对准英舰连轰数炮,使它遭到重创,仓皇遁去。此后十天内,英舰又接连向官涌守军发动六次进攻,结果都被击退。
关天培认真整顿、加固海防设施,培训水师,为林则徐放手查办和销毁鸦片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要不要禁鸦片?禁烟之明令早在雍正初年就颁布,百年来的局面竟如我们今天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后来言官黄爵滋陈述了鸦片不仅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会给国家经济造成危机。为了有效禁止鸦片,他提出了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竟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实施“查禁”)。钦差点了湖广总督林则徐,说明拖拉敷衍几十、上百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去了之后还是被“革职待罪”。
林则徐与关天培是心有灵犀,或者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到了广州就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一场战争。他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就支持关天培积极进行战备。然而,大清朝却没有这个意识,仍然是以“天朝上国”自居。
其实,大清帝国1840年的战争至以后的战败,历史早已注定,它是科学技术的战败,是政治制度的战败,更是创新使命感的战败。在1840年的前47年,也就是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要求与大清帝国开通市场,进行贸易时,当时的乾隆皇帝却认为:“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傲慢、无知的乾隆依然沉浸在天朝帝国地大物博、物产丰沛,儒家文明、教化四方的梦幻似的田园牧歌中。
据史料载,为了让马戛尔尼见识大清帝国的威仪与文明,并让马戛尔尼认为拒绝得有道理,也自认为可以从心理上彻底摧毁马戛尔尼的自信心,乾隆特意让马戛尔尼乘船由京杭大运河到浙江,然后再乘海船回国。乾隆要让马戛尔尼开开眼界,见识一下天朝的强盛。因为在他眼里,就算再强大的蛮夷,其文明程度也远远不及天朝。于是,乾隆处心积虑,在沿途特意安排了军事操练,他要让马戛尔尼从心理上惧怕天朝的威仪与中华文明,从而不敢报复。
在江苏镇江,镇江总兵秉承乾隆的旨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操练。但在这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军事操练中,英国人看到的却是虚弱与落后:护卫城墙濒临坍塌,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只是弓箭、戟、矛、剑,和几支火绳枪。英国人评价道:“这些军队马马虎虎,战备松弛,棉靴和长袍显得笨重,不灵活、柔弱。”看到了大清帝国真面目的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两艘战iKrLfr3of95kK/J47L3+3g==舰就能胜过整个清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我们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
100年前,中国的西洋火炮制造和应用技术与西方差距不大,落后正从康雍乾盛世开始,以为天下太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康熙22年,天下既定,康熙对火炮技术改良便不再重视。黄一农《火炮》载:1715年,地方官员奏陈捐造新型子母炮,分送各营操练,上谕:“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其原因是害怕地方部队利用火炮谋反。而恰恰就在康雍乾盛世的一百多年间,西方火炮技术与日俱进,到鸦片战争前夕,已不可同日而语。黄一农先生叹息道:“无怪乎清朝军队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战争中,封疆大吏们纷纷向皇帝奏陈火攻破敌舰之法,让世人以为中国人仍生活在“火烧赤壁”的三国时代。还有那杨芳叶名琛之流的鸡血女人尿抗英之法,荒唐得则更让人哭笑不得。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1840年6月21日,40艘英舰在广东海面集结。为了粉碎敌人的进犯,关天培和林则徐认真商讨了退敌之策。英国侵略军曾多次妄想从这里攻进来,但壁垒森严的虎门,使他们胆战心惊,望而却步,便沿海向北进犯,攻定海。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前一天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在九分钟内就全军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英军攻下定海后,8月窜至天津海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闭关锁国而腐朽的清廷,稍遇挫折,就打击忠良,卑躬屈膝,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接替林公。
据《后汉书·灵帝纪》载:汉灵帝昏聩无能,他治国无方却玩物有术,早先玩马,其后玩驴,待两样玩腻了,就玩起了狗来。他让狗戴上“进贤冠”,系上“绶带”,一切按官员打扮,尔后把狗牵上金銮殿,还大叫大嚷:“狗官上朝了!”从表面看,汉灵帝让“狗官”上朝,是开玩笑,搞恶作剧。可纵观历史,比如对主人的忠诚等方面,人官不如狗官的却是大有人在,譬如讲,琦善就是一个。
琦善一到广州,就反对林则徐、关天培的做法,下令撤除关天培多年苦心经营的海防,水师被遣散三分之二,战斗力最强的募勇被全部遣散,这正迎合了英军的需要。
1841年1月,英军乘虚而入,攻陷沙角、大角两炮台,这样虎门失去屏障。此时虎门炮台只有少数兵力防守,形势万分危急。关天培坐镇前线,向琦善请求增援。可是,琦善怕妨碍“议和”,拒绝发兵。关天培极为愤恨,决定死守。他拿出自己的银钱补充军饷,鼓励将士英勇杀敌,又将数枚脱落的牙齿和几件旧衣寄给家眷,表示了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虎门,这个位于珠江口咽喉要隘的南国重镇,是进入珠江流域的重要门户,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两岸峰峦飞峙,水中岛屿突屹,在这众多的峰峦岛屿中,有大虎、小虎两山,宛如两扇虎形的大门,日以继夜地注视、凝视和窥视着过往的舰船,警惕地护卫着这珠江出海口。
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关天培以60岁的高龄,孤军奋战,浴血拼杀,亲自点燃大炮,与敌人激战l0小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拼杀不止,最后壮烈捐躯。
当时,已被“革职待罪”的林则徐闻得噩耗,悲痛欲绝,愤而挥笔挽之:“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竟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写下这副挽联后,林则徐意犹未尽,又笔走龙蛇:“我不如你”,接连两遍。
历时两年多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至后来的几十年中,又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国人痛心疾首。是什么让清政府失败的呢?军事战术、军事武器、官兵素质;经济实力、武器制造、后勤保障;官心民心、国民素质、人心向背……而从来没有人从大清帝国,制度层面上去寻找原因。几十年过去后,魏源写出的《海国图志》在书中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但却不为当时的帝国所用,后来的东瀛岛国日本却把此书捧为圭臬,最终变成日本发轫、变革、强大的思想基础……
是的,是与制度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尽然。“我坚信中国的社会闹得如此糟糕,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这是朱光潜先生七十多年前在《谈美书简》中的一段话。持这种看法的还有鲁迅先生。鲁迅的小说写尽了人心的凉薄和人性的黑暗,并终生以“立人”为其志业。先生说:“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举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鲁迅先生当年力抵“制度救国论”的迷思,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应该看到,他是在看到,任何制度都仰赖人对规则的敬畏,对人性的底线的持守。在一个人性的底线不断退却的时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完善的制度也难逃被扭曲、被消解的命运。
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在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
当然还有一种心坏透了的人:内鬼。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偷偷运进了天朝。”(《马恩选集》第2卷26页)其实,内鬼即经济间谍,自古至今从未断绝。最近的力拓间谍案就是例证。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而负担了抗战全责的清国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线集结的路上忙于勒索民财和污辱妇女,搞得民怨沸腾,就是整队整队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拱手让给敌人,英勇作战的场面屈指可数。即使那让可歌可泣的镇江之战,按照史家分析,那也是为守护家园而战。英军突破镇江外围后,用云梯攻城,镇江守将率1600名八旗誓死抵抗。城墙轰倒后,手持长矛大刀的勇士利用有利地形继续与敌激战。英军从多个方向突入城内,清军遂转入巷战甚至肉博,将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镇海一战,毙敌39人,伤130人,其伤亡数量创之前英军各战役之最。
为什么这一仗能打出国威呢?重要原因是英军侵犯了军人的家园。海龄率领的八旗子弟,其中有1185名已在此驻防了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茔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这个现象从“三元里”抗英也可找到例证。
相反,真正保国时,军民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官,贪贿的多,不少借机发国难财;兵,溃逃的多。英军进至厦门城下,“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此城”;民,观望者众。
民众为什么爱家而不“爱国”呢?家有父母妻儿,家有田园粮蔬,家是他们亲情和生存的全部之所在。而国呢?就太模糊了。千百年来,皇帝和各级官吏治下的国,给予人民的,没有温暖和关爱,没有权利和尊严,有的只是纳粮、缴捐、徭役和血泪。人民有做奴仆的自由,没有做“主人”的自由;有跪下的自由,没有抗议甚至逃跑的自由。历朝历代就是这样的“以民为畜”。
苏联的自我毁灭也发人深思。在诸多原因中,重要的原因是始于极权导致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之丧失,当权者的特权和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终于被人民抛弃。
是的,事情从来是相互的。
尊重百姓的朝廷被百姓尊重。
爱护百姓的政府被百姓爱护。
牛顿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量相等方向相反。
……
大清帝国,从开始的无坚不摧,到后来的不堪一击,难道就单单是体制问题吗?没有价值上的人心上的坚实支撑,再先进的体制也不会有生命力!
古老的大清帝国的大门最终是被枪炮打开的。办洋务、建立新军、建立新学、兴建报馆,虽然志士仁人懂得不仅要从科学技术上学习西方,更要从政治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但大清帝国的皇权贵族,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私利,不顾国家和长远利益,一再阻挠变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实际上,“医疗方案”与“实施方案”之间的距离却是形同云泥般的遥远!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从林则徐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帝的大旗,首先是林则徐高举起来的。“虎门销烟”,宣告了中华民族的奋起和觉醒,宣告了华夏儿女禁烟的决心和信心,成为中外历史。其实,每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华民族总是英雄辈出,有国耻、国难,必有国魂。在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人物,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实干家,并非林则徐一人。如果说林则徐是主战派的代表的话,那么,关天培就是主战派的实践者和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