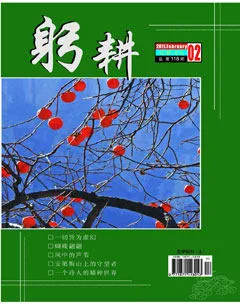香莲
香莲,此时坐在门前的矮凳上,用一副圆圆的竹撑子,把一块细白布绷紧,然后就在上面一针一线绣花。她不绣鸳鸯戏水,也不绣喜鹊登梅,她绣的是荷塘里的并蒂红莲。她从小就喜欢莲花,名字也叫香莲。生她的那年,父母是看门前池塘里盛开的莲花而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待到香莲深闺长成,果然名如其人,出落得亭亭玉立,面如脂粉,娇艳得十分可人,是远近出名的美人儿。
香莲在核桃树的浓荫底下,脸面久久地注视着池塘里的莲花,一只天蓝色的蜻蜒轻盈地在一朵盛开的红莲前上下翻飞,欲却又还。终于它落在了莲花上,细长的屁股却一翘一翘地翘得非常生动。香莲禁不住嫣然一笑,脸颊上立刻就显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香莲目前取景,就地取材,她要用写实的风格,把红的花、绿的叶和蓝得发亮的蜻蜒一起绣到雪白的绣花布上。虽说她绣不出蓝蜻蜒不住翘动的身体,但只要绣出它的轻盈,也就算十分生动了。
哥哥从生产队收工回来,一看见妹妹坐在门前一副招惹人的模样就来气儿!农村人最见不得女人不守妇道,倚门而立的样子。于是就黑着脸训斥:做针线活不正儿八经在屋里做,坐在门外干什么?香莲一见哥哥那不中看的脸,立即就收起一对好看的酒窝,一转身把个脊背正对着哥哥,仍旧不理不睬地勾着头绣她的红莲。母亲听到儿子的吼声,急忙在老蓝布围裙上蹭着湿淋淋的双手走出来数落:她坐那儿咋啦?碍着你啥事啦!我看你就是不待见你妹子,她在家吃你一碗黑饭心里就下不去?儿子愤怒地刚说了个你字,见自己的老婆又是摆手又是挤眼又是咧嘴的,只好长叹一声:都是让你给惯的!便荷锄进到院子里不吱声了。
要说这香莲也真让全家人伤透了脑筋。父亲去世得早,打从小母亲就娇惯着她,好吃好喝好穿养活着还不让下地干活。家里穷得叮当响,只靠鸡屁股银行换点油盐,一个妇女一年可挣两千多个工分,但老娘愣是由着她不参加集体劳动,整天穿得花哨哨的不是串街赶集,就是在家里做针线活。香莲不但模样长得俏,而且还心灵手巧,针线活是百里挑一,远村近舍没有哪个姑娘媳妇能比得上。特别是纳的鞋底和做出的黑灯芯绒方口布鞋,真是周周正正,有模有样,跟街上供销社商店里卖的鞋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但话又说回来,针线活再好既不当吃也不当喝,农村人只要身不露皮,脚不露趾就行,整天泥哩水哩,就是有好衣好鞋也没有好穿戴,更何况眼下连粗粮也填不饱肚子,哪里来得那么多穷讲究!
这些还都事小,更可气的是香莲到了出嫁的年龄,母亲也不知错了哪根筋,非要把她许配给邻村一户姓徐的人家。明明香莲又哭又闹死活不从,但老娘贪图徐家的三间大瓦房,一意孤行,硬着心肠看着徐家用帐着蔗棚的牛车把女儿娶了过去。香莲看似柔弱,实则内存刚强,临出嫁的前天晚上,就偷偷地把贴身上下衣用针线密匝匝地缝在了一起。新婚之夜,在她的奋力反抗下,新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一宿也没有把她的裤子扒下来。好不容易捱过了三天回门,她就再也不登婆家的门槛。害得媒人和新女婿三天两头往家里跑,又是说合又是苦苦哀求,但香莲终不为所动,坚决不到徐家生活。出了这等丑事,十里八乡传得沸沸扬扬,村里人也指指戳戳,说短道长,弄得全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接下来,香莲又提出了离婚。婆家在鸡飞蛋打的情况下,为争一口气,坚决不同意离婚。公社管离婚的干部老是磨磨唧唧,调解了一次又一次,总也调解不成。每次到公社去调解,人们便闻风而动,像看猴戏一样撵着。全国解放才十来多年,离婚在人们眼中是件极丑陋的事,人们说是去看离婚,实际看什么不言自明,还有围观的人们起哄说的那些话,更是下流无耻可恶至极!但香莲却不管不顾,依然一次次地去公社要求离婚。徐家人抱定烂麻绳也要沤过铁曲链的决心,就是不离不说,还到处散布香莲作风不正,已经和人好上了的谣言。
无独有偶,这时又传来了公社管离婚的干部也要同自己的老婆离婚的消息。好像要印证这一传说一样,那干部还时不时地骑着锃光瓦亮的永久牌自行车到村子里来,也不知道有什么公干,一来就到支书家里,掏出四两粮票两毛钱落脚吃饭。香莲一听说公社干部到村,便失急慌忙地前去相见,说是去要求尽快离婚的事,其中还有其他什么含义,谁也说不清楚。那干部穿着外贴四个兜的蓝卡其上衣,左胸前的小兜子里插着两只带鼻子的钢笔,胡须剃得溜净,满面放着红光。一见到香莲便热情异常,连连让座。香莲也不坐,只是依着门框,两颊飞满红云说她离婚的事。那干部一边打着哈哈,一边笑容可掬地说:别急别急,再调调,再调调。香莲艾怨地说:还别急呢,都两年多了,你能把人熬死!那干部就撇着腔说:离婚是件大事,不能马虎,真要夫妻没有感情了,而且分居多年,政府是会准许你们离婚的。看着香莲不满意的表情,趁机又用商量的口气说:你要是还有啥想法,隔天你到公社去,具体详细咱们再谈谈。香莲说:行。
第二天,香莲就收拾得干净利落地去了公社,下半晌才回到家来,具体谈得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于是,人们就猜想,就又传说,把她哥哥气得牙根直痒痒。
不过,最终徐家还是妥协了,毕竟就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数年坚持耗尽的不仅是香莲的青春,徐家也同样倍受煎熬。眼看着儿子年龄越来越大,再这样无谓的耽误下去,要想再娶就不那么容易了。香莲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那张渴望已久的离婚证书。当公社管离婚的干部在离婚书上盖上大红印章,把一张白纸对折,斯斯文文地从骑缝线上把下半截离婚书扯下来时,香莲掩住自己狂跳的心,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过了霜降,农事已毕,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街市开始熙攘起来。这天,香莲也精心梳洗打扮了一番,随着人们到街上去赶集。她先看了供销社的布疋商店,又进到百货商店,顺便浏览了街面上的小摊小贩,正欲折身走进一家街中心的缝纫店时,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挤进了汹涌的人群,任她怎么挣扎也难以脱逃。身前身后的十几个年轻人,紧贴着她的身体大呼小叫,明明是他们自己故意在制造拥挤,却又大声地嚷嚷:挤啥哩,挤啥哩,看把我的筐子都挤扁了!一边趁势用手在她的奶子上、后臀部不停地抓挠。香莲只觉得自己就快要窒息了,但是却无能为力,只能像一叶扁舟在人的洪流中忽东忽西地飘移。特别令她难以忍受的是紧贴在她身后的一个男人,把她的脊梁都捂出汗来了,却仍用一只手高高地举着一个篮筐遮住半个脸,煞有介事地大呼小叫,推波助澜。村里去赶集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冲进人群抓住香莲的一只胳膊生生把她强拽了出来。好心的叔伯禁不住劝她:女子家家的,没事来街上瞎逛个啥?谁知满脸汗水的香莲并不领情,白了他一眼,恼道:你管我来街上干啥哩!受戗的叔伯只好白埋白怨:好好好,算我多话行不行!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自打发生了这件事后,香莲的老母亲有了赶紧把女儿嫁出去的想法。但是看了很多家,香莲推三阻四不是说人长的太黑,就是嫌家里太穷,填房有孩子的誓死不嫁,反正总是没有如意的,出嫁的事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耽搁了下来。门前池塘里的荷叶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灼灼的莲花红了又谢,谢了又开,眼见得细细的纹路悄悄地爬上了香莲的眼角,核桃树下依旧坐着香莲,依旧是不急不忙,面含笑靥,深情地凝望着碧绿的池塘、清澈的小河和小河蜿蜒到远处的沟壑。已经年迈的母亲看着女儿的样子,不住地伤心垂泣:我的娇娇的女儿啊,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庄户人家的门儿不愿进,有工作的又找不到,长此下去能在家里扎老女坟不成!
直到有一天,一个在白水市工作的亲戚回来探亲,听了香莲母亲的苦诉,便试试摸摸地说:白水市一家大企业里有一个人,先前曾经是北京一家大报社里的总编,因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这里烧锅炉,早已妻离子散,现今独独一个人生活,绝对是个好人。就是岁数比香莲大许多,而且又是个右派,不知道合不合适?香莲的母亲大睁着昏花的老眼,无从应答。在一旁静听的香莲想了想说:行,先见见人再说吧。第二天香莲就打点行装,随着那亲戚去了白水城。
谁知,这一看竟看成了香莲的一世姻缘。也许是“右派”分子虽历经磨难却风韵犹存,也或是他挥动大锨时仍蕴涵着知识分子的斯文,反正一见面香莲没有意见。于是,就在单位草草举行了个简单的仪式,娘家也没有人送,仅置办了一桌酒席,请锅炉班里的几个工友喝了一场,就算结婚了。
婚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倒也充实甜蜜。家里人既把个包袱甩了出去,又觉得香莲找了个又老又有政治问题的“右派”,也不算啥光彩,平素便绝少往来。村里人反倒认为,这桩婚事虽说不上十分完美,但香莲毕竟是跳出了庄户门,在大城市生活,再不吃黑面窝窝头,倒也算嫁得不错。从此,便没有了闲言碎语乱磕牙。
原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不成想没过两年,竟然沧海桑田,时事变迁,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巨变。香莲丈夫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昭雪,马上调回北京原单位工作。一时间全家人欢喜不尽,一齐搭车到白水市去送行。看着市新闻系统欢送的热烈场面,香莲母亲喜极而泣,拉着女儿的手诉不尽的牵挂,话不完的叮嘱。一声汽笛,车轮铿锵,随着列车的渐渐离去,也把母亲对女儿绵绵不尽的思念带向了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