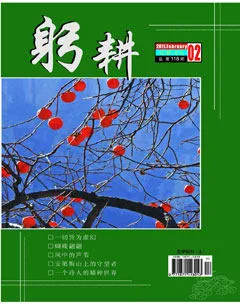风中的芦苇
雪下的那天,女人又出现在阳台上,望着对面山坡的“彼岸”出神发呆。
所谓的“彼岸”,其实是一座寺庙。坡上树木葱郁,于绿色的掩映之中,藏着这琉璃宝刹。
我刚刚从闹市搬来。这是一片废弃的厂区,绿意怡人,正适合我隐居写作的心态。我租住的这栋红砖楼,与“彼岸”相对。一入夜,便有寂寂的钟声从对面荡来,让人心有戚戚。
散步时,我发现,楼前有一棵树,造型别致,姿态生动,就去拍照。先是拍树,而后教孩子摁快门,把我和树一起照出来,以作记念,标示我曾经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此树为证。
“喂,照相的,过来。”
我寻声望去,原来是那个女人在二楼的阳台上喊我,一边招手。房子低矮,阳台可以攀爬上去。不过,安装了林立的铁条,像一个笼子,把这个女人关在了里面,但她的容颜,仍使我怦然心动。
“喊我?”我端着相机过去。
“嗯。”她笑起来,“你好浪漫呀,这么冷的雪天,还有心情同一棵树合影。”
我不好意思,她是在表扬还是讽刺呢?美丽的女人,危险的剌客,总让男人琢磨不透。
“喂,帮我来一张吧。”她继续笑,“告诉你,我也是一株植物呢,不过被栽在了阳台上。”
我为难,那些铁栏杆,太刺眼,拍下来,定会让人误以为是在看守所拍罪犯。想了想,我建议,“这样,你能不能下来?”
她拼命摇头,“下不来,他们不准我下来,我有好多年没有下地了。”
我暗吃一惊,她怎么啦?
“乖女儿,扔给妈妈一个雪球吧。”她又对我孩子喊,几乎是哀求。
孩子莫名其妙,望着我,嘀咕,“哼,哪个是你女儿?你又不是我妈妈。”
“咦——乖女儿,你不肯听妈妈的话啦?你爸爸那个坏蛋,悄悄跟别人跑了,我想去杀了他,你爷爷奶奶他们不准,才把我关在家。连下了好多场大雪,我都出不来,我想帮你堆个大大的雪人,一直可以堆到夏天,太阳也晒不化。乖女儿,听话,捏一个雪球,使劲朝我甩来,妈妈想尝一口。雪是最甜的,比盐还干净。”
孩子害怕了,紧紧拉住我的手,悄悄问,“爸爸,她是不是疯啦?”
我猛地醒悟,看来,她真的不正常。问题是,她到底怎么啦?让我看起来这么舒服的一个女人,怎么也会疯掉?
不忍心,我捏了一个松散的雪球,交给孩子,命令她使劲扔过去。孩子听了话,扔歪了,又扔,正中女人的胸脯,散落开。
两次落空,接不到雪球,女人哭将起来,变为号啕尖叫,非常伤心,听起来好不残酷。
过来了两个老人,对我训斥:“别逗她了,拿疯子来开玩笑,你讲点道德行不行?”
我辩解:“我不是在开玩笑,她要我帮她照一张相,还要一个雪球。”
老人“哦——”了一声,扯我到一边,叹气,“你们才来,不晓得情况。她是一个疯子,别理她,免得发作惹事。”
我追问:“怎么疯的?”
老人说:“都怪厂里面的下岗。我们这里是个大型棉纺厂,以前红得很,女工都有几千人,个个香得不得了,嫁人还要挑三捡四。现在啊,一垮台,哪样都完了,怪事也接二连三地来,跑的跑,走的走,病的病,死的死,疯的疯。以前我们这里是模范小区,现在鬼都打死人。咦,你是做哪样的?怎么还搬来这里?”
我难堪地笑笑:“我是写字的,喜欢清净。这里的房租便宜,到处是树,对面还有一座庙,让人安心。”
老人惊奇:“你是记者?怪不得,一看就不像做生意的。哦,对面的庙才新建几年,我们经常去烧香拜佛。那另一边,还有一个小教堂,拜上帝的地方。年轻人啊,要是有空,你也可以去玩玩,烧一炷香,才花两块钱。”
我点点头,“是是是,我最迷信菩萨了,念过《金刚经》。当然,我还信奉上帝,也读过《圣经》。”
老人高兴地走了,像完成一件功德。
雪,越下越大。放眼望去,对面的“彼岸”若隐若现,像一篇神话那样实实虚虚。
回到住处,孩子看电视。我泡杯茶,继续写作那篇叫《风中的芦苇》的小说。
玻璃外,雪花在疯狂地堕落,像一群隐入凡间的白色精灵。
为难的是,我不知道这件作品,究竟是该写成小说,还是写成散文。毫无疑问,想象都是现实的延伸,我要写的主人公,是一个女人——我的表妹玲玲。听到她的噩耗之时,我正在省城读大学。说来可笑,我的具体烦恼,不是学业,也不是所谓的失恋(还未恋上),而是对一件乐器的投入。本来,我是一个乐盲,对任何乐器都漠然,但听了小盼的吉他演奏之后,我就被音符俘虏了,他弹的乐曲,是西班牙著名的《爱的罗曼史》。
小盼是我的室友,下铺。他瘦瘦的,戴一副黑框眼镜,一天到晚练古典吉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的洁癖:任何人坐他的床铺,他都不舒服,但他不说,等你一挪屁股,他就扬起巴掌使劲地拍呀拍,好像要把秽气拍光。然后,低下头去找头发。找到了很满足,找不到很失望,他不容许一根头发躺在床上,包括他自己的。我要睡觉,总是光脚踩他的床跳上去,他也不舒服,照样啪啪地拍床单。最后,竟放了一块“遵义”牌烟壳在我踩的位置,成了我专门的“上马石。”
在班上,小盼几乎不讲话,只是疯狂地弹他的吉他。他在床头的台历上,记录了两句诗——“吉他的一生,就是被拥抱的一生!”被我偷看,嘘唏不已,以为他深得吉他之魂。可惜,他生错了国家和时代,要是在百年前的西班牙,他会是一名吉他大师,或者会与塞戈维亚(吉他之神)、耶佩斯(《爱的罗曼史》)的编曲及首奏者)他们齐名。遗憾的是,小盼并没有为吉他艺术献身的理想,他真正热爱的,是班上的女生余文静。她五官奇妙,长得像个混血儿。让人绝望的是,余文静和莫兮成双入对了。莫兮有钱潇洒,舞跳得好,是著名的校园歌手,会弹民谣吉他,经常哼唱那首《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一天,莫兮把余文静带进寝室,整夜快活,而另外的7个室友,则痛苦了一宿,包括我,也包括小盼。
校园的第一场雪终于落了,随同坠下的,还有一个女生。那天清晨,余文静套着睡衣,从六层高的教学楼跳下自杀。雪地上,溅开的鲜血,像宣纸上泼出来的写意梅花。
我们全班把余文静抬到殡仪馆,安排火化。化妆后,与亲属和同学作最后告别。躺着沉睡的余文静,化着精致的浓妆,像一个隔夜待嫁的新娘。小盼忍受不住,突然扑上去,俯下头,狠狠吻了余文静一嘴,由于用力过猛,竟把死者的头颅撞歪向一边。众人大惊,失声而叫。莫兮冲出,朝小盼拳打脚踢。死者的亲属,反而呆立不动。小盼跪倒在地,毫无痛苦之状,反而咧嘴一笑,笑得毛骨悚然,吓得莫兮立刻停止了施暴。
骨灰出来时,小盼苦苦哀求死者的亲属,由他来保管,他会用一生一世的光阴来陪伴余文静的魂灵。
当然被拒绝了,无名无份的,像哪样话?
回到学校,晚上小盼坐在狭长的宿舍走廊,又弹《爱的罗曼史》,反反复复,凄凉绝望的音调,把我们弹得浑浑噩噩,睡得极不踏实。
第二天,小盼离校出走,留下那把砸得稀烂的“红棉牌”古典吉他。我把那六根弦拆下来(断了两根),安装到了我的琴上,似乎凄凄不似以前声了。
不久,得知他的归宿——到黔灵山上的弘福寺,出家当了和尚,法名“无音”。在庙里,只有他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怪模怪样的,像个小沙弥。我们去看他,他神情淡漠,称我们为“施主”,仿佛根本不曾同窗就读。而我的心态,却完全称得上是“悲欣交集”。红尘与法门,岂是一墙之隔,余文静啊余文静,算你狠,你倒是“美人如花隔云端”了,留下我们在尘世苦苦挣扎扑腾。
紧接着,表妹玲玲的噩耗也传了过来,她死了,沉水自杀。在我有限的记忆之中,表妹是多么的活泼啊,一天到晚笑个不停,连挨大人的斥骂也都在笑。我只知道,忧郁成疾的人才投水自杀,比如外国文学史中提到的意识流作家伍尔芙,她在衣服口袋里揣满石头,一步步地蹚向湖水。我胡思乱想,表妹要是也热爱文学的话,长大后,会不会也变成伍尔芙?在我就读的这所大学,每个学期都要自杀一批学生(女生居多),以中文系为最,仿佛这二者有着某种神秘的对应。
无论我怎样地构思编造,这件作品仍是难以完成。现在,为了这个梦魇一般的夙愿,我从闹市隐居到这片衰败的厂区,继续虚构。我准备,还是用一首小诗来终结吧,献给表妹,献给疯女人,献给余文静,献给小盼,献给我自己,献给天下一切早逝的生命,哀怨的人生,以及整个忘恩负义的世界。
风中的芦苇
我看见你的时候 / 你正在水里游弋 / 河水吻着你 / 鱼儿躲着你 / 我站在岸上 / 幻想再等几年 / 就可以青梅竹马啦 / 像《红楼梦》里的少男少女 / 成长只是为了一种相思
后来,你死了,自杀 / 为几句流言蜚语 / 他们骂你是婊子养的 / 你的母亲,谈多了一次恋爱 / 离家出走,找那个骗子 / 你决定替她去死 / 帮父亲挽回一点可怜的面子
你就真的死了,让水淹的 / 没有发生奇迹 / 二十年了,我还站在岸上 / 在风中,就这样站成了一棵芦苇
写完,我扔下笔,朝窗户望去:那雪,下得更不耐烦了,敲击着玻璃,拷打着外面的世界。